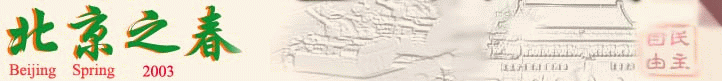比赛革命的革命
--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胡平
一、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革命是一场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广泛
的群众参与,就成为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
文革中的群众参与给出解释。在我看来,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
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
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这当然不是说,在文
革中,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只是说,各种不同的思想行为大致都
可归之於一个相同的心理动机。由於人们的处境不同,性格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不
同以及诸如此类,因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会表现出颇大的差异;但是,那并不妨碍他
们在心理动机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二、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
众所周知,当年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在人类生活中,政治本来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仅有政治
活动才能赋予生命的意义。人类最精华的本质在於追求不朽;而达成不朽的唯一方
式,便是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同类中安身立命,因为唯有与他对等的人方能判断其
行为,同时也唯有借助於同类的在场见证,才可能使他的行动进入共同记忆即历史
之中,并维持不朽。福山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认为,人不仅有满足肉体欲望的需要,
而且还有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为一个
具有某种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为了赢得这种承认,他甚至乐於冒着风险,克服其
动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标。这就是政治的意义之所在。
在当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革命。别佳耶夫指出,在俄国,革命并非仅
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中国的情况更
加如此。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
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於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
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
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
唯一归属。
在一个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谓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资源的社会,革命和个人物质利
益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本来,革命是贬低个人物质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
在前,享乐在後。”革命具有克制个人物质欲望的斯巴达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
有吸引理想主义者的强大魅力。但与此同时,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既然革
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这种社会又不可避免地会依据人们的革命程
度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它势必要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给予奖赏和惩罚
;因此,革命又常常是(虽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
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就迫使那些本来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尽量做出要革命的
样子。於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
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仅被大家视为唯一的价值,事实上它也的的确确是唯一的
价值。因为其它活动一概遭到否认、压抑,或者是被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而又大体
平均的范围之内。譬如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赚大钱是多么光荣的事,事实上你
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周围也没有谁比别人有太多的钱。一般人(这里主要是指城市
居民)的物质生活大都过得去,还不至於为了糊口而必须终日劳碌无暇它顾。换言之
,人的物质欲望既有基本的满足,故而缺少迫切的冲动,再加上没有明显的诱惑和
没有独立追求的机会;这就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民众将其精力投入政治,投入所谓革
命。
三、没有对手的革命
和以往历史上的各种革命都不同,文化革命--如果你硬要称它是革命的话--是一
场没有真正的对手的革命。由於十七年的极权统治,大多数人的思想心态均被铸入
同一种模式,大家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服从的是同一个最高权威(甚至连文革
的被打倒者也常常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尽管人们对同一套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
各自心目中的领袖形象也远非一致;但只要大多数人还都认同一个权威,整个运动
就必定还处於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任何真正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观点和行动就必
将遭到有效的压制。因此之故,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
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
。在没有公开的外部竞争者的情况下,文革势必成为一场内部的竞争。
文革既然是一场内部的竞争。因此,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
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大
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
不革命或反革命。我们不能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最关心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可以
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诚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言: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
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那些最可能使自己
获得胜利的手段和那些最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办法常常不是一回事。
文革的情况便是如此。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
为他们认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点更容
易证明自己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
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个人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回事;一个人
去做一种他认为最能招致他人好评的事情,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把问心无
愧作为最高标准,他会采取某种做法;一个人把赢得他人承认(或避免他人否认)作
为最高标准,他常常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态是宁“左”勿右。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宁可
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既是求胜的策略--左
对了,证明你比别人更革命;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错了,那只算认识问题,你的
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数人都宁“左”勿右,互相作用的
结果,又怎么不导致越来越左的结局呢?本来,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任何
一种政治运动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天然趋势;只不过在
多元社会中,由於其它派别、其它运动的对抗和牵制,防止了这种趋势走向极端。
整个社会有可能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相互制约中获得某种平衡;一旦社会本身是高
度一元化的,那么,这种激进化趋势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照理
说,毛泽东关於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
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
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
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四、文革--表演革命的舞台
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
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
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
普遍的沉闷和压抑;而且,越是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
越是那些处境优越因而自命不凡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
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那立刻就引起了
全国性的巨大骚动。这场骚动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如说在更
大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
。学生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
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
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不错,他们清
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
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
最高当局,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更
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最高当局为原则为光荣呢。
多年以来,共产党不断地向民众灌输它那套意识形态,灌输它精心编织的革命历
史神话。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许多青少年)对革命抱着一种高度浪漫化的憧憬,对
革命的暴力行为怀有极大的欣赏和崇敬,对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充满效仿之心
。因此,只要现实生活提供了某种理由或借口,许多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角色,
以种种夸张的姿态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而那种普遍的夸张表演反过来又造成了一
种煞有介事的气氛,以致於使得这些人把表演变得和真实难解难分。如果我们把这
些狂热份子称作真正的信徒(True Believer),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过於装
腔作势;然而,我们也很难把这一切仅仅称为表演,因为它们的的确确造成了可怕
的现实。
五、对若干现象的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革中群众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了。不妨举几个例子。
1、关於造反
和现今流行的解释不同,文革中的造反首先还不是对压迫的反抗。因为最早的造
反者大都是红五类出身,党团员,积极份子,既得利益者,不错,造反是指对那些
仍然享有正统地位的当权派发动攻击;可是,这种攻击决不意味着反抗正统。恰恰
相反,造反者是站在更正统的立场,批判对方的背离正统。因此,只有那些原先就
具有正统的身份,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具有更大信心的人,
才会率先打出造反的旗号,照理说,这种人既然是原体制下的受益者,因而似乎没
有造反的动机;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人比别人更早地领悟出文革的意义,他们正要
通过造反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尽管说到後来,造反派队伍吸收了不少
原体制的受害者,少数造反派人士还萌生了若干异端思想,不过这两类人始终未能
构成造反派的主流或核心。
2、选择与被选择
许多原体制下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投入了造反阵营,那与其说是他们选择的结果
,不如说是他们被选择的结果、在运动初期,他们被强行排除在“革命”潮流之外
,想“革命”而不可得;尔後,那个“革命”被宣布为“保守”,宣布为反动路线
,於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造反派。当然,他们之中的一部份人,从一开始就反
对歧视,反对压迫,这种反抗无疑是合理的。应当说这一部份人是比较自觉地选择
了抵制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只是就整体而言,那些政治地位低下者之所
以成为造反派,乃是文革那段特殊进程的产物,文革中最不寻常的一段插曲就是,
以刘邓为首的党的各级领导人,依循阶级斗争的惯例,排斥和打击那些政治地位低
下的群众以及敢於向上级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不管这种批评多温和或者是比正统还正
统)的人;而毛泽东却站在了刘邓的对立面。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古代希腊
的僭主就常常以下层民众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带领民众打倒旧体制和旧的统治者
,建立起更彻底的个人专政。如此说来,下层民众起初把毛视为他们的解放者,後
来又视为秦始皇式的最大暴君,那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3、从右派到左派
人们不难发现,文革中的某些左派,骨子里其实是右派。也就是说,文革中造反
派的某些(不是全部)成员,倘就其先前的思想倾向而言,实际上和五七年的一大批
右派份子更为类似。这种人大都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揭竿而起、投
身造反运动的。如果你认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动路线是打“人权牌”,那么,这些
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投身其间自是不难理解,但事情显然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所谓批判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
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
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
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这就怪了:为什么那些原来就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倒会
反过来对他们先前还暗中欣赏的人和事发动攻击呢?看来,那也应归因於比赛革命
的心理。
不错,这种人思想“右倾”,故而在文革前不被组织信任,且常常受到批评;但
在明确的意识层面上,他们自以为还是认同革命,认同领袖,认同正统观念的。正
因为他们痛感自己的革命性不被充分承认,所以他们把文革视为表现自己革命性、
证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机会,因此积极投入文革。在反动路线猖獗之时,他们多半
受到排斥,甚至遭到迫害。可是,由於他们在主观上仍认同革命,因此,迫害并未
直接导致反叛意识;相反,它倒强化了他们的忠诚意愿(吃不着的葡萄格外甜)。尔
後,毛号召批判反动路线,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既把毛视为自己人;与此同时,他
们又把自己进一步视为毛的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於是
,他们就更加积极地为毛的路线而战。作为过去受冷遇被排拒的一批,如今,他们
更急於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
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
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右倾情绪--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
一边。他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4、关於群众性暴力迫害
文革中,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论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暴力
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权),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
。相反,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在
於,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施暴者呢?尤其是,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
分明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以至於常常要违心地被迫参与
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
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行为往往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
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原因在於以下几点。
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於师出无名。一旦有了一个堂皇
的借口,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於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
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无怪乎率先出手者总是
某些根特红苗特正的人了。
更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於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
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激的行为来;於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激的行为,以证明
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
。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
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後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
。它是理性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
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
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
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
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
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
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
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
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
,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
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5、关於“失控”
文革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另一方面,
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於实
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充耳不闻,阳奉阴违。这与其说反映了群
众或群众组织的某种反叛性,不如说反映了这种群众运动的自身逻辑,反映了权力
本身的二重性。权力的本性是禁止。换句话,权力只可能对它要去禁止的事情有效
力,但对於它不去禁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效力。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地位相当於一个
终审裁决者,他说什么是革命的,什么就是革命的;他说什么是反动的,什么就是
反动的。当毛宣布某事是反动的时候,他的权力可谓锐不可当,因为紧接着就会是
强大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对於毛承认其为革命派的那些人而言,毛的威力就相当
有限了。群众组织在思想上接受毛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并不受毛的直接控制,其内
部又无严格的纪律约束。除非大家自觉执行毛的指示,否则,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
能够迫使他们不得不执行。不错,大多数人在主观上都是承认毛的无上权威的,可
是,在这种群众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最关心的是自己在竞争中胜过他人,因此,
他们往往不会按照毛的指示去做,而是按照最可能使自己获胜的做法去做。正如前
面分析的那样,在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中,故意做出种种“过火”“过激”的行动
分明是有利於自己获胜的,而一丝不苟地执行毛的指示反而会陷於被动。在毛这一
方面,既然你承认他们是革命派,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正确,这就意味着你对他们做
出的“过火”行动会采取一种理解和原谅的态度。那自然只会助长种种“过火”行
为变本加厉,屡劝不止。起初,毛“放手发动群众”,其目的很可能是假借群众的
自发行动之力,狠狠地打击他的政敌,同时又乐得以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为名推卸掉
自己的责任。但这种手段一经实行开来,毛也就使得自己对群众中的那些自发性的
“过火”行动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得於此者必失於彼。
毛对群众或群众组织的“失控”并不是後来才发生之事。例如,老红卫兵从一开
始就没有把毛泽东关於要团结大多数的指示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正想用排斥大多数
的办法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大体上说,毛泽东越是支持某一派群众,那一派群众
倒越可能对那些试图对其行为有所约束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这毫不奇怪,你
给予的信任越多,你能施加的约束就越少。被支持的群众一方则有恃宠而骄,有恃
无恐的心理,用当时的话讲就叫“自我膨胀”。对此,毛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他
干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动,打成保守,然後强力压制。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就是这
样从“小太阳”变成阶下囚的。要么,他搬出另一支更具正统性的力量(解放军、工
宣队)用以控制那些群众组织。最後,毛泽东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结束了群众运动,
重新回到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控制。
6、关於造反派的内战
导致造反派之间长期内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造反派的分裂实属难免。文革既是比赛革命的革命,老的竞争者(保守派)
退出後,新的竞争者必然出现。造反派内部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当初为了
对付共同的对手保守派,其内部矛盾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内部矛盾便尖
锐化、公开化。造反派的分裂与其说是矛盾的产物,不如说是竞争的需要。要使竞
争继续成为竞争,没有对立面也会制造出对立面,而制造对立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
到的。造反派通常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第三派势力一般都成不了气候。这和许多
民主国家两党竞争的格局很类似,第三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是缺少存在的空
间。要竞争,必须有两派;要使竞争保持高度的张力和集中的焦点,只需要两派。
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或曰争当核心。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
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
反对保守派,这就等於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
央不可能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给不了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
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选民投票
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
旷日持久,并且愈演愈烈。再加上普遍的暴力崇拜。当着两派内战发生暴力冲突时
,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消除它、防止它。许多人以为武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
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有些人甚至欢迎冲突的恶性发展,因为那使得
他们有机会效仿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谱写出一曲血染的青春之歌。本来,赞成武斗
的人并不算多;可是一旦武斗发生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其规模便会越来越大。
我并不否认造反派的内战也可能揭示出某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我相信,这种社
会矛盾决没有尖锐到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地步。我也不否认在这场“全面内战”中
,当局的纵容、挑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我这里主要是讲群众方面的原因。在
我看来,把造反派内战归结为争夺权力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尽人皆知,权力只可
能属於极少数人。大部份参与者不是追求权力,而只是追求自己这一派的优胜;这
样,作为该派中一员,他就能分享到一份胜利者的光荣。事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也
许会认为那种荣耀其实毫无价值,可是在当时那种戏剧般的场景下(不妨想一想培根
所说的“剧场假相”),它却使很多人感到莫大的激动。
7、赶下舞台之後
很多当年积极参加文革的青年学生都回忆道,他们是在六八年底、六九间初离开
学校,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之後,才开始对文革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刺激
这种集体性反思的原因很多。依我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被赶下了舞台
,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在被下放的最初日子里,有些人还力图保持先前的战斗姿态
,他们不时地交流有关运动的最新信息,力图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可是他们很
快就发现这种努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既然他们已经远离了舞台,他们如何还能继
续表演?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开始对文革有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他们开始产
生了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这其实是很自然的。
8、关於“峥嵘岁月”的回忆
三年前,一位昔日的红卫兵头头接受记者采访,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
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於说那段
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表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
。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
么具体的利益,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对之怀抱着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
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注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
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人
们热烈地投入文革的基本动机。假如我们承认,许多群众参加文革,与其说是为了
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不如说是通过革命以实现自己,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是那
样严重地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就对他们在运动中的种种表现--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也许是为我的论点提供的最後一个证
据。
六、政治心性学--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取经
以上几段分析,自然还很粗疏;要充实本文的主题,那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论述。
在这里,我只是想提出文革研究的一个值得深入发挥的方面,那就是从政治心理学
的角度研究文革参与者的行为。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可
是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们自己不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让
我们自己信服的解释。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关心这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