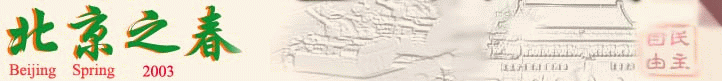我们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了?
仲维光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
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
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
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
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
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
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
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
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於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没有像李泽厚和金观
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
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
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
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
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
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
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
出国後,这些感觉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却依然存在。这两种文化和“知识”冲
突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在我的精神世界可能永远也消除不掉了。
从北京回到埃森,我第一次感到,两种不同知识的气氛,两种不同文化不仅存在
於知识界中,存在於人们的一般文化生活中,而且渗入到那些书本和木制的家具中
。
回到埃森,北京知识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北京知识界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依
然缠绕着我,令我思索。在知识的寻求中,在价值的认同中,根本性的区别在什么
地方,知识追求和精神探索又有什么关系?
一、王淦昌先生的行为奇怪吗?
七月中旬,还在返回大陆的途中,我就听说杨振宁在香港《联合报》上发表了王
淦昌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说,联署宽容“呼吁信”,实在是由於不了解情况
,受许良英愚弄。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去看望许良英先生。见面的第一个题目,当然就是这件事
。许先生首先问我,海外怎么看这件事。我说,在一般不了解情况和不认识王淦昌
先生的知识分子中,首先的反应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人们的反应和对
八九年冰心在签名信後的反悔的反应类似,认为,这么老了,你们还能丢掉什么。
虽然,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不完全是由於苟且软弱和出卖良心而致,但是这件事极大
地损害了王淦昌先生的形象。
许先生详细向我谈了签名信和最近发生的事情,并给我一篇他刚刚为这件事写的
文章的复印件。(详见《北京之春》九月号,总二十八期,许良英,“王淦昌先生是
受杨振宁愚弄了”一文)
许先生说,他七月十五日一见到王淦昌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受杨振宁愚
弄了!”王淦昌先生则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木头,他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
杨振宁愚弄了。”他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大科学家,在最近杨振宁送给他的一本书上
,有人称杨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许先生则回答说,“我无意贬损他作为科学家
的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
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墨索
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六四’後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
屏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相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
,叙述了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
王淦昌先生到底是受谁愚弄了呢?许先生是我的老师,王淦昌先生又是许先生的
老师,我的同出於许先生师门的几位“师兄”,都见过王淦昌先生。我虽然没见过
王淦昌先生,但是,看过几乎每一篇许先生写过的关於王淦昌先生的文章和庆祝王
淦昌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因此对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关系我是十分清楚的。“愚弄
”一说,首先出现於王淦昌先生致杨振宁的信中,他说,“此次签名事件,实受人
愚弄。”按照此说,应该是受许良英先生愚弄。然而在他见到许良英先生的时候,
同一个王淦昌先生又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
愚弄一词在中文中的涵义是蒙蔽玩弄的意思。就许先生对王先生的尊敬和爱戴,
就许先生所述整个签名过程来说,许先生没有任何要蒙蔽王先生的意思,而就许先
生的为人,不要说他敬重的老师,对任何别的人他也没有过用“手段”玩弄的想法
,因此玩弄问题根本不存在。况且,许先生找王先生,目的是“请”王先生签字。
以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地位比较,是“下”请“上”,“外(在野)”请“内(在位)”
,签与不签名,对王先生不构成任何心理的压力。况且王先生有过在八九年参与许
先生签名信的经历,按理说对此次签名公布於外国新闻界也应该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对王先生来说,签名信,信的内容如果没有任何错误,签了就完了,像八九年一
样,没有那么多後续节目。他只对内容负责。许先生请王先生签名,诉求的王先生
的正义感和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此次事件和八九年的签名信不一样的是,杨振宁先生要继续导演这件事。
他为此事专门给王先生寄去了信。首先,从信可知,杨先生给王先生寄去了一些谴
责和讨伐的材料,以及他自己的发言。并表明此信已经给国家造成危害,表明立场
後,询问王先生为什么签名。和许先生不同,杨振宁和王先生在此事中的关系则是
另一种性质。杨振宁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在私人信件中逼迫王先生在“危
害国家”问题上表态。而王先生在信中所澄清的就是,损害了国家,实非自己所愿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自己受到愚弄的结果。而杨振宁收到此私人信後,接着
要求公布此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诱迫。在杨振宁这样一个人面前,王先生无法拒
绝。在这件事情上,杨振宁先生充分运用了他的地位和声望,带着王先生走。
在整个事件上,王先生在和许先生的关系上是主动的,在和杨振宁先生的关系上
却是被动的。
事实上,使王先生说出“愚弄”一词,也属心理诱迫的结果。王先生从事科学,
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唯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技进步”。杨振
宁先生很了解这一点,因此祭出“危害国家”乾坤圈,自然打中了王先生的要害,
王先生要么花力气和杨先生争论辩驳这没有“危害国家”,要么否定自己,两者中
唯有“受愚弄”一条托词,可以躲避左右。但是,他却没有料到,杨先生还有第二
着,要求公开他的私人信件。杨先生此言一出,王先生又怎能拒绝。
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只用受愚弄来解释。杨振宁先生之
所以能把王淦昌先生在呼吁宽容信上签名事件导演成一个“闹剧”,是因为他利用
了王先生在价值问题上矛盾:尊重个人人权、人是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民族至上。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拥有现代知识,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把个人和人权
价值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则有可能被人利用,走入尴尬境地。
二、杂草丛生的知识界
这几年大陆的情况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争论起来莫衷一是。因为,社会问题好
和坏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它不像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那样,某些参数就是决定性的
标准。然而,就我回大陆所看到的学界情况,有一点可以说,方法和价值从过去的
教条、专断走向了混乱和堕落。人们也许可以说,混乱打破了过去的一统,为新的
,好的学术带来了可能。但是令人忧虑的却是,在眼下的混乱中,人们看不到任何
“好”的,甚至好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学风如江河日下,而且比从前四
十年更快。我是研究科学思想和科学史的,在北京时,居然看到了在德国和日本也
不敢登堂入室的一篇奇文。
在中国大陆一本主要的自然科学杂志《物理》上,一篇维护曾经为纳粹工作的德
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攻击石油大学的科学史研究专家戈革教授的文章中,居然出现
了这样的话:“其实海森堡就是造了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帮助德国造原子
弹是一大罪状,那么帮助美国造原子弹(如波尔、费米等)又是什么呢?何况原子弹
是美国扔下的,而不是德国扔下的。”(《物理》杂志,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卷五期,
第314-315页)
海森堡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和其他几位拥护纳粹的
物理学家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纳粹制造原子弹的工作,虽然在科学史上仍然有争
论,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材料的公布(如战後他们被关在英国时的谈话窃听录音的公
布),事情已经日趋清楚。而且无论怎样争论,也只是一个是否“积极参与”的问题
,都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的记录。否则的话,外才克尔(C.F.von Weizsae
cker)也不会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辩护。
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在德国,如果一位教授或教师,有这样的言论,他就可
能为此失去自己的教职。然而,在时下的中国,这青年学者,却可能自认为,也被
人认为是有思想。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这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青年学者”怎么会有这种言论,怎
么会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
在大陆我处处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被扭曲,这位青年学者是在和一位老教授
的谈话中,附和逢迎这位老先生时,说出上述这番话的。这位老教授四十年代曾经
在海森堡那里学习过,因此始终含蓄地维护海森堡,而著书翻译将近千万字的科学
史家戈革教授,在三次到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作访问研究时,研究波尔的同时
进一步研究了很多有关海森堡的资料,并就此和很多波尔研究专家和接近波尔的科
学史家讨论过,因此,他对海森堡和外才克尔的这段历史作出了否定的历史描述。
这引起了上述这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史实而是对海森堡性格的
相信,由於他在德国学习过,他爱德国,因此,他甚至对洪堡大学的德国科学史教
授弗里德里希·赫尔内克所著的《原子时代的先驱者》一书中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
史实,著名的物理学家约当(Jordan)曾经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
说,“约当曾经为纳粹效劳过,我以前确实没有听到过。”问题还不是在於这些老
先生自己怎么看,在於在这样一个一元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利用了这种一元
性,自己仅有的一点发言权,而不自觉地封锁了其他的声音。
无论怎么说,在物理学史上,海森堡可以说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是,谁能想像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中居然没有海森堡的传记?
而没有的原因居然就出在这位教授和戈革先生对海森堡的这段历史的不同的评价和
介绍上。事实上,海森堡的传记戈革先生已经写了。对海森堡的科学史研究在中国
就我所知恐怕没有人比戈革先生更有功力,然而,只因为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位海森
堡的学生,感情上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而恰恰有另一位老教授有不同声音,形成
了对立,结果就没有了戈革先生的这篇海森堡传记,就也被排斥在外。倘若不是老
教授间,恐怕就连一片涟漪都不会泛起了。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先生还了解
知识界的规范和伦理,说得很含蓄,没有任何过分的话,但是,他的“不相信”,
“没听说过”,并以此影响另一种意见发表,到了他的学生那里,就变成了那种放
肆的言论,并且毫无道德规范地攻击戈革先生。这种现象在文化和知识界的各个领
域都有反映,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知识界的怪事。
然而,怪事并没有完。本来那位青年的言论在共产党社会是极其禁忌的,现在确
实颠倒过来。戈革先生受到上面这位青年知识份子的这样的言论甚至包括私人攻击
,却没有地方发表反驳的文章。必须承认,这在共产党社会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这种变态,犹如共产党社会要用市场经济来挽救一样,各种怪异都会由此出来而
生。“假作真来真亦假”,一个竭尽所能也无法维持自己的价值的社会,为了苟延
残喘它所能做的只有宁肯混乱也绝不能允许任何极权相对立的价值观念进来,尤其
是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念。他们深知,在无理维持自己的价值时,也许越混乱对它就
越好。它形成一种虚假的宽松。这种宽松之所以虚假,在於它对和它对立的价值仍
然是毫不宽松。“真”的东西过去面临暴虐的专制镇压,现在在虚假的宽松下,更
面临杂草的窒息。
戈革先生虽然不过问政治,一生勤勤恳恳治学不缀。但是,到头来他在知识界吃
的却一再是变态的政治恶果。
三、丧家犬和知识份子的断梁之痛
师辈的是是非非,是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半个世纪的社会的沧桑变化,在每个
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风化石,浪淘沙,谁不想在生命中谱写美好与甜蜜,谁
不想体面而尊严地走完自己的生命。然而极权社会的风、浪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还涉及过另一桩关於他的另一位老师的争论。那位当年浙江
大学的著名的物理教授,解放後有很长时间被排除在科研以外,被迫劳动改造,从
事扫地清洁等工作。粉碎四人帮後,他终於鼓足勇气给上级领导写信,他说,最大
的希望是能够让他重新搞科研。後来,他获准了重新从事物理研究。此时,我怎么
也没有料到他竟然说出,“现在我才认识到,共产党真是伟大啊!”在读老先生去
世後的纪念文章时,看到此,我真是欲哭无泪!这位老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曾经
参加过对抗国民党的活动,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他没有低头,的确是一位正直
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共产党的几十年统治下,却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共产
党居然能把这样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脊梁如此彻底地打断,而事实上比这更可悲的
是,不但是打断,而且已经到了不知脊粱已断的地步。断了脊梁,还在发自肺腑地
喝彩。打断脊梁的丧家犬,尚且会哀号,尚且无人能钳住它的哀号。我问自己,我
问苍天:这是知识分子吗?这是人吗?人的基本尊严哪里去了呢?这样一个社会,竟
然还有人歌颂它,竟然还有人在它之中如鱼得水地成名,还有人在挽救它不要重蹈
东欧共产党的覆辙。
这位受尽苦难的老先生在七九年发表了一篇采访谈话文章,说他在1928年5月见到
爱因斯坦,後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曾经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一年(《光明日报》,
1979年3月9日)。
虽然在此前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谈到过曾经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经历,包
括当年他在浙江大学的同事王淦昌教授也从没有听说过此事,但是,许良英先生出
於对老师的信任,还是相信了此事。其後,许良英先生认为,无论如何这对中国的
爱因斯坦研究,是一件重要的事,因此,详细研究了这位老先生1949年後填写的多
种履历,并且再次查对了各种记载爱因斯坦在1928年的生活和研究情况的资料,最
後不得不得出否定性结论。
许先生发现,这位老先生在此前和此後填写各种履历时都没有提到此事,甚至没
有提到28年在柏林工作过。他的所有的履历中到只提到过28年在汉诺威工作,28年
10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而另一方面,在1928年,爱因斯坦几乎病了一年,年
初由於心脏病到瑞士疗养,回柏林後卧床四个月。夏天又到北部海滨疗养,因此不
可能给学生上课。事实上,自从1914年後,爱因斯坦就没有再担任过本科生的教学
工作,他在柏林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是柏林大学的荣誉教授,并没有正式
开设课程,只是偶尔对研究班做个报告,没有什么卷子要批改。那时,爱因斯坦研
究的是统一场论,其後一直跟随爱因斯坦工作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和其他四位很有
造诣的数学和物理学家是当时的爱因斯坦的助手。而许先生的这位老师当时刚刚上
大学三年级,不可能对爱因斯坦的研究有什么帮助。他所谈到的“查过资料,进行
过计算,也帮助他改过学生的卷子”,都是不可能的。他所谈到的其它情况和当时
也不符。於是,在九二年纪念这位先生逝世的文集中,许先生建议不要收入这篇不
服合历史史实的文章。
我看过许先生写过的考据这一历史史实的文章,也看过老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和
他的家属及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从史实,从我在大陆生活和与这些知识分子交
往的经验,我相信,许先生讲的是事实。我再次感到,共产党不但打断了知识分子
的脊梁,并且使他们丧失了能感觉到这种断梁的痛感,而且扭曲了他们基本的学术
和道德规范。老先生的文章出现在七九年,也反映了他整个性格被改造的时间变化
。从某些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到八十年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化到了一种什么
状况。我们能相信这个社会的什么?!
这位老先生,一生中竟然能如此被彻底地改造,固然是悲剧,而对於我们这些晚
辈,就不是改造问题了,我们从懂事时就成了畸形儿,就失去了正常的感觉。我们
这些晚辈曾经兴奋地跟着伟大领袖搞文化革命,参与迫害别人、迫害自己;在八十
年代依然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的改革要解决世界文明的精神问题,自以为那种无知
的叫嚣式的所谓文化讨论是百年来的最高峰?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自己
愚昧浅薄,知道自己丑陋吗?
我再次深切地感到哈威尔在九零年元旦文告中所说的:
“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
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早已习惯於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
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止是它的受害者,
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
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
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
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
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我回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见到各类知识分子,留下的和出来的一样,多的还
是毫无反省,还是那么无知而自大,还是忙於各种“市场效应”。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