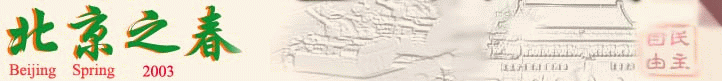漫谈“法制”文化与“人制”文化
David Mos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在我刚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些美国汉学家所写的关於东西方文
化对比的书,他们普遍认为,相对於西方的“法制”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应定义为
“人制”文化。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体系培育了不同的文化,西方社会是法律和
规范的结合体,中国社会则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产物。记得当时,我认为这种论断
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或者是过分简单化的以偏盖全。在我看来,美国人不管是找
工作,还是出书,买房子等等也都依赖“关系”,而且中国社会也必定大体和美国
一样是被法律所统治的,要不然的话,不早就乱七八糟了?
但是,通过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多次旅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论断的精确
性。它绝对不是什么简单化的以偏盖全,而是一个存在於两种社会之中的根深蒂固
的差别。认识这种差别对任何想和中国打交道的西方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最近
,一些美国人注意到了吴弘达,魏京生的审判,他们可能意识到了中国司法制度的
虚伪,但他们之中又有几个人能想像法律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
经常向我的美国朋友谈起中国,我发现他们完全想像不到两种文化的不同是多么的
普遍,大到几亿元的对外贸易,小到在街边买几斤蔬菜,几乎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
和差不多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最初是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到这种差别的。
在中国最让我们美国人感到不习惯的一方面是中国没有排队。有一年我在到达中国
的第二天去邮局发一封信,大厅中稀稀疏疏的只有几位顾客,不怎么忙,我排在一
位小姐後面,该我了,我刚要把信递进窗口,左肩头猛地被什么撞了一下,身体不
由自主的向一边滑去,耳朵里听得“两张邮票!”我站稳脚跟急转头,一个不算强
壮的中年人已然站在了身旁,手上拿着十元人民币直直的伸进了窗口,我惊愕地打
量着他没有一丝一毫惭愧的脸,一边还自以为是地想售票员一定会让他回去排队,
谁想到售票员竟然什么都没说就照办了!我有点生气,可信还得发,只得退了两步
让他先办,当我再次接近窗口,这次更简单,还没等我把手抬起来就被另一只冲锋
陷阵的胳膊抢了先。当时我真被搞糊涂了,“怎么回事?售票员竟然不闻不问!”
不用说,如果再排的话还会是同样的下场。我无奈地四处张望才恍然大悟:那两个人
并没有插“队”!只见所有窗口的所有顾客都蜂拥在一起争先恐後的把手伸进窗口
,这里根本就没有“队”可排!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误认为我在排队,并且以为我
後边的中国人也都这么想,但中国人并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没有什
么目的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的“老外”而已!不久,我发现很多我们习惯排队的地
方,例如:公共汽车站、食堂、售票处、邮局等等,排队这个概念对中国人并没有效
果,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这个习惯,尽管排队有很多明显的诸如缓和气氛,方便老
弱病残等好处。当然,要使全社会养成排队的习惯需要一种合作精神,那就是每个
人,不管那天你有多忙或心情多么不好,都必需遵守这个不言而喻的社会规则--老
老实实地排队,由於很多原因,中国文化之中恰恰缺少这种为了某种抽象的法律而
情愿牺牲自己眼前利益的精神。
当然缺少法律并不是没有好处,它意味着人们在处理事务时可以拥有更大的灵活
性,因而有时也会带有一些方便。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带了满满两箱子书
,上海机场,一个行李员通知我由於我的箱子超重必需到行李管理员那儿交纳罚款
,我随口问:“多少钱?”“你跟他商量吧。”他说。商量?这对任何在中国呆过的
外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当时我可吃惊非小。在我的美国观念里,飞机
场之类的公共场所的规定可以说就是上帝制定的金科玉律,几乎没有人就此讨价还
价。在美国的飞机场,超重多少罚款多少都有明确的规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我三十年的美国生涯中,从没有和任何公共服务员(包括汽车司机,邮局职员,护
照办理员或是飞机场的行李管理员)商量过任何关於价钱的事情。如果你试图和美国
飞机场的官员商量关於行李超重的规定,我敢保证你将得到彬彬有礼但口气坚定的
回答:“对不起,规定就是规定”。但在上海,我只简单的告诉行李管理员我是个学
生,箱子里全是书,并问他能不能免交罚款。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竟然同意了!
随着我在中国时间的增长,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由於公共机构缺少必要的规定而
造成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情况。有一年,我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去友谊宾馆换了些钱
并想顺便给我的父母打个电话报告我已平安抵达。我用中文清清楚楚填好一份付款
的电话单交给服务员,还好,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好心情地出了电话亭走到柜台
前。“先生,三百元人民币。”服务员还算和气。“我打的是对方付款,小姐。”
我赶紧指着电话单向她纠正。“噢,是吗?”她拿过电话单低头仔细地查看着,我
发现她的脸倏地一下红了,随即不好意思的冲我笑了笑。但她似乎对自己犯的错误
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一小会儿,皱着眉头拿着电话单走到里头去了,看样子是去
找什么人商量。好了,既然不是我的错,宾馆就理应支付这笔电话费,我自然而然
地这么想着。突然一阵唧唧喳喳的声音传来,我转头一看,只见那个可怜的犯了错
误的服务员正满面通红不知所措的坐在一边儿,另外两三个服务员挤在一起把那张
电话单仔细地看来看去并小声地议论着什么……看的出来,他们都认为这是她的错
,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看来是“头”的人走到我面前,想先试试
“硬”的。“你必须付电话费,这不是对方付款。”她态度很强硬。“我要求的是
对方付款,不是我的错。”我跟她讲理。“好吧,我们免收二十元的手续费,怎么
样?”她在讨价还价。“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对方付款,我一点错都没有。”我继续
坚持那怕是一分钱也不愿意付,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
。“你付两百元,怎么样?”“你这次付了,下次你在我们宾馆打长途电话我们免
收服务费,行吗?”他们七嘴八舌的都努力想说服我,唯独那个犯了错误的服务员
始终愁眉苦脸的盯着电话单坐在那儿一声不响,那表情就像面对不及格的期中考试
卷。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受到了侵犯。可以肯定,宾馆里这种事还会经常发生
,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那儿?在西方,宾馆就有相对清楚的规定,如果是宾馆方面的
错误,顾客就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但在中国这类事儿往往是就事论事,缺乏比较固
定的规则,每当事情发生後,问题基本都是通过双方复杂的协商解决的。整个事情
纠缠到最後我才意识到,如果我坚持不付款的话,这笔钱就会从那个倒霉的服务员
的工资中扣除,三百元人民币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於是我最终还是付了电话
费。近几年来,尽管中国的宾馆越来越多的采取西方宾馆对待顾客的标准,但外国
人还是经常遇到由於缺少固定的规定而引起争议的情况。
中国自古以来就在某种程度上对以法治国持怀疑态度,儒家认为刑和法对於他们
所创造的社会来说就是一种不理想的选择。他们认为法治只是通过惩罚使人畏惧,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态度,其结果,他们认为,是造成社会的表面的
,暂时的,脆弱的稳定,而相较之下,“礼”才是理想的治国之道,即改变人们的
思想,而不仅仅改变人们的行为。但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儒家一直把“法”看
作“礼”的直接威胁,而这种威胁又指向传统阶层。Donald Munro这样解释:无论贫
富贵贱,法律对所有的人适用,这必然会动摇贵族及其家族的优越地位,因为贵族
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很符合“礼”了,他们不需要接受和平民同样的法律制约。(D
onald Munro.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
ity Press.1969,P110)在中国,统治了近两千年的儒家创立了一个有利於统治阶层
的有着严格等级划分的父权社会结构,维护这种结构的有力武器就是所谓的“礼”
。而法律,意味着人人平等,它若付诸实施必然会导致等级划分的消失。我们不难
理解,儒家若要维护他们的正统观念--划分严格的等级,就必需排斥“法”而提倡
“礼”。
或许儒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中国现今的统治者一如既往地把和平,公正的法律
系统的发展当作对他们政权的巨大威胁。名义上,中国没有一整套的法律,但实际
上,很多法律得不到实施,而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例如:警察或掌握法律实施
的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如果得不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贿赂,那么
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的给你找各种各样的麻烦。
一九九四年秋天,我曾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和另外两个日本学生由北
大中文系曲艺专业的一位教授陪同应邀去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山东省林清,参加一
个研讨会,而且我还要在会议上报告一篇论文。从北京出发,经过十二个小时长途
汽车的颠簸,我们终於在晚饭时到达了大会安排的旅馆。作为人地两生的外国人,
我们老老实实听从大会组织人员的指挥住进了指定的房间。看起来,一切手续都办
完了,相当顺利。
第二天一整天都是在大会发言和讨论中度过的。主持人解释说,由於想发言的人
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分钟。他指着摆放在前边的一只闹钟强调“我
们必需严格遵守这个规定,要不然,时间就不够了。”
发言开始,第一个人上台,二十分钟後,铃声大作。“噢,这么快?好吧,我马
上就完。”他说。似乎没有人敢打断他,结果,这“马上”一下子拖了二十分钟。
这使我惊诧不已。接着,主持人重申了每个人必须严格守时,我想应该是对他的温
和警告,并告诫以後的人不要在犯同样的错误,但这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第二个
人仍然超时十五分钟。在我所有参加过的美国学术会议上,虽然也有超时现象发生
,但没有人会被允许超时一倍的时间,也同样没有人胆敢超时一倍的时间--那实在
太不好意思了。每个人,从著名的教授到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应当自然而然地遵守
规定。我是那天唯一没有超时的发言者,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结果可想而知--两个
人没有机会发言。
晚上八点多钟,我和那两个日本学生正在房间里说笑,北大的教授突然跑进来说
:“赶紧带上你们的护照和身份证跟我到楼下去,警察要找你们谈话”。糟了!我突
然发现我忘记带护照了!我曾经和这位教授参加过好几次类似的会议,从来没有人
向我要过护照,这此匆忙之中我竟忘记带了。
我们被领进一间烟雾弥漫的屋子,两个警察坐在床边一边看着无聊的电视连续剧
一边抽烟。他们站起来和我们握手,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带证件了吗?”
他们问。两个日本学生递过护照,我把我随身带的唯一证件--学生证递过去,其中
一个穿黑皮夹克的年轻警察仔细地查看证件,另外一个披绿薄呢军大衣袖子上标着
“科长”的年老警察开始用粗鲁的声音向日本女学生问话:“昨天你们几点到林清?
”他问。“我记不清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们六点到这儿,”科长继续问,
“现在是几点?”我们没有人带表,於是耸耸肩表示不知道,随即,科长从衣兜里
摸出一块表伸长了胳膊到我们眼前,那表情就像人赃俱获。“现在是晚上八点”他
说,“按规定凡是外国人到他们居住地以外的地区去,在到达该区的二十四小时内
应当登记。你们为什么没有登记?”“没有要求我们登记,”她有点紧张的自卫,
“我们是被邀请的,别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应该登记,我们
昨天到达这儿的时候,他们只说可以去房间休息了,我们以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把一
切手续都办好了。”
这时,黑皮夹克说话了,“粗心不是理由,”他用手指向我们“你们三个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们现在林清是不合法的,问题很严重。”我偷偷地瞥了
北大教授一眼,他平日弥勒佛般的脸已变得雪白。
“莫先生,你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黑皮夹克加重口气,“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第×××条关於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必需带齐证件的规定,你必须受到制裁
。”继而他脸上显出嘲讽的表情“你应该懂得这个,莫先生,你是美国人,大家都
知道美国是法制国家,对不对?你现在触犯了我们的法律。”我的腿开始发抖,我
知道试图辩解是没有用处的,只是不断地小声重复道歉“对不起,我懂了,我错了
……”
“哼哼……”科长不耐烦地清了清喉咙,一团浓痰落在了破旧的红地毯上。没有
人说话,素有洁癖的日本人惊慌失措地盯着地上那团发黄的的东西,空气里有点凝
固,我本能的感觉到这儿是“裁决”的时候了。
“两个日本人每人罚款五千元吧,这个美国人情况最严重的,我们决定他应交纳
罚款五千人民币”,(他们决定?难倒就没有固定的标准吗?)“而且,由於他的来
历不明,不能呆在旅馆,必须到公安局过夜。”我的血一下子凝固了。我原计划第
二天乘火车回北京,而且实在对冰冷的,耗子横行的林清公安局不感兴趣。我们几
个你看我我看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显而易见,这件事完全
是由於疏忽造成的,我们这几个书呆子是来参加学术会议,而不是在贩毒时被当场
抓获!我一直想他们是要我们的贿赂。这时,北大的教授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去
,亲热地搂住对方的肩膀,拍着胸脯自愿承担这场误会的一切後果,并迅速地抓过
纸笔开始写担保书,嘴里边一个劲儿的道歉。警察似乎愿意接受这个办法,但很快
我发现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保证书的遣词造句上,也就是说,教授无论怎样都不能
达到他们的要求,担保书写了一次又一次还是不合格……
他们整整扣了我们两个多小时,把我们的证件像研究古董似的看来看去,对我们
在中国的行动严厉地问了一边又一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几次提到“你们是远
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当然衷心地欢迎,但我们的工作是保卫你们的安全。”(但为什
么他们的出现反倒使我们感到更不安全了呢?)两个日本女学生被搞得泪眼汪汪,教
授还在与警察周旋,他的外交技巧和激情保证连基辛格自愧弗如。
真是“山穷水尽,柳岸花明”,正当我们被折磨的筋疲力竭要举手投降时,一阵
吉普车的马达声驶进了院子,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头”从里面探出来喊到:“别在这
儿胡闹!赶快回局里去!”刚才还趾高气昂的警察马上像老鼠见了猫灰溜溜地走了
。後来我们才发现,那两个骚扰我们的警察是因为对会议的组织者不满。大会早就
通知了他们我们将要出席会议,却忘记了请他们参加大会举办的宴会(最平常的小贿
赂)。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威被忽视而愤怒极了,决定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有意等
了二十四小时後才到旅馆来盘问我们。整个事情就像一场冗长而无聊的闹剧,我们
受尽折磨,而导演的动机只不过是报复没有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得到的“好处”!
一个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你应当理解这个,美国不是法制国家吗?”,具有讽
刺性的是,这些警察的行为却恰恰说明了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让许多美国人感
到惊奇的是中国的警察拥有太大的权力--他们可以自由的规定罚款的数目,可以任
意的拘留我们,可以随便地没收我们的证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情地威胁我们
,他们可以让我们在监狱里过夜,做任何他们想得到而又不至於引起外交风波的事
情。不难想像他们对自己的同胞该有多么严酷!当然,美国的警察也都不是尽善尽
美的,最近就发生了广为人知的警察殴打黑人事件。但一般来说,美国警察履行职
责时不能超越法律的控制,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警察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一
般情况下,他会警告你下次不要再犯,假如他恰巧那天心情不好的话,他会按具体
的法律条文收取固定额的罚款。
法律程序的缺乏,意味着在中国权力不仅掌握在警察手中,而且也掌握在某些提
供各种服务的人的手里。在美国,很多日常的服务(例如铺设自来水管道,安装电话
等)只涉及简单的合同性规范性的交往,只要你付了款,公司就会按部就班的提供相
同质量的服务。而在中国,这类服务往往牵扯到贿赂,拉关系,走後门,最让美国
人吃惊的莫过於许多中国的医生只有收到“红包”之後才会认真的对待病人了。当
然,美国也有贪污,警察和政府的官员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财富,但这两种文化
的不同之处在於对法律的信任程度,在美国,人们相信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能从法
庭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裁决。而中国的法律是如此的软弱无力,没有人把法律途
径当作严肃的事儿,有权势的人可以随便的修改,解释法律,一般老百姓即使受尽
冤屈万般无奈也不会想到用法律保护自己,在中国人眼里法律只是中看不中用的摆
设。多年的经历告诉人们,贿赂要比单纯的争取公平合理省事有效的多,所以,行
贿受贿,贪污腐败等等成了中国人既成的生活方式。
贪污不仅仅限於官员,即使非正式的协议也要涉及到美国人意识不到的而对中国
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贿赂。我曾经参加过密西根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进行的一次
调查。密西根的学者想就美国企业和中美合资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采访一些经理(结
果将作为机密文件保存)。采访美方经理的过程通常很简单。只要他同意,约定时间
,按时采访就可以了。中方经理要麻烦的多,我们在采访他们时往往需要请客,送
礼,这使增添了许多预算外开支的美国学者很不高兴。在美国人看来这种花费就是
贿赂,中国经理却认为这仅仅是他们所应得的最平常的利益。
我发现我很难对我美国朋友说清楚这两种文化的不同是多么的普遍。一般来讲中
国人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在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商人经常诧异的发现中国商人很少能
遵守商业合约,西方人倾向於“事先应订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约,不管最终我
们的私人关系好不好,双方都应继续守约”,而中国观念则是“如果我们的私交破
裂了,那么合约也就没用了。”
中国广播电台的热线有奖竞猜节目是中国人对待规则态度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节目形式类似於美国电视,电台的竞猜:听众打进电话回答主持人提出的一系列的问
题,如答对第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以此类推。答对题目的越多,奖金,奖品也越
多。在美国,当回答者不能回答问题时,他们如果要求主持人再给一次机会或要求
比较简单的题目,通常被认为是愚蠢的和无礼的。因此,美国人很少这样做。但许
多中国节目的听众当答不上来时,他们会说:“噢!这个太难了!能不能给我简单一
点的?或“你能给我一个提示吗?”或“让我再猜一猜”或“前边的问题容易多了
!”主持人常常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在美国,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别的听众会
喊“不公平!真愚蠢!规则就是规则!”。我总觉得这两种文化差别挺有意思。
北京新建立交桥的交通管理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西方以“法”为中心和中国以“
人”为中心的明显区别:近几年来,交通堵塞越来越成为北京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每个十字路口,犹其是立交桥的下面,自行车,公共汽车,出租车混杂在一起虎
视眈眈的等着转向不同的方向。美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严密的交通指挥系统来疏通
混乱的秩序。中国的办法却大相径庭,当我第一次看到友谊宾馆附近北三环高速公
路立交桥施工现场时,我暗自庆幸:“这下好了,他们肯定会建立一个严密的交通指
挥系统,划定仅供左转弯的区域,我就不用把脑袋提在手里左转弯了”。但当工程
完工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他们并没有在立交桥下面划出车道,也没有向左转的信
号灯,交通部门解决交通混乱的办法只是加宽了路面!人们转弯的时候仍旧重复着
他们以前所做的事--看准机会,扭动车把,毫不犹豫的插进两辆汽车之间,向着既
定的方向前进--仅仅是有了更大的“战场”!美国方法是尽可能的把人与人之间的
摩擦减低到零(连最小的城镇也设有左转的红绿灯),中国办法却是为人际的周旋提
供更大的余地。
理论上,设立一整套解决像交通混乱之类问题的法律意味着人人平等。也就是说
,数目庞大的车辆排列在十字路口,即使谁都不肯让步,而我技术不佳又不具侵略
性,我依然能顺利的左转弯,如果每个人都按法律行事,我们的生活就会简单的多
。美国的交通像一场编排精良的集体舞蹈,而中国的交通更像一场乱烘烘的拳击赛
。
美国人遵守交通法规像一日三餐那样自然。我的许多来自中国的朋友经常对美国
人凌晨两点钟在空旷无人的十字路口停车耐心地等待红绿灯感到诧异--没有别的车
辆,为什么不直接开过去呢?“怎么人都那么老实?”他们大笑,确实,美国人经
常想的很离奇,有时甚至可以说“无法无天”,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又都变得老实
听话了。这是我们从小就不断接受必须遵守法以适应社会生活的教育的结果。
基於这个原因,许多中国人总是嘲笑美国人“傻,死板。”在中国,我们通常挤
不上公共汽车,更不要说抢占座位了。在拥挤的商场里,我们天生的不会讨价还价
(我们潜意识里似乎认为商品价格是上天注定的,顾客和售货员讨价还价是不礼貌的
行为,如果你认为价钱太高的话可以到别处去买),在美国仅有的几次讨价还价的经
历在中国仍让我觉得不愿意这样做。作为美国人,我觉得它更像打架,而中国人仅
仅把它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排队,遵守交通规则等等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下意识的习惯,所以我们很少对
此产生争论。一次,我所在的印地安那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小组的一位中国学者因为
把车停在了禁止停车的区域而吃了罚款单。“我该怎么办?”他问。“去交罚款”
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去交通办公室说说,他们能不能就算了?”“
你不懂,”我有点得意的笑道,“这是美国,你不能再翻中国的老皇历,规定就是
规定”。但他还是决心试一试,我索性跟他进了办公室看个究竟。他向秘书解释他
没有注意到那儿禁止停车,并问能不能取消罚款。秘书被他这一问吓了一跳:“以前
从没有人拿着罚款单提过这种要求,”她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来你也许
不相信,交涉的结果竟然是他没有付任何罚款。这是我所知道的发生在美国的唯一
例外。
综上所述,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真实,广泛的根植於两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不同也反映在语言上。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曾经写道“西洋的
语言是法制的,中国的语言是人制的。”(《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47,
P,197。)就是说,西方语言借以单复数,时态的区别以及规范的语法表达意思,中
国语言更多的依靠上下文及场合环境不同的意境。“古人不主张不以辞害意,西人
的行文却是希望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
所有这些意味着,当美国人和中国人进行交流时(不论是贸易,人权还是其他的一
些日常琐事),他们常常在使用两种语言:法制语言和人制语言。中国人倾向於具体
事物,而美国人倾向於抽象规则。可以说两种文化难较长短,依关系行事会造成混
乱,一切以法律行事又显缺乏人情味儿。当然,这种说法有点简单化,但我想不管
怎么样,认识这种文化差异,对於东西方携手创造一个同时被“法律”和“人”统
治的未来是颇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