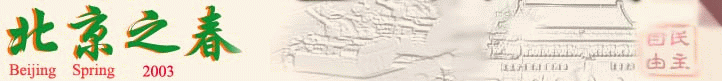铁汉刘刚采访录
胡平
五月二日,有“秦城铁血汉”之称的八九民运领袖刘刚逃离大陆後抵达美国波士
顿。当天,刘刚与《北京之春》编辑部的于大海、胡平通话。《北京之春》编辑部
与刘刚约定在五月五日进行一次电话采访。下面是这次采访的纪要。采访者胡平。
逼离大陆
胡平:半月前,我们从《新闻自由导报》上了解到你在大陆深受当局骚扰迫害,处
境危险的消息,十分关切。几天前,军涛、刘青告知你已安全逃离大陆,我们都非
常高兴。你能否把这次逃亡过程大略讲一讲?若干细节,眼下还不宜公开的,可暂
且不讲。
刘刚:我首先感谢海外对我的关切。我能够在监狱里坚持下来,那是和海外人士的
精神鼓励分不开的。
说实话,直到半个月前,我都并没有出国的打算。四月九日,我离开辽源的家。
当时没想到我能走出辽源。到了北京,我分别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和最高人
民监察院,检举辽源公安局对我的严重迫害。我有一盘录音带,录下了辽源公安人
员对我的辱骂以及来我家骚扰的情况,我还制作了一盘录像带,交给了路透社及其
它几个外国通讯社。我告诉他们先不要公开,等我和公安部交涉後再说。我向公安
部要求必须对辽源公安局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後来,公安部通过我一位
朋友转告说,他们也认为辽源公安局作得太过份,认为应该归还我被抢走的照相机
和其它钱物;但要求我必须回到辽源,并要求我不准将所带材料交海外公开,一旦
公开就要通缉追捕。这已是四月二十日左右的事了。我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四处
追我。我接触过的朋友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有时我邀约朋友出来见面,发现他们身
後有许多警察跟踪。在我投书公安部之前,我和朋友们的接触还问题不大。交出控
诉信之後,情况变得很紧张。有一次在许良英教授家门口,他们抓住我,我奋力推
开跑掉了。看来我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到了外地也是受到同样的待遇。於是我便
向海外的人权组织呼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辗转到了国外。
我能够在监狱里挺下去。可是我出狱後却受到更大的迫害。我的生活来源被掐断
,和我有交往的朋友亲人都受到骚扰以至殴打。在监狱中,我好歹还有吃有穿,也
不会连累其它人。出狱後我连生存都十分困难。我是在辽源市公安局的逼迫下才出
走的。
胡平:你讲的情况非常重要。以往一般人总以为关在监狱里固然是受尽折磨,出狱
後情况总是有改善的。可是在出狱後,当局的迫害可能更严重、更恶劣。这说明当
局对许多异议人士的迫害比以前更残酷。
出狱後的迫害
刘刚:关於辽源市公安局对我的迫害情况,我以前写过一些文章揭露。我可以举几
个例子。
我在辽源期间,凡是来我家看望过我的人,第二天就被公安局传去搜身审讯,把
衣服全扒光,警告他们。朋友和我在大街上走路,警察先把他们撞倒,然後辱骂殴
打,逼得别人谁也不敢和我接触。我到卡拉OK歌厅去,警察马上叫老板封掉歌厅。
我去乘坐出租车,警察马上把司机的执照没收,叫司机去公安局“请清楚”。我在
大中午,在辽源闹市区交通岗亭下给弟弟妹妹照相,警察上来抢走了我们的照相机
和钱物,还打伤了我的弟弟妹妹。
胡平:这简直是十足的流氓行为!你的遭遇告诉世人,我们不仅要对关在监狱中的
异议人士的状况予以关心,也要关心那些虽然出了狱,但仍在受迫害的异议的人士
的状况。
刘刚:据我了解,和我有类似遭遇的异议人士还很多。例如江棋生在天安门广场被
一群冒充流氓的便衣人员无缘无故殴打。邵江在天津也遭到一批便衣警察的殴打。
胡平:很多异议人士出狱後都面临到生活上的巨大困难。当局故意刁难,让你无法
生活下去。
刘刚:我出狱回家後,辽源市公安局给我提出了十三条监管规定。其中一条是要求
我每星期向派出所作一次思想汇报。都什么年月了,还思想汇报。我问他们你们是
要我汇报真的思想呢还是汇报假的思想。我的思想多啦。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思想
,汇报也汇报不完。我拒绝汇报思想。一周後他们宣布对我拘留。我向公安局申诉
,然後向法院起诉,最後向中级法院上诉。每一次均告败诉。直到九月一日世界妇
女大会期间,我被拘留。还有一条是规定我不准离开辽源市龙山区,除非向公安局
申请获批。另外,还规定我不准在国营和集体单位任职,不准到私营或个体单位担
任法人代表。这样我就无法谋生了。我申请干个体户,反复申请,拖了四个月,最
後宣布我不能办。後来我只好以别人的名义申办个体户,半个月之後又把执照没收
了。开头我以别人名义租了间房子,两天之後公安局就要求房主赶走我,还连累几
个中间人,说不赶我走就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是成心要断我的生路,要让我露宿街
头。在我家周围公安局布满了明的和暗的岗哨,单单是明的岗哨就二十多人。公安
局还安了一个探照灯直照我家,连邻居晚间都无法入睡。
胡平:这不仅是在威胁骚扰你一个人,也是在威胁骚扰所有的人。
刘刚:异议人士出狱後,生存更加艰难。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是非常残忍的。
八九之前的活动
胡平:我想,那些认为中国的人权与法制已经改善的人,应该充分注意你讲到的情
况。下面,是否讲一讲八九民运之前的事情。
刘刚:我本科就读於中国科技大学。八四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北大的政治气氛很浓
,每年都有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例如八五年九一八那次学潮,就是由我们物理系
研究生发起的。这次学潮对我是个很大的锻炼。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我写了很
多大字报表示不满,被公安局和 校保卫部带去审讯。一月一日我被捕,一同被捕的
还有三十多人。第二天,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我们获得释放。八七年四月,我
们推荐李淑娴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开始,我向学校提议提名邓小平和方励之,看
谁更得人心。校方不允。经过几次协商後,校方同意我们推荐李淑娴。校方施加了
很大压力。主要是由我出面和校方进行了多次抗争。团中央还派人来作我的工作。
在正式投票那天,校方用武力把我关了一天。这次选举很成功,李淑娴以超过百分
之八十的选票当选。
胡平:李淑娴高票当选人民代表,海外都及时地有所报道。不过对於这次选举活动
中的具体过程和你们所做的工作,外界知之甚少。
刘刚:我们关心的是如何使事情成功。在八九民运中也是如此。我和一些朋友做了
很多工作,没去争出名。共产党非点着你出名不可,那也没办法。要不是共产党下
令通缉我,恐怕你也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很早就读过你写的东西,受到非常大的
影响。
胡平:谢谢。我想,在国内一定有很多人,长期以来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海外不一定都了解。
刘刚:的确如此。这正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主要力量。我们一旦出了名,做事受到很
大限制。我们能起到示范的作用,传授经验的作用;但许多具体的工作,更多的还
要靠那些没怎么出名的人去做。我一直致力於和那些有着坚定的民主理念,现在还
不大出名的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我们的经验,在我们工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而不必老是从头做起。
胡平:中国民主,一是要前仆後继,一是要有效地传递经验。
刘刚:我发现我们彼此在观点上相当接近。关於民运的策略,关於广场学生该不该
撤,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原来我不知道你的观点,後来读了你的书才了解到你的
观点。
从八八年起——我那时已经毕业了,我在北京参与和组织了一些在学术界和在校
园内的学术沙龙,有些是在宾馆饭店,有很多重要的学界人士参加。八八年五四,
我和方励之先生组织了一个活动,我当时取名百草园,後来王丹改名民主沙龙。第
一次请了方励之讲演,第二次请了许良英,然後还有邵燕祥、吴祖光,最後是包柏
漪、洛德。
胡平:在科大时,你和方励之先生有不少接触吧?我们从方励之那里了解到你的不
少情况。
刘刚:我经常听他讲课作报告。广大同学对方先生的人品和学术成就十分敬佩。到
北大後接触更多了。我从方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原则。
我们和方励之组织民主沙龙——我还是更愿意叫它百草园,这名字更平民化,我
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公民论坛。通过这个活动,在北大同学中广泛地传播了民主理想
。在洛德夫妇讲演之後,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北大地球物理系本科生柴庆丰被流氓
打死,由此引发一阵学潮。同学们群情激愤,有些同学想上街游行。我当时不赞成
。我希望运用已有的条件凝聚成一股自由民主的中坚力量,而不是在时机不成熟的
情况下急於采取激烈行动,以免让当局把我们已有的力量和阵地摧毁掉。
胡平:我完全理解你的观点。先要做好扎扎实实的工作,积蓄力量,巩固已有的阵
地。
刘刚:从八七年开始,我就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特别照顾,到哪儿去都有人跟着,
我在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是我在走出陈子明的研究所时给他们偷拍的。
柴庆丰事件後,公安部把我视为北京不安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公安部副部长於雷
要我父亲去北京,要求我父亲将我接回老家辽源,给我发双份工资。这点我没答应
。另一条是要求我不准进北大,谁和我有接触谁就有麻烦。这时我发现我去北大的
确很不方便了,於是我就把民主沙龙的工作交给王丹、邵江他们。然後我又在圆明
园办了一个讨论会,叫渊鸣园。办了几期,後来受到警察骚扰。这些活动一直持续
到八九民运。
在八九民运中
胡平:接下来就是八九民运了。
刘刚:四月二十日,我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注意到吾尔开希,他敢於挺身而出反对
共产党。第二天我约他来到我圆明园住所。然後我们又邀约一批北大、政法、北师
大和清华等高校的同学来,成立了北京高自联。这大概是四月二十三日的事。从四
月二十三日到五月四日这段时期,我一直在高自联起核心作用。应该说这段时期高
自联的活动是很有理性的,很有秩序的。例如四二七大游行。起初我不赞成游行。
我提出几个方案。主张先在校内集会示威。这个建议没被大家接受。我又提议同学
们拉出队伍站在校门口,相对游行,我们不动,让来往的行人走动观看。这个建议
也没被接受。我当时主要担心发生流血冲突。
胡平:这种考虑很可理解。一场大的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一定要对风险有充分的估计
。
刘刚:最後,大家一定要上街游行。我说游行时要避免和警察冲突。遇到警察拦阻
大家便就地坐下。後来这一条做得相当好。走在前面的同学有些一坐一两个小时的
,然後警察自己退了。大家基本上在中午十二点到达广场。四二七大游行组织得相
当成功,它显示了人民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巨大力量。
进入五月,学生要绝食。我先找到王丹说最好不要绝食,一绝食就容易失控。後
来绝食开始,许多朋友劝我退出,我就退出了高自联。事後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件事
做得不妥,有点不太负责任。以後在联席会议上我又起了些作用,每次联席会议,
我都主张学生尽快撤出广场,回到校园进行整合。五月二十七日开会决定五月三十
日撤出,结果没有撤出。我不希望见到学生与军队对抗,但是我没有力量让学生撤
出,我只有自己走了。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回避责任,可是我觉得我要是留在广场会
被看作是赞成呆在广场,而那并不是我的主张。所以在五月三十日我就撤走了。
被捕与受审
刘刚:六月十二日发布通缉令,六月十九日我被逮捕。对於我被捕後在监狱中的表
现,我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也可以说为中国知识份子争了光吧。过去不少人总认
为中国的知识份子骨头软,一坐牢就成了甫志高。可是我在监狱中的表现,别人都
说不像知识份子。其实我是个知识份子,正是出於坚定自觉的信念,我才能顶住压
力不屈服。
胡平:说知识份子更软弱,这话本身未见公正。不过它也提醒我们,因为知识份子
大都是以提出一种观点、一种主张而进入实际运动的,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观点和
主张以及它们可能招致的压力有清楚的把握。我们应该考虑到,当我们的主张付诸
实行後,压力来了,我们自己,还有别人,是不是扛得住。这就是政治责任感。在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光辉的榜样。我之所以倾向於不太激烈的策略主张,是因为我
相信采取这种主张,大家比较容易坚持下去,不容易被压垮。
刘刚:通缉令公布後,到处抓人。这时,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跑了,我应该主动承担
起责任。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在警察面前不低头;同时我也相信我能树立一种榜样,
给其它人也增添斗争的信心。
胡平:我相信你一定事先对入狱後可能遭遇到的压力想过很多。
刘刚:想过是想过。我只是相信自己一定不会低头。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中国的监
狱竟是那么黑暗。这是没坐过牢的人无法想象的。
胡平:的确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住就更了不起。
刘刚:最让我自豪的是,在预审阶段,大部份时间我都直截了当地拒绝回答他们提
出的任何问题。有时让我签字,我就写下这样的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这当然是剽窃陈玉成的话,写完後把笔一扔,真是痛快无比!
胡平:这实在令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段经历都会感动。这实在是一种视
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
刘刚:本来,你是害怕的,你留恋生命;可是,当你面对警察写下这句话後,你一
下就感觉到你已经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胡平:是的,人就是这样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进入到一个更崇高的境界的。正如我
当初读到军涛写给律师的信时一样,我能够体会到你们在做出这样一番举动後那种
心灵的宁静、从容与坦然。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完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秦城 在辽源
刘刚:在秦城监狱受到很多折磨。我联络难友,经常展开抗争。刚开始我们约定每
个月前五天进行绝食。後来发现这样做对大家身体伤害太大,又改为每年的四月五
日、五月四日、六月四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十月一日进行绝食。许多次是很
多人一道进行的,为此也受到多次惩罚。有时,警察叫人恐吓我,殴打我,我奋起
自卫还击,警察打开门说别打了,咱们玩别的。(笑)
胡平:你在秦城关了多久?
刘刚:一年十个月。
胡平:和北京相比,外地是否更恶劣?
刘刚:北京要算文明的了。到了外地监狱,首先就要挨打。九一年四月一日,我们
被转到外地,先说要送到长春,到了沈阳公安局六处看守所,一进去武警就拿着枪
托来打。到了长春也是如此。这是他们的习惯,见面礼。
胡平:古代叫做杀威棒,像水浒传里的武松,一送到监狱,先打你一百棍再说。
刘刚: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十三个政治犯送到辽源第二劳改支队。一下车就来下马
威,来了二十多个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就开打。後来解释说为什么要打,是因为我
们眼神不对,没有低头认罪的样子。当他们用仇视的眼光盯我们时,我们不是像狗
一样表现出乞怜的神情,而是用严正的眼光回敬他们。
在预审阶段,当局想逼出你的口供。生活条件很恶劣,但折磨还不算太多。到了
判刑入监狱,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思想上洗脑,在肉体上折磨。他们要你改造思想,
改造不了就用暴力折磨强迫你改。一个负责人说:“我一手拿蛋糕,一手拿电棍。
我就不信有谁不要蛋糕专要电棍。”我对他们说,你们就是要把别人变成电影《追
捕》里的那个横路进二,你们不如发明一种药给别人打进去,然後叫别人干什么别
人就干什么,叫别人跳楼别人就跳楼,省得费那么大劲。在辽源监狱,我们受到极
大的折磨,讲也讲不完。
胡平: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刘刚:比如说,他们要求我们每天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是一本小册子,我带出
来了。
胡平:我还没见过。
刘刚:可以印出来给大家见识见识,一共有五十八条,六千多字。他们用刑事犯来
管教政治犯,每天抽背,正着背还要倒着背,背错了多少就打多少。刚进监狱我们
有个误会,看到日程表上列了大量的学习时间,以为真是学文件读书写字,後来才
知道学习实际上是体罚。要你面壁反省,坐一个小板凳,有时是坐一块砖头,一丝
一毫不准动。在所谓学习中,随便抓你一个错处就动电棍。
我们忍无可忍。我串连一批难友,在一次考试中集体罢考。警察来了好几十人,
一齐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着我们。有些人到最後几分钟支持不住了。不是他们软弱,
是那目光太凶狠。後来我们这些一直坚持的人,被他们一个个轮番拖去打。几个人
上来,拉住你的手一拧一转,胳膊几乎立刻就伤了,人疼晕过去。我出狱後和几个
关在别处的朋友一交谈,了解到别处的情况也是这样。
然後我被带到“严管队”,几个警察上来就是几十个耳光,过一会儿,我脸肿得
像馒头一样。一个警察炫耀说,谁能经得起我三个耳光,我就佩服他。他打了我一
连串耳光。犯人把这种打耳光叫做“拼盘”,这是五月二十四日,刚到辽源一个月
的事。
九一年七月南方水灾,辽源监狱特别想出风头,组织“献爱心”募捐,弄了几万
人民币,上了中央电视台。实际上这个捐款过程十分血腥。狱方要求每个犯人捐出
十元二十元。政治犯由刑事犯管,一些刑事犯要政治犯多交钱,他们就可以少交钱
或不交钱。有一个政治犯因为没有钱,所以叫捐钱时没吭声,几个刑事犯就上来用
皮鞭抽打,警察中队长也上来用脚猛踢。我说我帮他交了三块五角钱(这是我们每月
的零花钱),可是他们还是不答应。
凌源二支队非常恶劣。队长刁小天上窜下跳,六四後几次向上级请命,要求把全
国的政治犯都交给他们管理,中央拨款五百多万人民币,盖了一个可容纳万人的监
舍楼,但後来没有转来这么多政治犯,直到九四年,才迁进了一部份刑事犯。当时
给这群监舍楼取名暴犯楼(意指暴乱份子),我给他取名暴动楼。
胡平:像你刚才讲到的刁小天这种恶劣的典型,真应该把他们的劣迹记下来,公布
出来。
刘刚:刁小天极其恶劣,一言一行学毛泽东的样子,蛮横无理,说一不二。他领参
观团参观猪圈,指着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对人说这是三个月养的。有犯人提醒他这些
猪已经养了一年半。事後他把说这话的犯人打一顿,对他说,我说是三个月就是三
个月。他领参观团去食堂,那儿捆绑着一些大肥猪,他说我们天天给犯人吃肉。有
犯人对参观团说,你们一走,这些猪就送回圈了。当然,说这话的人事後也免不了
挨电棍。後来,连那些作摆设的猪都成了条件反射,一放出圈就往食堂的杀猪案子
上跑,让你捆,知道不会挨刀,事完後还可以大吃一顿。
每天,刁小天坐在门洞里,脱了鞋扣脚,盯着过往的犯人。看着谁不顺眼,就把
谁叫过来拿起鞋乱打,嘴里还训斥着,有时候知道打错了人也还是打。在监狱里,
警察用电棍打人是家常便饭,打得犯人叫唤,在外面听起来你会以为是屠宰场。
刁小天一手遮天,他把他儿子刁烈也弄来管犯人,连升三四级。刁烈最喜欢变着
花样整人。他说我的样子就是不服管教,因为我没像有些犯人那样,一见他眼色就
知道该点烟还是该倒茶。他要训练我也学会看他眼色点烟倒茶。我故意做了一次,
然後把这事告诉了新闻界,那以後他再也不敢让我点烟倒茶了。
刁烈随时寻机害人。狱方要我们糊火柴盒,发一把剪子。我上厕所,把剪子放在
书桌里。刁烈说我要给你加刑,因为你藏凶器,若有人拿这把剪子杀人,就有你的
责任。刁烈要我上厕所时也要随身带着剪子。可就在这同一天,当我带着剪子又上
厕所时,他又说我可以一脚把你踹死,因为你带着凶器,要杀国家政府干部。就是
这个刁烈,还不断地在犯人之间制造事端,挑起斗殴,实在恶劣透顶。有趣的是,
刁烈刚来监狱时还是一头黑发,很快就长满了一头秃疮。大家都说是报应。
这批警察打人还有一套理论。一次,我父亲——我父亲也是警察——来探监,对
他们说不应打犯人。他们倒振振有词地说,自古以来监狱里就是要打犯人的,不打
犯人就不叫监狱。象你这样心慈手软的就不配当共产党员的警察。
有几次我抗议警察用电棍打人,他们说,警察用电棍打人是合法的,要不,上级
为什么发电棍呢?我说,上级还发了枪呢。你用枪打死我们吧。
胡平:这真是赤裸裸的法西斯行为。
刘刚:我们进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贝克来访,我联络大家绝食
。开始警方没镇压,还做了肉包子引诱我们。二十小时之後对我们隔离殴打。在这
次绝食前,我用暗语告诉前来探监的弟弟,把这件事透露了出去。结果这个消息很
快传开了。警方对我们的惩罚没有上几次那么狠毒。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要求把
政治犯与刑事犯隔离,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包括刁氏父子),要求缩短劳动时间。那
时,当局刚刚发表人权白皮书,我们要求实行白皮书,照白皮书说的要就近服刑,
等等。这次斗争很成功。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明显好转,劳动时间也缩短了。
我们在监狱里受的折磨太多。必须讲清细节,包括警察的口气表情,才能给大家
一个清楚的印象。
胡平:我在八九年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记变天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
不报,时候未到。专制者干坏事,一向借助於庞大的镇压机器,造成群体犯罪。这
就使得那些作恶者能够以无名氏的身份躲避罪责。我们要善於把犯罪的责任明确到
每一个个人身上。索尔仁尼琴讲得好:这种人只有当他们是大机器中一个不被察觉
的零件时,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
候,他便脸色发白,十分恐慌,他知道他也等於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
。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虽然身处一部大机器之中,但你们还是可以选择的,事实
上也总是在选择。同样是执行上级命令,是消极应付,还是拼命嚣张。做好事记个
红点,做坏事记个黑点。
刘刚:我的体会是,共产党专制机器虽然凶残,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不
屈服,它也无可奈何。关键是我们大家都从自己做起,能做多少做多少,至少是不
要充当他们的打手,为虎作伥。
实现民主 保障人权
胡平:你和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在八九之前就有不少接触?
刘刚:是的。我毕业後找不到工作,当局处处作梗,找一个破坏一个。後来与子明
、军涛结识,彼此十分认同。那时,我後面有一大群尾巴,子明的研究所也受到严
密监视,有些事不方便合作,只能分头做。在经济上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没有他
们的帮助,我当时无法坚持下去。子明他们早在八九之前就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外
人知道很少。
胡平:子明他们的工作,对後来的八九民运有很大的意义。
刘刚:现在,共产党对异议人士实行经济封锁,尤其是对有些异议人士,出狱後继
续骚扰迫害,把人逼上绝路。例如我自己,出狱後完全没有经济来源,找工作,申
请个体户都遭到封锁。当局故意刁难,起初要你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等你什么都备
齐了,它又不批,让你在精力财力上都受很大损失。警察多次打伤我弟妹,还扬言
要打我父亲。我母亲身患瘫痪,我在家里,不断受骚扰,直接威胁我母亲的安危。
据说李鹏曾下过指示,说对刘刚及其亲属要严加监视,若有出轨行动,就采取断然
措施。一付六四屠夫嘴脸。我在大街上,几次被人用摩托车故意冲撞。还有警察呆
在家门口,对着我们摆弄枪枝。
胡平:这是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动向。
刘刚: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还很多。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是
随着经济发展而好转了呢,还是在许多方面更恶化了。我们必须唤起世人对这些情
况的重视,尽自己的力量给国内人士支持帮助。归根到底,只有改变专制,实现民
主,才能真正保障人权。
胡平:六四又要到了。我相信你的讲话会给大家很多启发和鼓舞,希望你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