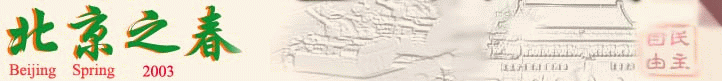一个外国汉学家回顾文革
林培瑞
(一)瞎子摸象
今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中国人作回顾的同时,像我这
样的外国汉学家,也不妨作一点回顾吧。
一九六六年我刚大学毕业,学了点中文,中国的媒体发出来的理想主义口号对我
很有吸引力。当时我常看《中国建设》,学习怎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偶尔
还戴上毛像章。很想到中国去,但中美两个政府都不允许。
一九七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美国第一次公开的来往。我很荣幸的被选为美方翻译之一;後来,因为我和其他
五位美国翻译的这项服务的关系,中美两国的政府似乎都改变了初衷,批准我们去
了一趟中国。
我们一九七三年五月动身,兴奋不已,喜出望外。四个星期里头跑了七个城市—
—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费用少得不可思议:吃、住、玩和
一切交通费用加起来不过五百六十块美元。
当时到中国去的白人真是很少,我们到哪里都享受非常特殊的待遇。每次上公共
汽车,卖票的大声喊,“外宾!外宾!让位!”然後我们上了几个人,马上就空几
个位子。我们自然感到难为情,怎么会愿意坐呢?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让给我的
时候,我注意到一副很疲倦的脸,知道他并不是很情愿站起来的。因此我也拒绝坐
,恳请他再坐下。但上面吩咐,他不可能再坐。车上虽然挤得不堪,那个位子却一
路上都是空着的;真是滑稽现象。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小孩成群地跟着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後就会有几百个,甚
至上千个小朋友,像彗星的长尾巴一样,默默地跟着,不走太近,不太说话,但不
管多么远也不散。有一次我们穿过动物园门口,已经买了票的小朋友就跟上了我们
;显然,我们比斑马、长颈鹿还新鲜。
我偶尔喜欢停下来和小朋友们谈话。有一次我问了他们将来想作甚么。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
“像甚么地方呢?”我问了他。
“像…”他想了一会儿:“像新疆啊!”
“你呢?”我问了另外一个小朋友。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跟刚才的回答一模一样。
问了十几个小孩,都照样重复了那句话。除了那句话,几乎甚么也不愿意说了。
我们作为外国客人,连比较艰苦的地方都不容易看到,更不必说“最艰苦的地方
”了。只有到唐山的时候,访问了有名的煤矿,坐电梯下到了矿底的隧道网,那里
坐上了小轨车,大概走了四十分钟。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矿外头,不
管到哪里,都看的见毛语录,红红金金的都是很漂亮的牌子。但是矿底下,虽然有
灯和许多工作有关的牌子,但是毛语录都没有。
出来以後我问了我们的官方导游为甚么矿里没有毛语录。他想了一会儿回答:“唔
……太脏了吧?对毛主席的语录不够尊重,工人自己不愿意。”
我当时基本上还是很羡慕毛时代的理想主义。只有听到这些反面的线索以後才开
始发生怀疑。为什么十几个小孩里头没有任何不同的想法?为什么所谓“太脏的地
方”对於几万个活着的工人不算什么,但对毛泽东的话反而就“不够干净”呢?
一九七九年我到中国去住了一年,那时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我六年以前发现的小
线索现在已经变成大河流了。我一层一层地更深入的理解了毛时代的真实情况,一
方面感受到了毛的骗,一方面怪自己本来太天真。
承认自己受了骗,自己太天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受骗的时间越长,
放弃幻想就越难。很多美国自由派,亲左的所谓“liberal”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
父亲可以作个例子。他老人家一九零七年出生,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受
过苦,开始向往左派思想,羡慕过苏联,几次带了旅游团访问苏联,越访问越相信
共产主义。六十年代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爸爸觉得毛对。我小时
候一直跟着爸爸信社会主义。後来到中国去,发现爸爸的理想和中国的日常生活根
本不是一回事,大失所望。但是我告诉爸爸真实情况却一点不起作用。他不太相信
,反而觉得儿子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为此,我颇有几分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但後来想了个法子。父母退休了,表示愿
意到中国去教英文,我介绍他们一九八三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住了半年。我以为,让
他们去住一段时间,就是不懂中文,一定也可以感觉出来毛的宣传和中国的日常生
活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回来说中国很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
”。毛还是对的。江青四人帮也不像政府说的那么坏。
我那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并不一定客观事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尤其是一
辈子根深蒂固的信仰。积累久了的情感和理想比事实更有力量。我爸爸这种好心的
美国左倾知识份子,对於中国文革抱的希望尤其没法子改变。在他们看来,中国似
乎不是实际的中国,而是一个奇妙的镜子。美国社会有什么问题,遥远的中国能够
反应出一个理想的解决法。美国贫富悬殊太大,中国是平等主义;美国犯罪率太高
,中国路不拾遗;美国人自私,社会主义新人都大公无私。有这种理想的美国人之
所以没法子放弃对中国的幻想,是因为放弃了它等於放弃了改变美国的希望。
韩丁(Willian Hinton)先生出了一本新书。韩丁本来是美国人,在毛时代的中国
住在中国农村,写了一本叫做《翻身》的长篇著作,盛赞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邓时代的改革一来,韩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这本新书叫做《从九天之上到九地之
下》是歌颂大寨的主角和文革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陈在毛时代的大寨过的
是天堂般的精神生活,後来在北京公寓里头过的却是一种地狱生活。我爸爸今年八
十八,肯定会喜欢韩先生的书。
(二)极权和反作用
一九六六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美国人对这个运动的初步印像
是很好的。那年我刚进中国历史研究所,最羡慕的是文革目标的彻底性。不但是要
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人的自私心理,要“斗私”,要“一切为人民”,要“在灵
魂深处闹革命”。我觉得多好啊,多大胆!
後来发现我同辈的很多年轻中国人本来有过同样的感觉。他们决定以身作则,抱
着很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精神到中国农村去参加劳动,“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等
等。没想到的是到了人民公社以後,发现农民的生活和本来所抱的社会主义理想是
完全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农村的普遍贫困是主要问题,但是很多别的社会情况也远
不如理想。当地的干部骄傲不讲理,甚至剥削、虐待、强奸,和雷锋模型相比的话
,是一个大讽刺。“为人民服务”和其它漂亮口号都显得空洞和虚伪。
有一位加拿大华侨学者,名字叫梁丽芳,前年出了一本书,里头搜集了二十六篇
访问录,受访者都是中国中年作家,包括莫言,王安忆,张承志,郑义,等等。这
些作家几乎都是六十年代热情献身於文革,後来大失所望的人。但梁教授发现这一
代到了七十年代末,并没有因为理想落空而放弃了理想。放弃的只是盲从权威的习
惯,本来的理想主义却还依然活着。文革的经验给这一代人带来的最後效应不是“
朵朵葵花向太阳”,而是一种反抗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
”,“寻根文学”,“文化热”和“八九民运”都跟这一代人在文革期间产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有关。九十年代初,刘宾雁说了一句“没有文革今日中国可能跟今日的
北朝鲜一样。”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但是文革的效果,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等於文革的极权主义起了很大的反作用
。种下的种子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梁教授的书名叫做“早晨的太阳”就包涵着这么
一种微妙的涵义。她借用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名言,“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
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是那一代青年走的路子不是毛先生所希
望的。也可能不是他能够想像得到的。
九十年代,文革的另一方面的很有意思的反作用出现了。在毛时代的中国,一切
“资产阶级”行为都是避讳的。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的形像都是反面教
材,而且描绘得很清楚、很新鲜生动的:住大楼,开快车,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八
十年代邓小平说“发财是光荣的”,到了九十年代有一部份人在中国的商业化社会
里头发了或大或小的财,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呢?似乎没有别的,只好参考毛所
骂的那种反面形像,只是现在由反面教材成了正面教材。好行为了。毛时代的极端
禁欲主义,物质需求积累久了,造成物极必反,现在晃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种放
肆主义。
可惜的是,毛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於简单的卡通漫画。实际上的西洋
资本主义多多少少受民主法制的制约。法律制约诚然不是最完善的,时时刻刻需要
公民投票者的监督;但现代的西洋资本家,哪怕是野心最大的、最不择手段的人,
也很难像毛所骂的那样轻易剥削,放肆欺骗,无恶不作。要是一部分中国人,从毛
那里得到的印像是这种行为应该是发了财的人的自然行为,那恐怕也得算是文化大
革命的一个相当大的反作用。
反作用的产生不限於文革。大跃进也是一个例子。中国自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追
求国家富强,大跃进的目标也是“超英赶美”,但在经济上的实际效果却是相反的
,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
的一次饥荒。与大跃进同时,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同样是为了中国更富强
的目标,鼓励中国人口尽快增长,把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教授骂为“资产阶级思
想家马尔萨斯的信徒”。後来,到了八十年代,仍旧是为了中国更为富强的目标,
政府宣称“独生一子”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应该视为毛的五十年代末政策的反作用
结果。
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里起反作用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德
国、日本、苏联、罗马尼亚、伊朗、伊拉克、乌干达和其它国家的现代历史上都可
以找到的极权主义导致反作用的例子。闯祸的方式有时候是打侵略战争,有时侯是
国内搞斗人运动,但所有的例子都有两个共同之处:(1)指挥的人都是自称最正确的
极权主义者。(2)遭殃的人都是服从,甚至“全心全意服务”的老百姓。正相反呢,
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上,很难发现在国内搞过斗人运动的例子。侵略战争和庞大
社会运动的出发点都是极权主义者自己的蓝图。他们很相信他们的蓝图,以为别人
不相信是因为别人的水平不够。他们势力那么大,有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
殊不知社会生活是复杂多端的,并不是一部汽车,你想把它开到那里就可以开到那
里。
民主政治不是没有毛病的,但它的基本性质是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民主政府的领
袖知道为所欲为是做不到的,颁布自己的伟大蓝图是没有用的。伟大蓝图因为用不
上,所以也自然起不了一贯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