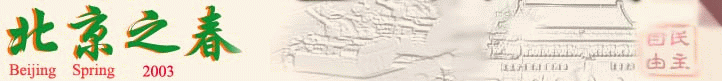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二十六)
胡平
241、大串连
元旦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
的影响的一年”。可是,怎么批判,怎么清除呢?此时的十九中,校园内一片冷清
,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外出串连去了。
全国性的大串连始于六六年九月。当时,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
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那正是“对联”横行一世之时,十九中派出的
赴京代表,清一色都是出身纯正的红卫兵。高三(二)班有四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
,其中还有两个是黑五类,未经校文革批准,自行搭上了北上的列车。校文革闻讯
大怒,在会上对这四位同学点名批判,扬言要对之严加追惩。不料形势很快就急转
直下,还没等这四位同学返回学校,校文革自己倒先垮了。
其实,早在六六年六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各地学生要来北京,应
该欢迎,应该免费。还在八月上旬,就有少量外地学生赴京上访,反映本地区本单
位的运动情况,受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的接待。不过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情况并不
知晓。八一八毛泽东首次检阅文革大军,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外地的师生代表;我们不
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北京,我们祗是想当然地以
为他们一定是最出色的积极份子。那时侯,人们都把上北京见毛主席视为一种特殊
的荣誉。四川大学一位姓杨的学生,在八一八大会上,以西南地区革命师生代表的
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回来后顿时身价百倍。他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西南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的组织,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看那架势,俨然是全西南红卫
兵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也许是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这个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很
快就被其它更具草根性的组织比了下去。另一条可以想象的原因是,到后来,人人
都有资格上北京见毛主席,物不稀则不贵,杨司令的威望自然也就低落了。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热爱北京热爱毛主席。记得在小学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库
尔班.土鲁木见到了毛主席》,讲的是一位新疆老汉日夜思念伟大领袖,骑着毛驴上
北京,上级领导得知此事,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和毛主席见了面。我在上小学一
年级那年从北京转学到成都,同学们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无不对我另眼看待,个
个都很好奇,常常围着我问长问短,流露出十分羡慕的神情。在过去,祗有英雄模
范和先进人物才有机会上北京见毛主席;因此,一般人都把上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当
作一个美好的梦想,很少以为那还会有实现的时候。直到中央发出串连的通知之前
,我都没发现周围有谁认真动过上北京见毛主席的念头。
和其他许多学校一样,在十九中,第一批赴京人选是由校文革确定的。但很快地
同学们就发现,原来上北京并不需要什么人的批准,谁想去谁就可以去。本来上火
车要凭学校的介绍信,可是火车站人山人海,混乱不堪,没有介绍信照样可以挤进
车厢。再说,上北京见毛主席,这是何等堂皇何等革命的理由,难道还有人能反对
不成?祗有黑五类同学不敢轻举妄动。那时候,某些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红卫兵
战士见到陌生人,劈头一句就问你什么出身;倘若知道你是黑五类,很可能会把你轰
下去。事实上,就在这段时间,北京正在发起一场将地、富、反、坏份子赶出首都
的运动,许多子女也受到波及。黑五类出身的同学除非撒谎,隐瞒家庭成份,否则
很难混入赴京朝圣的行列。然而在当时,我们又都把隐瞒家庭成份视为莫大的政治
错误;即便在黑五类同学之中,这种行为也往往得不到谅解。于是,我们就老老实实
地留在学校。好在“对联”肆虐的日子不长,进入十一月,黑五类同学上北京也不
再有什么阻力。祗是到这时,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已经临近尾声。
242、 赴京朝圣
按照千千万万赴京朝圣者事后的描述,那经验大同小异:数倍超员的列车,重重
迭迭的乘客,忍饥挨饿尚在其次,最难受的是便急而上不成厕所;火车开开停停,运
行时间拉得很长。幸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去见毛主席,太兴奋了,
倒不觉得有多么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立刻被分送到远远近近的接待站,说是“
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吃住游览一律免费。到了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通常在头一天
才宣布),大家凌晨就起身,潮水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涌去;等到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
天安门城楼之上,人群便拼命地向城楼下挤,无数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
赶快掏出小红书或日记本写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
席,这是我一生最最幸福的时刻!”
据说,毛泽东曾经讲,在苏联,革命的精神没能很好地传下去,是因为亲眼见过
列宁的人太少。看来,毛泽东对领袖接见群众所产生的力量抱有很高的期望。应该
承认毛泽东的期望并没有完全落空。许多参加过接见的人都表示他们从接见中获得
了极大的鼓舞。在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祗觉得自
己的一切都属于伟大领袖,下决心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在所
不辞。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表现出的高度狂热,显然和毛泽东的八次接见大有关系。
再加上巨大的集体场面的磁场效应,个人身处其中,很容易产生小我消失,溶于大
我的感觉。和以往的五一、十一庆祝大会不同,在这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上,秩序都有些混乱,特别是在毛主席出场后,大家都拼命朝前挤,口号声也乱成
一片。然而正是这种混乱,突显出群众的自发性,加强了周围人们的情绪对你的感
染力,从而把大家的热情都推向了最高峰。
亚里士多德指出,僭主常常要人民集合于公共场所,汇集于宫门之前,使人民习
惯于谦卑顺从的风尚,并显示僭主的赫赫威势。如果一个人心怀异志,见到群众欢
欣若狂,山呼万岁的场景,很难不产生孤独与恐惧之感;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人
们的谦卑与顺从。
不过,我们也不应夸大接见仪式的效果。群众太多,广场太大,城楼太高,很多
人根本看不清毛主席的面目,祗能望到一个小小的黑影,还不敢肯定是与不是;这如
何能让人激动得起来?先前的宣传对被接见的幸福感渲染得太浓烈,一旦身临其境
,不少人发现自己的激情并不象预期的那么强,反倒觉得有几分失望。再有,人们
之所以把见毛主席视为莫大的荣耀,那显然和领袖历来深居简出,凡人极难见到有
关;接见的次数多了,反应也就弱了。一般来说,外地人比北京人把受接见看得更神
圣;头几批受接见者比后几批受接见者感受更强烈。头几批人在接见完毕后,赶快到
邮电局发信发电报,向学校、同学和亲友报告“特大喜讯”;后几批人在回来后甚至
对周围的人都少有讲述的兴趣。正如婚礼的隆重未必对婚姻的和谐长久有多大的帮
助,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所期望的那种革命精神并没有维持得很久,而参加过
接见的人和没参加过接见的人也没有表现出有多大的区别。
243、我没见过毛主席
我没有去北京。 起初是不准,后来是不肯。中央号召批判血统论,我十分振奋,
我希望认真彻底地肃清“对联”的流毒。要是大家都走了,那怎么行?再说,我对
上北京见毛主席似乎也没有太高的热情。我不觉得就那么远远地望上一眼有多大的
意义。这并不是说我对伟大领袖不够热爱;很可能,我对领袖的感情比许多人还更严
肃些。我祗是对这种表达崇敬的形式不大热衷而已。
从小学起,我们就参加各种名目的集会游行,例如庆祝五一十一,例如支援古巴
人民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等等。先前,我对参加这种活动很热心;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渐渐感到有些厌腻。我发现我在这种场合下有点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总是
无法和集体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周围的人群越是紧密,越是令我感到孤独;周围的
气氛越是一致,自己的心境越是游离。大约正是出于这种感觉,当我看到毛主席接
见红卫兵那种万头躜动群情热烈的场面,很少产生羡慕和向往的意思。
此外,我也不大体会得到那些见到毛主席的人所声称的“最最幸福”。如果你是
以先进人物的身份获得接见,那意味着你的优秀得到肯定,故而另当别论;如果你祗
是以普通群众的一份子见到领袖,而他根本没见到你,这“最最幸福”之感又是如
何生起的呢?我承认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幸福的,可是我看不出为什么亲眼见到毛
主席就会增加幸福的程度。也许,我这样讲太理性化了。倘若我当年参加了接见,
说不定也会有幸福之感--尤其是在强大的磁场效应下。不过,我仍然对“最最幸福
”的感觉存有几分疑心。我以为许多参加接见者并不曾感觉到“最最幸福”,他们
认为自己应该有那种感觉,于是他们也就以为自己已经感觉到那种感觉。
十九中动作迟缓,大部分同学没赶得上去北京见毛主席,事后并不见有多少人为
此感到特别遗憾特别后悔。这中间的情况自然多种多样,有些人和我类似,对领袖
很崇敬,但没有强烈的冲动非想见上一眼不可;有些人恐怕连崇敬之情都比较淡。我
们很可以推断,假如政府不是提供方便免费乘车包吃包住,赴京朝圣的人数一定会
减少大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极大地强化了青少年对自己的效忠热情,这一
史无前例的壮举,换一个角度看,那不是独裁者慷国家之慨而进行的一次空前的人
心大收买吗?
244、《只争朝夕》长征队
校园里既是空空荡荡,没什么事好做,我想,我们也去串连罢。这已经是六七年
的一月上旬,有风声说要停止串连,再不走也许就没机会了。我和另外九个同学组
成了一个步行长征队,队名是我取的,叫《只争朝夕》。 在大串
连的初期,通常有两种路向,一是外地学生上北京,一是北京学生去外地;以后才演
变成真正的全国大串连。每一座稍大一点的城市,每一处革命胜地,都成了串连者
的目标。各种客运工具--除了飞机--通通装满了学生,令交通部门不堪重负。就在
这时,中央发现有一批学生步行从大连到北京,赶快向全国推广,誉之为“革命创
举”。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连。我
们决定执行中央指示步行串连。考虑到所余时间不多,兼以对串连的兴致有限,我
们把重庆确定为此行的终点。 不言而喻,我们这个长征队,几乎全是黑五类。
其中有两人的母亲都是本校的老师,前阶段被打入牛棚;我为解放老师砸烂牛棚出过
力,所以他们对我颇有好感。经过半年多的运动,各班同学都陷入四分五裂。“对
联”以出身划线,尔后“对联”被否定,那根线却没有随之消失。不少黑五类愿意
向中间家庭的同学(四川人称为麻五类)靠拢,但我们宁肯自立门户;我们无意歧视别
人,我们只是不愿被别人歧视。
在准备步行串连的衣物时,我遇见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我没有棉衣。我的一
件还没穿过的新棉衣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妹妹所在班级的
一伙学生闯入我家抄家。说来也是,我在十九中被当作黑五类狗崽子的典型,可是
十九中的红卫兵却并没有去抄我的家(是否因为我家离学校太远了?)。我妹妹在离
家稍近一些的一所初级中学就读。初中生做起事来更胡闹。一伙半大不小的学生来
抄家,把凡是象样一点的东西全部抄走,包括我姐姐工作三年攒钱买下的一部美多
牌收音机,也包括我的新棉衣;还在大门口贴上一张批判我母亲的布告。冬天来了,
我祗得穿上旧的小棉袄御寒,如今要徒步行远路,小棉袄恐不济事。根据不久前发
布的一条政策,被抄家者可以领回一些生活必需品。我找到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
管理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当然,他们知道来者都是黑五类,大可不必客气。我反复
申说。最后她祗给了我三两件物品,倒是有一件棉衣,但显然不是我那件。临了,
她还指着墙上的一份中央文件警告说不准阶级敌人趁机搞翻案。这是在元旦社论发
表以后的事,我再一次感到歧视远远没有结束。
245、从成都到重庆
从成都到重庆,途经简阳、乐至、安岳、铜粱等县,我们步行用了一周的时间。
路上并不寂寞。一队十人,五男五女,来自六个班,还有一位同学的哥哥,是成
都近郊一所小学的老师,彼此间就有很多话可讲。文革以来,人们的生活圈子扩大
,人际交往增加,许多人都变得比以前大方了,男女界限也迅速地消失。过去,在
中学生中间,男女界限颇为分明,偶有接触稍多者,便可能引起一些人的议论讥笑
。那倒不是出于正统的卫道观念,因为官方一向提倡男女平等,提倡革命同志团结
友爱。在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之间,由于参加的共同活动较多,男女界限的观念一
般还要淡一些。这就是说,在那时,过份地讲究分男女界限是被当作落后思想、封
建思想而不受鼓励的;祗是这重思想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文化革命给这种思想造成了
很大的冲击。文化革命极大地强化了同志式关系。同志式关系不是反性的,同志式
关系是中性的、非性的、无性的;因此,它一方面有力地冲击了男女之大防的观念,
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抑制了异性之间的情欲。文革中,男女生间的交往大大增加;可是
,大多数人却真是“思无邪”。谈情说爱者自然也有,但为数甚少,尤其是在前两
年,而且常常是以同志式友谊为基础,无意中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余话,暂不多
提。
沿公路步行,不时能碰上其他的长征队,互相打个招呼,或是同行一段;在一起
食宿时.基本上都相处得很好,极少见到吵架打架的。这时候,出身歧视的恶浪已经
退潮,群众间的武斗派仗尚未开始;本班本校同学之间结下了恩恩怨怨视同陌路,和
外地外校的陌生者倒能相安无事,真好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
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偌大一场串连活动中,鼠窃狗偷、
强奸谋害之事甚少。一般的治安秩序,照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好得难以置信;但在当
时人们的心目中,这一切似乎又都很自然。十几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家远
行,还没有大人照应,作家长的免不了牵肠挂肚,不过很少有人耽心遇上歹徒强盗
。真可谓民风纯朴。然而与此同时,以“革命”之名而进行的暴力侵犯人身事件和
强夺他人财物事件则层出不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246、“长征是宣传队”
和许多长征队一样,我们也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长征的首要任务。动身前我们
就准备了许多传单,还带上了钢板蜡纸油印机,到了公共场所或人多之处就散发张
贴,到了接待站休息时就刻写印制。主要内容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其
他中央首长的讲话。这些宣传器具是临行时在学校领取的。干革命费钱但不花钱,
一切都有政府提供。 我们举着红旗往前走,正在路边地里干活的农民常常向我
们投来兴奋和好奇的目光。 有的农民高呼口号:“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
”我们赶快回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有时我们停下来,给农
民们读两段报。农民则最喜欢我们给他们演节目。这也是串连带来的风气之一。还
在六六年八月,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刚刚出现在外地城市时,他们就在街头空地上演
开了节目,不用化装,不用道具(顶多有一面红旗),连乐器都可有可无;通常是边唱
边跳,有新近发明的毛主席语录歌,有红卫兵自己谱写的“拿起笔作刀枪”,以及
其他一些革命歌曲;舞蹈很简单,无非是昂首挺胸挥拳跺脚。这种表演方式和表演内
容很快就被群起效仿,随着串连之风而普及城乡。不少长征队都能演上几下子。我
们队的同学大都不善表演,但有两位女生歌唱得很好--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成都市歌
舞团最出色的女高音。每逢这种场合,她俩就站出来为大家唱几曲,不是唱语录歌
,也不是唱造反歌,而是唱一些比较优雅点的革命歌曲,例如《东方红》里的几首
歌,例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赢得周围一片掌声。
说起语录歌,记得广播里初次播出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时,我听起来很别扭
,觉得象和尚念经。许多同学也有同感。我想,语录怎么能编成歌唱呢?可是,广
播里天天重复地播放,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听的次数多了,居然也渐渐地顺耳了。
有的歌因好听而流行,有的歌因流行而终于显得有些好听。语录歌无疑属于后一种
。专制用强力把它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我们,时间一长,我们习惯了,熟悉了,由于
熟悉而生出几分亲切;到后来,我们在理智上已然将之彻底否定,但那份亲切感却还
存留着一些,这反过来又可能动摇我们的理性判断,让你怀疑其中是否还有些值得
肯定的东西。
关于红卫兵的造反歌舞,粗糙固然粗糙,可是它别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能很快地
把观众带入情绪。演员没有特殊的打扮,演出没有专门的舞台,和观众没有距离,
更容易激起观众的参与感。红卫兵不把表演当作表演而是当作宣传鼓动,故而其简
单粗糙不构成弱点反而成了它的长处。不少人祗把演出当作革命激情的直接宣泄,
所以有些往日不喜欢唱歌跳舞的人倒对它上了劲。红卫兵的歌舞火药味十足,还经
常夹杂几句粗话。在过去的舞台上,祗有反派人物才讲粗话;如今,从十几岁的男女
学生之口,讲出“老子”,讲出“滚你妈的蛋”,那不仅表现出桀傲不驯,更表现
出十足的霸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演是在红八月的下旬,那正是“老子反动儿混
蛋”的口号开始在成都流传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和过去看一出你不喜欢
不赞成的艺术表演很不一样,因为它具有一种直接的力量。后来,造反派接过了这
种表演风格,在内容上则作出相应的改变,我发现我依然很难对它抱一种有距离的
观赏态度。再到以后,有的群众组织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大型
歌舞剧(例如川大八二六创作演出《四川很有希望》),重新回到舞台,艺术上变得
更讲究,可观赏性提高了很多,但与此同时,早期红卫兵表演的那种直接的力量感
和参与感也就削弱了。
247、 接待站见闻
沿着公路往前走,每隔三四十里便有一处接待站。接待站常常设在学校里,本校
的学生大都出外串连去了,正好腾出地方接待外地的学生。在接待站吃饭要交粮票
和少许的钱,住宿是免费的。当然,住宿条件很简陋,无非是在地上垫上干草,摆
成大通铺;我们随身背着被盖卷,打开铺上就是。那时大家都以吃苦为荣,很少有人
抱怨。但也有一些好事之徒,贴出大字报批评接待人员态度恶劣(不是批评条件恶劣
)。不知是谁最先发明把接待站讥为刁难站,此后,“刁难站”一词便流行天下。我
没见有哪家接待站没被批上“刁难站”这三个字的。这让我很不以为然。过去我们
下厂下乡参观劳动,离别时总要给人家留下一封感谢信,虽每每流于形式且言过其
实,但至少表示一种礼貌。如今的接待站,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不速之客,工作异
常辛苦;做客人的不道谢也就算了,怎么还要粗暴地指责讥讽?再说,眼下正是学生
最受宠的时候,其他人等见了无不退避三舍;来往同学个个都算革命小将,又是成群
结伙,我就不信有几个接待人员还敢刁难。我看是那帮学生成心找碴,有的根本就
是闹着开心。四川有句话,叫“人不宜好,狗不宜饱”。总有这么一种人,越是受
抬举,越是不讲理。在文革的大风暴中,这祗能算是小事一桩,不过它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长征路上颇多见闻。从城镇到乡村,到处都是语录牌、主席象和
大标语,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听人们讲话,满嘴革命术语。有天中午,我们
赶到一处接待站吃午饭,见一位中年农村妇女---看上去并非什么领导干部--在就餐
的同学之间走来走去,口中滔滔不绝;她把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文章句子东一段西一
段地串在一起,一口气讲上二三十分钟不打结巴。过去我们就听说有些没什么文化
的普通农民,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能成篇成段地背诵许多毛主席的文章和
语录;果然眼前就有一个榜样。看来,这位妇女大概经常到这里发表演说。我们自然
很佩服,但暗中又觉得有些滑稽。
在抵达重庆的前一天, 我们参观了歌乐山上的渣滓洞监狱。同学们都读过《在烈
火中永生》和《红岩》,对当年革命先辈在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无不耳熟能详,十
分敬仰。这两本书的作者之一罗广彬,现在是重庆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立派有人
指其为叛徒;就在我们到达重庆的几天之后,罗广彬跳楼自杀,到处张贴着现场拍摄
的照片,脑袋裂开,一只眼还睁着。由于多年的教育,本来在我们心目中,中共地
下党员的形象是极其高大的;文革发生后,事情变得复杂了。先是见到一些自称老地
下党员者写的大字报,揭发控诉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主要由南下干部所组成)对他们
打击迫害,原来这批老地下党员“解放”后的遭遇一直很悲惨;其后又是揪叛徒,似
乎那些身居高位的原地下党员个个都曾自首变节过,洗不清叛徒的嫌疑。这样一来
,活着的地下党员就没有几个不倒楣的了。当我看到罗广彬跳楼自杀的照片,想到
几天前我们刚满怀崇敬地参观渣滓洞,真有一种说不清的困惑和感慨。
248、 造反派爆发内战
我们到达重庆时,重庆的造反派正为夺权一事而爆发了内战。 六七年一
月初,上海造反派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紧接着,《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手中夺权”。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响应,兴起一阵夺权之风,报上把它叫做一
月风暴。在重庆,以重大八一五为首,联合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宣布夺了重庆市
委的权,成立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得到重庆市警备司令部(54军)的支
持。可是,另有一批造反派不肯承认市革筹,将之称为大杂烩,扬言要彻底砸烂。
于是,重庆的造反派公开分裂。一派叫八一五派,另一派叫砸派。后来,砸派大概
是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改称反到底派。围绕着对市革筹的不同态度,两派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
我们落脚的接待站在重庆市中区,不远就是解放碑广场,那里是大字报最集中的
地方。每日从黄昏时分起,广场上便开始出现一堆一堆的人群,打听消息或是交换
意见。我们常常到那里去看去听。当时,我对八一五与反倒底两派之争并不重视。
我更关心的还是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和北京动态,偶尔读几篇两派争论的文章,觉
得好象各有各的道理。八一五派主张联合,反对分裂,看来是正确的;反倒底派坚持
原则,反对凑合,似乎也不为错。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倾向于反倒底派。我们旁听
了一场重大八一五对三司联络站的公开辩论。应该说,那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一场
最好的辩论:双方唇枪舌箭,但并不辱骂对手,听众也很文明,无人起哄闹场。毕
竟,大家都承认这是革命派内部的争论,彼此还想着如何说服对方,争取游离的群
众;分歧刚刚公开化,感情上还没有太对立。祗是一场辩论听下来,我依然不得要领
,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接待站和首都三司的同学有些接触,还结识了一位
清华井冈山的成都老乡。那时,我们对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尤其是对首都三司颇有
几分崇敬,因此我们本是希望他们辩赢的;看到辩论的结果不清不楚,未免感到遗憾
。不过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不觉得这事和我们有多大的相干。
249、一月风暴
由夺权引起的混乱看来是很难避免的。问题不仅在于夺谁的权,还在于谁去夺,
如何夺,谁认可,如何认可。以前讲夺权--譬如电影《夺印》,无非是上级下令,
撤掉某人的职务,再派去另外的人接任。也有少数夺权采取了选举的方式,譬如在
高二那年我班团支部改选,红五类夺了麻五类的权;当然,这次选举祗是徒有形式,
因为上级的意图很明确,普通团员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可是,一月风暴中的夺权
完全打破常规,因此不能不导致一片混乱。
首先,夺谁的权?夺走资派的权。谁算走资派?更准确地说,谁有权确定谁是走
资派?若依中央依上级党委,那么,到目前为止,被明令撤职停职的当权派没有几
个;若依造反派群众,那简直是“洪洞县内无好人”。据王力在回忆录中所写,当时
周恩来曾经讲过:“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
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
判断。”平心而论,这大概是当时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凡是夺了权的地方
,人们也正是这么做的。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这段讲话在那时并不曾公布,也
不曾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市面上流传。中央发出夺权号召之初,我和很多人一样弄
不大明白,不知谁的权该夺谁的不该夺;虽说前阶段造反,几乎每个当权派都被扣上
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但我们也知道那还不等于最后定性。不过各地都有一批革命闯
将,从不象我辈那样思前想后,祗要看到别处有人做了一件事而受到中央支持,他
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在自己这里照着做起来,结果倒总是和中央的考虑部署不谋而合
。谁要是一板一眼地按报上说的去做,一定要仔细分辨严格认定之后才采取夺权行
动,他势必就落后了。 夺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谁夺权,谁有夺权的资格?答曰“无
产阶级革命派”。照一般人的理解,这首先是指造反派。然而,造反派的组织很多
.彼此间在观点上、背景上和亲疏关系上均有所不同,因此很难达成必要的共识,免
不了会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以及联合一伙,排斥一伙的情况发生。再者,夺权需
要有相当级别的干部参与,而在评价干部的问题上,造反派的意见最难一致。关键
在于,中央发出了夺权的号令,但没有规定夺权的程序;一旦有了矛盾却没有解决矛
盾的办法, 事情怎么能不乱套?
250、夺权斗争陷入困境
一月风暴来势迅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
和山东等地宣告夺权成功,消息刊登于《人民日报》,表明中央予以认可。然而接
下来情况就不顺利了。许多省市都象重庆一样,围绕着夺权斗争而爆发了群众组织
之间的分裂与内战,致使革委会无法组建,就算组建成了,由于无法赢得反对派的
认同, 中央也不敢轻易认可。从六七年三月到十二月这十个月的时间里,祗增添了
三个革委会(北京、青海和天津)。夺权斗争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在省市一级革委会无从确立的前提下,基层单位要成立革委会,因为得不到上级
革委会的认可,故而也难以确立。就在我们外出串连的时候,十九中也发生过一起
夺权的插曲。那简直是出轻喜剧。几个同学找到校长秘书,要她交出学校的大印,
对方立刻照办,夺权一举成功。可是同学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夺权和不夺权没有
什么区别,上面没人认可,下面没人买帐。自工作组撤离,校文革挨批以来,十九
中早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校领导的大权不等别人来夺便已然自行消失;如今你把这块
已经没有权威的大印再捡起来又有何用?印把子是权力的象征但并非权力本身。假
如一伙人在先前未能建立起普遍的权威,又不具有实行自己意志的强制力量,同时
又没有经过一种公认的程序而获得合法的授权;那么,仅仅是抢来一块大印是不会有
什么意义的。于是,十九中的一月风暴就不了了之。
夺权斗争引出了一大堆麻烦。看来毛泽东事先对这些麻烦有些估计不足。在揪斗
走资派,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各级党组织瘫痪,地方权力机构处于真空状态,新权
力的建立势在必行。可是,毛泽东不想沿袭旧的办法,他不想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打倒一批,再任命一批。不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他总希望文化革命
在表面上象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他希望见到群众自己起来联合夺权,建立起
更加革命化也就是更加忠于自己的权力机构;然后他再出面表示支持认可,从而显示
伟大领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料群众彼此之间却争
执不休,很难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另外,毛泽东又拒绝实行选举的办法。当张春桥
向毛泽东汇报上海夺权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了两条不同意见:一,毛泽东不赞成
用"上海公社”的名称,“都叫公社了,党往哪里摆?”可见,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
有要放弃党的意思,他知道他到头来还是要通过党来统治。二,毛泽东明确地讲:
“我就不相信选举。”倘若问,在过去,共产党不是也实行选举吗?例如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例如老百姓直接选举区人民代表。但是在那时
,党内矛盾没有公开化,举国上下祗有一个声音,选举等于不选举。文革中,两条
路线斗争公开化,群众中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这时候再搞选举,很可能会选出
不赞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那怎么成?象这样,一不要自上而下的任命,二不要
自下而上的选举,事情当然就很不好办了。毛泽东低估了这种困难,群众也低估了
这种困难。一月风暴引发了造反派的内战,可是我敢说,在当初,恐怕谁也没有料
想到这种内战竟然会演变为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流血局面。□(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