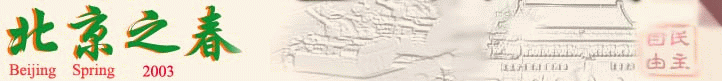以生命向专制挑战
——采访原《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
亚 衣
吴学灿,原《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八九民运期间因将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
上的重要讲话以《人民日报》号外的形式印刷出版而在六四之後被捕,当局以“反
革命宣传煽动罪”将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一九九三年九月被释放。日前,应哥伦
比亚大学邀请刚刚抵达美国访问的吴学灿先生在本刊编辑部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
童年:差一点饿死
亚:欢迎您来到美国。我想许多读者都会对您的平安到达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段
时间从国内传出来的不少消息实在使人担忧:刘念春遭受毒打,陈龙德被迫跳楼自
杀,王希哲申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没有被批准……。可不可以请您先将自己的经
历给我们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吴:好。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苏北农村。童年时代最深的记忆是我差一点饿死,母
亲那时得了浮肿病,而我最长的一次是连续有七天一粒米都没有下肚。一九六八年
三月,在我初中毕业後的两年。我穿上军装当了兵,当然从大道理来说,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实际上我主要是为了吃饭,因为我听
说当兵有饭吃,而且可以吃饱。从陆军到海军,我都很积极,得过奖,被评为五好
战士,一九七零年七月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尽的义务不算太少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复员,来到国务院出版口。当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从海军
调了四十个战士,到人民出版社“掺沙子”。我来到出版社後又立即被送入广州中
山大学读书,七五年毕业回到人民出版社。
亚:您当时在出版社做什么工作?
吴:因为我“根正苗壮”,品学兼优,一来到人民出版社就被分配到“要害部门”
的政治处工作。人民出版社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单位,在政治处的工作更没有意思。
我多次向领导提出要搞业务。一九七八年二月我离开政治处,来到经济编辑室当编
辑。那时整个社会潮流处在开放时期,西单出现了民主墙,有一次我还在墙报上批
了几句话,主张对毛泽东的余毒进行清算。在出版社里,我也经常发表各种“怪论
”,使得出版社的领导觉得很难办。
一九七九年:我成了共产党的“塌天派”
亚:这是不是您後来进入《人民日报》的原因?
吴:多年来,《人民日报》理论部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我对其中的许多人非常敬
佩,理论部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是我经常看的。我的思想的根本的转变发生
在一九七九年春天,那是在一批坚持思想解放运动的老前辈的影响下完成的。中共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党内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即那些老知识分子兼共产党员,
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编委兼理论部主任何匡,理论部
副主任汪子嵩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当时仔细阅读了他们在
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他们的文章的总的意图当然还是讨论怎
样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而我读了这些文章得出的结论却是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得中国兴旺发达。如果
说在理论务虚会以前我还是同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一样,是共产党制度的“补天派
”的话,那么此时的我就转变成一个“塌天派”了。这样,我在工作单位里的所谓
“自由化”言论也就更加多了,甚至主张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民出版社的领
导希望我能够调走,我自己也希望到思想比较解放的单位去工作。一九八零年十二
月我离开出版社,被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
亚:依照您刚才的介绍,您原来可以说是共产党中的一个优秀份子,但是在一九七
九年却变成了共产党的反叛者。对如此大跨度的转变,您是否可以作一些更详细的
说明?
吴:前面提到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是我永生难忘的。当思想解放
运动中人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所谓“不完善方面”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却是悲惨
与黑暗。在经常进行的“回忆对比”活动中,老年人忆的是所谓旧社会的苦,思的
是新社会的甜,而我回忆的痛苦却完全是“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好,一天三顿
吃不饱”——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党给我带来的是饥饿和痛苦,而且不只是给
少数人带来这种苦难。也许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无法的经历,使得我在对社会主义
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理论上的思索时,对它们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记得一九
九一年五月我在秦城监狱中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话:“少年倾听谎言,青春狂
呼口号;二十八年梦里飘,醒来怒火中烧。”从我出生到一九七九年我在思想上的
清醒,正好二十八年。这首诗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此以後,我就把埋葬共产主义作
为自己的生活目标。
亚:您到了《人民日报》,是否如鱼得水?
吴:不然。我刚到报社就觉得没有事情可做。因为我到《人民日报》报到的第二天
,副总编辑安岗正在报社传达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第一把手中有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人民日报》。黑龙江
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带头指责说“《人民日报》带领群众造共产党的反”,其他一
些省委书记附和呼应,说他们在下面没有办法干了,要求中央对《人民日报》在组
织上予以调整,思想上加以整顿。但是因为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一直比较
支持,他说思想整顿可以,组织人事就不调整了。
亚:整顿的结果如何?
吴:不了了之,这是中共许多运动的结局。但是,本来可以发表的说真话比较多的
文章不能发表了,在报社内部,有的话也不能说了。一九八三年又搞什么“清除精
神污染”运动,我“顽固地”站在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一边,为他们的人道主义和
异化理论辩护。我在报社里说,社会主义不搞人道主义,难道要“兽道主义”,“
鬼道主义”?我认为提倡人道主义就是对抗共产党的兽道主义的。还有异化,在中国
,人民名义上当家作主,实际上受尽奴役和苦难,这不就是异化?
亚:据说您後来担任过《青年论坛》驻北京记者站的记者?
吴:清除精神污染之後,湖北《青年论坛》创刊,他们通过远志明找到了我,我就
请王若水给杂志写文章,这是王若水在“清楚精神污染”之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
章,题目是“智慧的痛苦”。我也担任了记者站的记者,记者站一共有五个人,包
括远志明。这一年,胡绩伟为了培养思想解放的新闻干部,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新闻系合办了两年制的在职干部的研究生班。我通过考试後被录取,读了两年。八
五年毕业之後就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从事港台侨乡的报道。
震惊中外的《人民日报》号外事件
亚:在八九民运中,《人民日报》号外事件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的一件事情,您是
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者,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吴:按照我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思想发展,八九年我参与民运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像
报社的大部分记者编辑一样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只是普通的一员。到五月二十日
,就是实施戒严的第一天。报社里有人拿到一份《北大传单》,内容是赵紫阳在五
月十六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正准备印刷。我那天做值班编辑,当然就
参与了这件事。在考虑以什么方式印制这些内容时,我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决定印
《人民日报》号外,而不是一般的传单。当时印刷厂的工人问有没有批件,我说去
请示了,我还自己动手在铅字架上找大号字。当时印了几百份,我画了一张图,派
人外出散发。後来印刷厂副厂长来了,说没有批文不能印,把余下的收了起来,但
我们预先藏了一些,当天下午游行时带出去散发。
亚: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八九民运的资料中,没有关於《人民日报》号外的直接记
载,您是否保留着号外的原件?还记得赵紫阳讲话的主要内容吗?
吴:也许是当时的印发量太少,许多中外记者都和我说过他们没有见到过号外,但
是我保留着一份复印件。我记得赵紫阳讲话的主要内容大约有五条,第一是否定四
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第二条是说由他本人承担发表社论的责任,第三是
说要顺应民意,反官倒,反腐败,由人大设立审查高干子弟、审查官倒的机构,赵
紫阳说还可以从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开刀,第四,公布全国副部长以上干部的行为背
景,第五,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权等等。讲话的内容我们是从
北大印制的传单中得来的,我们在《人民日报》的号外上也注明了转载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认为党报记者应该把党的总书记的讲话及时告诉大众,这是记者应该做的
事情,不存在有什么错误的问题;但是我对於事情的後果是有所预料的,在印完号
外回到办公室时,我跟办公室的同事们说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
亚:您是什么时侯被捕的?
吴:顺便说一下,《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发表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其中说到在
北京戒严之後,在游行队伍中就少见了我的身影。这不符合事实。五月二十九日王
若水回到北京之後,我还和他们夫妇两人一起参加游行,在六月二日、三日我也在
广场。六四凌晨我回到家中,妻子在哭,原来她以为我被打死了。我是五日下午离
开北京的,当时报社的同事对我说还是离开的好,否则被乱兵乱枪打死也说不清楚
。於是我就离开北京,南下武汉,转道重庆,再到海南。十二月十七日我在海南三
亚被抓住,在海南第一监狱呆了六天,又在广州监狱关了一个晚上。八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被押回北京。在车站我对送报社保卫人员来的报社司机作了一个杀头的手
势。我被直接押送到秦城监狱。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因为病重转到北京监狱
。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奥运举办城市的前一个星期,我被释
放出来,同时被释放的还有魏京生、翟伟民等人。
亚:那时当局是以什么罪名起诉和判处您的徒刑的?
吴: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法庭上,一个检察员在起诉书中说我“盗用《人
民日报》的名义印刷号外”,我当时就说,“你现在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在这里说
话”。他觉得奇怪,说检察院的人怎么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说
《人民日报》的人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话可说,停了好一会,继续念他
的起诉书。後来在判决书上这一段话改成吴学灿“擅自”煽动、组织工人印刷所谓
《人民日报》号外”。这还差不多。按照制度,要总编辑或者值班的副总编辑签字
才可以印刷报纸,我当然不是总编辑,这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情况下的行动,是在
危机情况下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作的一件事情。
亚:按照您现在的认识,您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怎样?
吴: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按照中共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来看,我也是对的。
我受审时在法庭上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党的总书记是党章上规定的党的最高负责人
,而中共又是宪法规定的领导力量,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和声明当然在法理上有效力
,而邓小平在法理上并不是最高的领导者。我把赵紫阳这个合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指示印成文字传播,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无论从国家
宪法还是中共党章来说,都是做得对的,我是在模范地按照宪法和党章做应该做的
事情,是一个优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共产党员。法庭没有理由宣判我犯罪。
亚:那么,赵紫阳的五点声明的真实性是否得到证实?
吴:我在法庭上也郑重地提到了这一点。我在“最後陈述”中要求法庭传赵紫阳出
庭作证。因为赵紫阳是本案最主要的证人,法庭应当传赵紫阳作证。如果我在号外
中提供的消息是假的,我愿意承担造谣的法律责任;如果这内容是真的,那么我就
是在传达总书记的指示,我就是在按照党章和宪法的程序办事,我就是一个优秀的
共产党员和出类拔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庭判处我有罪是违反宪法,如果法
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就是违反党章。
亚:您在监狱中的情况如何
吴:中共一贯的做法是利用监狱中的管理干部来整犯人,在犯人中间挑拨离间,让
犯人自相残杀。他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面前把参加民运的一般市民称为“暴徒”、
“痞子”、“流氓”,说学生、知识分子是“文化人”,和这些暴徒不同;在市民
们面前又说“文化人”在运动中可以得到好处,有名有利,而市民们却什么也没有
得到。
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
亚:释放之後您的处境怎样?
吴:魏京生被放出来之後被当局限制活动,与外界隔绝,所以新闻界就涌到我这里
来了,先是法新社记者白维采访我,後来加拿大电视台,美国ABC电视台,香港的有
线电视、无线电视、商业电台,《明报》、《联合报》、《快报》、《天天日报》
等纷至沓来。
亚:记者们对您提出了什么问题?
吴:第一个问题,千篇一律都是关於奥运会的。第二是反腐败问题。当时大陆正在
抓新闻界的“有偿新闻”问题。我对记者们说,腐败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在这样
腐败的制度下,要工作就会腐败,腐败是正常的,而不腐败倒反而不正常。我的理
解是在合法的收入之外的收入,利用权力取得好处就是腐败。比如记者写新闻是自
己的权利和权力,但是《人民日报》当时规定的记者的差旅费是平均每人每年十二
元,住房规定一天不超过十元。而我们采访南方侨乡,路那么远,所以记者去采访
必须要由被采访者包记者的吃、住开销和来回飞机票,否则无法采访。这样,良心
好一点的记者写得尽可能实在一些,良心不好的记者就会笔下生花,乱吹一通。
亚:说起记者的采访活动,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有哪些采访经历?
吴:主要是对南方侨乡的报导。记者的现实经验告诉我,改革就是把社会主义的东
西改掉,开放就是向资本主义开放。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比较来说,
中国大陆不如台湾香港,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内地不如沿海城
乡,就是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还是比社会主义优越。在海外版,我主要是借歌颂改革
开放的机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写的文章中没有一个
字说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样的记录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中也是少见的吧。
亚:听说您还有一段经商的经历?
吴:我曾经在外地朋友在北京开的公司里干了几天,因为当局经常骚扰,所以我干
不下去了。後来在家里看稿子,解决基本生活费。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劣等民族
亚:就您的观察,在六四之前和六四之後,国内的民运力量有什么变化?
吴:经历了八九年这样一场波澜壮阔、前无古人也许是後无来者的运动,不管是共
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大家实际上都已经知道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是日益消
亡的东西了。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後,认识了不少原来不熟悉的有识之士,包括魏京
生、许良英、丁子霖、王丹、陈子明等等。我的立场是,不管你原来是什么背景,
只要你认同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我们就可以一起对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进行消
解和削弱,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民运朋友比以前多了。现在国内民运人士团结得比
较好,比如一九九五年普遍的呼吁书运动,对国内民众是很大的鼓舞。特别是许良
英、丁子霖、魏京生和王丹、陈子明等等优秀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先生和我说
过几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中华民族绝
对不是一个劣等民族,我坚信这一点。
亚:您是否认为在六四镇压之後,中国民众的争取民主的追求并没有削弱?
吴:可以这样说,不过,有些人囿於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大部份民众又不得不考虑
到自己的生活,所以在表现的形式上面就不那么简单。民众的觉悟是大大提高了,
尤其是中下层干部,都对共产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当权
者在没有自信时也会更加疯狂。在统治者的疯狂面前,老百姓又难免会恐惧。我一
直在想,究竟是专制制度的残酷造成了国民性的软弱,还是国民性的软弱加剧了专
制制度的残酷,我不得而知。也许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亚:那么,中国老百姓在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上是比以往更软弱了,还是相反?
吴: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当权者想用疯狂镇压来换取老百姓的恐惧,
把恐惧当做拥护来自我安慰。最近他们把刘念春折磨得不成样子,刘念春的妻子储
海兰从齐齐哈尔探望刘念春之後回来泣不成声对我说,刘念春被他们折磨得不成人
样了,你有机会出去,就走吧。
只要目标一致,不管体制内外
亚:八九民运过去已经多年,在海外,在国内,对这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战略和策
略上也有不少反思、研究和检讨性的文字。我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吴:有人说是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造成了政府的镇压,这是颠倒因果的说法。事实
上是政府蛮不讲理,根本无视民众的任何要求造成了步步升级的巨大危机。其实只
要中共领导人做到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当年周恩来总理的作风,在八九风波时期中到
老百姓中来一下,哪怕作秀也可以,事情就好办得多。但是李鹏、邓小平他们连这
一点也作不到,既害怕又残暴。民运力量要不要检讨?当然要检讨。但是事情的主要
责任在政府方面,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一党统治的专制体制
消灭了任何反对党存在的条件。八九民运中在反对政府的群众方面并没有组织和指
挥,而有组织和指挥的只有政府和军队,所以民众在被激怒之後失去理智的行为也
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老百姓作为一个没有组织的力量,没有权利也就没有责任。
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正是共产党的极权制度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状
态,当社会危机和政治冲突发生时,找不到一种缓和、调解、谈判的途径或方式。
因而从整个社会体制来看,政府和执政党应当负担主要的责任。
吴:是的。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和解式的双赢。要么是政府镇压老百姓,要么像
以往农民起义杀掉皇帝一样,老百姓推翻政府。
亚:您是否了解在海外关於激进主义的争论,其中涉及到在中国大陆的今天是否要
进行合法斗争的问题,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吴:中国现在的宪法和法律虽然不能表达人民的意思,但是我仍然遵守;现在的法
律我不喜欢,我就提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作我要做的事情,说我想说的话
,推动宪法和法律的重订和修改。我不赞成在中国民主运动中采取武装的手段,因
为武装的方式不符合民主法制的目标,现代社会不能采用过去梁山好汉“反法制”
的办法来反对专制,中国人通过自相残杀的途径也不能建立民主社会。这是我的一
个观点。
第二,只要是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
,不要强求一律,做法可以五花八门,千奇百态,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可以
。我们当时就在体制内,利用体制内的一些有利条件进行反对体制的活动,也是一
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很多人在体制内还是这样做。我觉得在表达一种思想的时候,
不要去分什么体制内外。
共产党在和平演变中积聚私产
亚:根据您的观察,在现时的共产党内,有没有可能走和平演变的道路?
吴:和平演变早已开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和平演变,就是用资本主义来改社
会主义。
亚:既然共产党的和平演变早已经开始,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和平演变?
吴:这是一个政权的问题。邓小平的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既然不可逆转,那就把
社会主义变成他们的子孙作老板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东欧式的全民私有化的资本主
义。就是让共产党特权阶层的子孙後代(如陈云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人”)从部长、
中央委员变成总经理和董事长,把中华民族的几亿老百姓的血汗转变成他们子孙们
的私有财产。中国的私有化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现在已经开始第二轮,共产党设法把
国有企业的财产转移为“太子”、“太孙”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不是用现代资本主
义文明来发展社会生产从而使民众受益,而是千方百计积聚自己的私有财产,让老
百姓继续受苦受难。
亚:本刊不久前发表的一位大陆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也指出,改革的实质是在中国建
立官僚资本主义。您是否认为在中国现在的官僚私有化的进程与中国建立自由的市
场经济的方向还有某种一致的地方?
吴:我与大陆的一些前辈学者谈论过这些问题,他们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
是後封建社会,是现代化的封建专制。共产党现在的私有化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
原始积累不一样。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不可避免的血腥,那么在现代共产
党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却选择了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更加卑鄙下流丑恶的道路,
造成中华民族道德沦丧,其後果无法估量,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的自相残杀。在民
众极端不满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人起来与太子太孙们拼个死活,这种可能我并不排
除。
亚: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或者私有化的过程中,老百姓
也得到了一些益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一种认为在官僚的掠夺中,人民生活就是
一种下降的趋势。您认为哪一种判断更加准确一些?
吴: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在工商、税务、邮政、电讯这些垄断性行业中工作的人
生活比较好,例如在电讯局的,百姓要装电话,必须买它们出的电话机,不买就不
让装电话,这些单位的人不是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高收入。而真正老实巴交的
又没有其他路子好走的人,生活水平在下降。但是这些人在整个社会中占有多大的
比例?由於中共的资讯的封锁,我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我不同意民众生活在上升,
社会矛盾不激烈的这种看法。问题还是在於统治者太残酷,使得老百姓连表达不满
的机会都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毕竟是少数,布鲁诺在西方也是少数
。我不赞成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说法,实际上敢於以生命向专制挑战的人物在任
何一个民族中都是少数。正因为共产党太残酷,所以我赞成用累积和渐进的方法推
进中国民运。
亚:顺便问一下,国内的民众对南朝鲜最近审判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太愚有什么
评论?
吴:我在秦城监狱时就说过,将来李鹏、陈希同、李锡铭会到秦城监狱中来。现在
陈希同去坐了,将来李鹏也一定要去。老百姓的普遍反映是“不要看他们今天跳得
欢,将来就要拉清单”。总有一天要算帐的。有些比较明智一些的干部子弟也知道
这一点,认为不要搞得太过分,将来激起民变时自己可以有一条後路。我不希望中
华民族将来有那种暴力清算的悲剧出现,但是我还是想奉劝中共权贵子弟在盗窃国
库时不要做的太过分,不能只管今天享受,哪管祸及子孙。
我的四项基本原则: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亚:您的妻子曾经作过您在法庭上的辩护人,容我冒昧,您可以说一说您家中的情
况吗?
吴:我的妻子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我深感内疚的是家中妻子、孩子为我受了苦。我
希望他们不要再受到株连。公安局的人曾经对我的邻居说,说是不株连了,但谁能
保得住呢?吴学灿个人坐牢,老婆孩子工作上学难道一点也不受影响吗?难说!这是一
种明显的威胁。
亚:您这次出来作访问学者,有什么学术上的打算?
吴: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进出国家的自由。早在九四年,安全部
的人就让我的朋友动员我出国,我没有答应。他们就变本加厉对我跟踪、盯梢、传
讯,甚至在我家大门口一天三班坐了一个月。我这次自愿出国,主要想实地了解考
察现代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
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这些缺点。
亚:在政治理念上有什么变动?
吴:我没有参加民运组织的打算,但是我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不会改变。我的四项基
本原则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在这里,我想借《北京之春》向海外的民运朋
友说几句话。既然大家认定了自由民主的目标,那么就应当容许别人在共同理念的
引导下采取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做法不要像共产党处理党内斗争的方式对待民运队
伍内部的分歧。我对详细情况不清楚,只是提一点希望。
亚: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预祝您在美国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