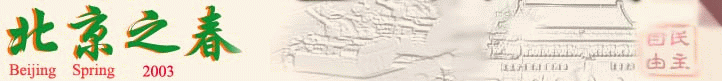多元化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
——访著名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
亚 衣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先後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开
设过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等课程,撰写和出版了关於中国文化和社会政治
的大量中、英文学术论著。林培瑞教授具有娴熟地驾驭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同
时怀有热切地喜爱中国文化,关怀中国民众疾苦之心。不久前,在碎金般的秋阳洒
向新泽西州大地的一个晴日,记者拜访了林培瑞教授,在悬挂着康有为的手迹和侯
宝林的条幅的客厅里,一起畅谈了许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学中文更具有挑战性
亚:最近您在本刊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有人甚至对一个美
国学者具有如此的汉语写作水平感到惊讶。请您将自己的经历,包括学习中国语文
的过程向我们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林:我是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小时候玩挖洞的游戏,一个小朋友说如果
不停地挖,把地球挖通,我们钻出来就到中国了。这是我对中国的最初的印象。直
到我十三岁那年,我才结识了第一个中国人。我从小就喜欢语言,中学时候学的是
法文,读得还算不错。到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法文似乎太简单了,想学一种更具
有挑战性的语言,就选择了中文。我大学读的专业是西方分析哲学。这种哲学认为
所有古典的哲学问题,关键都是在於对语言的分析,比如善与恶,真与假,以及知
识问题,只要在语言上搞清楚了,就不再是问题。由此出发,比较中国语言与西洋
语言的区别,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英文的“This is a table。”,法文是“Voi
ci la table。”,相差不多。但是在汉语里,“这是桌子”,就大不一样。中文里
的“桌子”,既不是单数也不是复数,很像是柏拉图那儿的抽象的东西。“桌子”
要个别化就必须加上数词和量词,“一张桌子”。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概念上
,在结构上与英文、法文就有区别。所以我想,学习中文对我研究语言也许是增加
了一个角度。我先在大学里念了两年中文,後来又读了一个暑期班。一九六六年,
也就是“文革”爆发的一年,我大学毕业,到香港去住了一年。这一年使得我的中
文大有提高,尤其是口语进步很大,对中国的情况也更加了解。本来我的计划是继
续读西方哲学,也已经申请进哲学研究所;从香港回来後,我改读中国历史。到现
在为止,我研究中文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亚:您对中国语言艺术有相当深的造诣,还写过关於相声的论著,我想顺便请教一
下,中国的相声与美国的“TALK SHOW”有什么异同?
林:笑话与语言的关系太密切了,因此我也玩过中国的相声。在美国的“talk sho
w”节目中,主持人在电视上说笑话,常常是说了一个就换一个,一个笑话接一个笑
话,保持新鲜;而中国相声却是在节目中慢慢积累,制造一种滑稽的气氛,不是马
上把那个关键的东西,那个叫……(亚:叫“包袱”)对,不是马上把“包袱”给抖
出来,而是让你慢慢体会。例如侯宝林的一个相声段子,因为方言的隔阂,北方人
到上海,把上海人说“汰(音“DA”)头”(就是北方人说的“洗头”),误以为是“
打头”,上海理发师问“汰一汰”好不好,北方顾客心想,为什么理发还要“打我
一顿”,就问理发师是不是“所有的顾客都打,还是只打我一个”?回答是“统统全
汰”。顾客想那就不破坏规矩,“打就打吧”。後来理好发,洗好头,再照镜子,
顾客问“怎么还不打我”?理发师说“汰过了”,“那我怎么一点也不疼”?顾客又
问。就这样,多少笑话,都是围绕“汰”与“打”的误会进行的。美国人在电视节
目中调侃柯林顿或者杜尔,往往拿当天发生的事情作笑料,常常是隔一天就不新鲜
,笑不起来了,而中国相声的有些段子,可以说是百听不厌。
人类共同本性比文化差异更重要
亚:根据您多年来的研究,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
林: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生活的道德表现,包括语言在内。做人要怎么做,比较
注重外界对自己道德上的评价。而美国人对自己是什么形象不那么敏感,只要自己
去生活就是了。在中国文化中则比较敏感,对行为的评价也是道德上的,“对不对
”,“好不好”。母亲骂孩子“不象话”,“不象样”,这种骂法在美国母亲那里
听不到。还有,如果有人评论说您讲话“讲得不错”,往往不是如同英文中所指的
,是说您讲的内容正确,而是说您讲话“表演”得不错,是指在讲话的内容之外的
那些东西。再有,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接触方面,中国与美国还有一个相反的现象。
这是我一九七九年到八零年间第一次到中国去长住时发现的。照理,中国是“社会
主义”,应当是很讲究公共道德的;美国是“资本主义”,是很重视私人关系的,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在广州的大街上看到一些人排队不排,踩了人家一脚也不说
一声对不起,不太讲究公共道德。而在美国,这些公共道德是比较讲究的。反过来
,在私人的接触方面,与中国人可以交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会很忠於你,很靠得住
;中国人知道朋友的做法不对时,为朋友的利益着想,会“劝”朋友应该如何去做
,在美国社会中则很难找到这样的好朋友。
亚:您在一篇谈论中国民主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类共同的本
性比文化上的差异更为重要。您可不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林:这正是我想继续说的,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看法就是,人到底还是人。美国人看
中国人,中国人看美国人,常常喜欢说两国的文化完全不一样。这种说法失之肤浅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人,都有父母、子女,对於母爱、父爱都会有很强的直觉,
失去亲人都会有深深的痛苦。一个人是自私还是慷慨,是诚实还是虚伪,与他是中
国人还是美国人无关。有一个社会学家不久前告诉我,人与大猩猩在基因上的差别
只有百分之二以下,更不要说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别如何之小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文化背景,是在什么样的国家中长大的,我想人性大概都是一样的。人们在讨论不
同文化的时候,常常会对不同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这很自然,但是不要在这个时候
忽略了大的相同的方面。
亚:从这里引申开来,您是不是觉得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家常常过於强调一个
国家或者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特殊性,从而抹杀了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方面,比
如在基本人权的保障上,在民主的社会结构上,在经济自由发展需要的环境上,他
们都喜欢强调中国特殊的“国情”,忽略了人类在这些问题上更加重要的普遍性方
面。
林:我不敢用“忽略”这两个字,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不是一种忽略,它可
能是明知其理,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不说。
反对官方的语言统治
亚:根据您的了解,仅仅就文化层面或者更狭义的语言层面来说,自一九四九年中
共掌握政权之後,对中国文化或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什么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
林:我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中国正式的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区别。当
然,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有不同的语言,这恐怕是全球性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的
那种话语的特定发展,直到与日常用语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这主
要是在五十年代後期开始的,是在整风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开始,直到文化革命达
到顶峰。两种语言的词汇不一样,口气不一样,甚至文法也不一样。
亚: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文革”开始之後的这样两个趋势:一方面是表现在中共
官方文件和“首长”讲话之中的官方语言本身随着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不断开展
而变得越来越极端和狭隘;第二是官方语言对原本属於民众语言领域的侵略越来越
厉害,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扩大到工人班组、农村生产队,甚至老百姓的家庭和
私人的日记里面。
林:这跟整个官方文化的蔓延有关。清代也有政治官话,但是它没有深入到底层,
只是延伸到一定层次。毛泽东的政治却直达社会底层,包括语言的同一化。官方语
言影响最深入的大概就是文革时期了。记得在广州我与朋友一起吃饭,最後朋友们
说把这一桌菜给“消灭”了吧。在生活中用武器、战斗、军队作比喻是相当多的。
比如“文艺战线”,“作家队伍”,工作的“战略策略”等等。共产党政治家经常
玩弄朦胧的字眼,从“清除精神污染”到“搞社会主义”。这个“搞”字就很模糊
,从物理学家搞物理一直到搞革命,“搞”字在政治环境中频频使用,恰恰是它没
有内容。邓小平出来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那很容易,至於具体怎么搞,他不用说,
搞运动也是这样。“搞”字在文法上到处说得过去,在内容上不必说出来。
亚:中国这样的官方语言对民众语言的压迫和侵犯,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是否
也存在?
林:也有。外国政治家也喜欢空泛的词语,喜欢把空洞的东西说得很漂亮。不过民
众的模仿不是一种政治压力的过程,而是一种对时髦的追求。比如最近几个月来,
我注意到“compelling”这个词用得特别多,说这篇文章很“compelling”,似乎
是动人的意思;说这个方案很“compelling”,是指你非接受不可,要把它弄好。
以前我们坐下来一起谈话,是“talking with each other” 或者“conversing”
,现在突然崩出了一个“interface”,也是时髦的新东西。政府特别会制造这些东
西,然後别人就赶时髦,跟着学起来。我不喜欢这种时髦,但是我觉得这与中国的
情况不一样,中国的老百姓是被迫使用毛的语言,在各种场合总要有个正确的表现
,不能出错,所以非接受官方语言不可,非跟着玩弄不可。
亚: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记载,邓小平在家庭中常常沉默寡言,与子女家人之间没
有什么话好说。赵紫阳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我想是不是这样的领域也被官方语言
侵略,没有私家民众话语的天地?或者说在亲子关系中也必须使用官方语言,否则就
无话可说?
林:我曾经与肯尼迪家庭的子女待过一个晚上,他们说话就和普通美国家庭一样。
中国的高干子弟如何我不知道。我在 UCLA工作时接触过李先念的孩子,不过都是在
正式的场合下,她使用的也都是官式语言,包括她写的硕士论文,引用列宁的话也
很多。我是她的论文的评审之一。当然我不敢说在晚上与丈夫聊天的时候,她是不
是也这样说话,估计不会吧。
不要热衷於西方的新名词
亚:您曾经批评过一些中国学人过於热衷於接受西方的新名词,还提出中国知识份
子要创立自己的词汇和理论。您是否愿意作更详细的说明?
林:我所批评的现象不光在中国知识分子那儿有,在外国知识分子身上也许更厉害
一些。我刚才说过政府的时髦语言我不喜欢,学术界中的时髦语言我同样不喜欢。
在美国学界中,象牙塔中制造出来的空泛的时髦语言实在太多。我发现有的中国学
者,尤其是年轻人看美国西洋世界,以为都是先进的东西。在科学领域,也许可以
说美国的东西比较先进,但是人文的东西就未必。有时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论出来了
,只是一种新的时髦的词语用法出来了。所以有一些大思想家,如福柯、德利达、
德曼,我个人觉得他们几乎是骗子。他们劈烈啪啦将一大堆新的名词玩来弄去,别
人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一定愿意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归根到底
是他们很少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意思。美国严肃的哲学系根本不理会这种时髦的语
言。我不责怪那些年轻人,当他们看到这些新名词时候,会觉得新的学问有可能在
其中,但是,马上将这些新名词翻译过来,放在自己的文章里,或者不翻译就用英
文插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这样做就很可惜。
亚:这一点对於中国学者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不仅在资料的占有上有很大的限制
,语言上的障碍也使得他们难以全面了解一个外国学者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的著作
,这是客观上的困难;如果主观上再浮夸一些,问题就更大,断章取义,甚至在只
知道片言只语的情况下就大加发挥,以洋人的新词汇来烘托自己的博学。
林:这种现象基本上跟美国年轻学者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掌握这
些,而是为了时髦引用很多注释,如果把那些注解和漂亮的名词拿下来,看他还能
说明什么?
亚:相比之下,这一点在实证科学领域中要好得多,那里提出一个概念,理论,往
往需要实验的支持,而且这种实验应当具有可重复性,即他人在同样条件下也可以
重复验证结果。
林:对。几个月之前纽约大学有一个数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使用了很多後现代主义
那种不像话的话。他把这篇文章给杜克大学出版的一个时髦刊物《Social Text》寄
去,刊物编辑部很高兴地将文章发表了。这位数学家马上在另外一个学术刊物上发
表另一篇文章,说自己原先写的那篇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而编辑部却看不出来,
这样弄得那个编辑部很没有面子。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最重要的就是您
刚才说的,一种学问可以实证,可以重复实验;另外一种学问确实是爱怎么说就怎
么说,没有一个衡量的客观标准。
一九八九:在北京
亚: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您曾经担任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美国科学
院驻北京办公室主任。这是不是一个官方职务,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算是官方机构,但是美国科学院并不属於政府,它由国会
创立,在法律上是民间的,其管理都由科学家主持。那年我的工作跟美国政府没有
关系,只是代表美国科学院。主要是安排访问团和具体的研究项目,从考古学到现
代生物学,有的是集体的研究项目,有的是个人项目,特别是在人文方面都是个人
的研究。平时我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事务上面,剩余的时间我就写文章。慢慢收集
材料,写成了一本书《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一九九二年在纽约出版。
亚:这本《北京夜话》是不是模仿《燕山夜话》?听刘宾雁先生介绍,这本书多年来
销售很好。
林:书名是模仿邓拓写的《燕山夜话》。不过现在看来材料已经旧了,是八十年代
的东西。
亚:方励之先生曾经告诉我,八九年二月在中国政府阻止方先生参加布希总统的宴
会时,您始终陪同着他们?
林:对,不过不是有意的。记得在宴会的前一天我们为了别的事情在长城饭店开会
,会後有人问方先生明天总统的宴会去不去,方说去。我当时想我有车,住得离方
先生又近,方先生安排车可能会有困难,就问方要不要一起搭车去。方先生说“好
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後来的事情。那天我们与方先生、李淑贤在车上谈的
是在会场上有没有机会与布希总统说说话,握握手。方和李说大概不会,只是吃吃
饭拍拍手就走吧。我们关心的也只是在进会场时会不会有许多记者围上来问问题,
准备回答什么问题,都没有想到後来警察会以方励之夫妇所持的邀请函无效而禁止
我们将车开到举行宴会的饭店。我们後来就想到美国大使馆去问一问这个邀请究竟
是否无效。我们的车已经被赶走,公共汽车也坐不成,後来就步行到使馆,几个便
衣一直跟着我们。
亚: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发生了学生和市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後来又有政府
当局的戒严和军队镇压造成的六四流血事件。为了方励之先生的安全,您当时曾经
建议他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为此作了一些联络工作。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
情况?
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点,我太太叫醒我说大屠杀发生了。我住的地方
有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一个广播站,广播说在天安门和别的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
来自各处的学生也纷纷讲述自己看到的军队杀人场景。我就骑自行车到一些我所认
识的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去。我找苏炜,他已经跑到广州去了。再到李淑贤那里,李
很激动,方不怎么激动。我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我可以帮忙。我想他们听懂我的
话,因为在两个星期之前,方的儿子方哲就来找过我,那时方励之夫妇到西安去了
,方哲问我必要的时候他的父母能不能进入美国使馆?我说我帮助打听。後来在一个
宴会上我见到美国使馆的一个官员,他说这种事情很困难,主要是没办法保证什么
时候可以出去。我问他是不是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是不可能,而是最好
不要这样做,主要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这个局面。我後来把这话告诉了方哲。因为
有过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六四那天我在离开方励之家的时候就说“我能够帮忙,我
愿意”。虽然我没有提进使馆的事情,但是我想他们能够理解我的意思。李淑贤就
说:“我们需要你帮忙的话,就打电话让孩子过来玩”。这是暗语。
亚:方先生一家那次是两度进入美国使馆的?
林:那天下午四点半,家里的电话响了,李淑贤在电话中说让我孩子过去玩。我就
马上找了一个出租车赶到方先生家。那天是星期天,使馆不开门,我就在香格里拉
饭店用我的名字租了一个房间,方家在那儿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一起楼上的CBS电
视台租的套房看电视,正好播放的是天安门的镜头,坦克车在街上,一副要打内战
的样子。李淑贤打电话到北京大学,与学生谈话,学生们说军队要到北大来,他们
准备拼命,堆了一些石头在校园里。学生们还希望老师能够保护好自己,李淑贤拿
着话筒几乎要哭了,说学生会有危险的。方先生并不是那么激动,还说原先约好和
李政道一起吃饭,问我有没有办法和李政道联系,可见他还在想继续正常的生活。
主要是考虑到学生所说的事态的严重,那天中午我们就到使馆去了,当时还带了CB
S的一个工作人员一同前往。我们和使馆的官员谈了很久,後来方决定还是离开使馆
。他作这个决定有很多因素,一个很大的考虑是会不会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让他
们用方进美国使馆的例子去指责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学生、知识分子“与外国势力勾
结”。美国使馆的人也是这么提的,说有没有考虑政治後果。考虑了半天,方励之
决定出去,李淑贤害怕丈夫有生命危险,似乎不太愿意离开。我们後来到了建国饭
店,那里有我的一个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朋友,他正好到上海去,房间空着,
可以使用。我让方家留在那儿,自己回到友谊宾馆我的住所。
亚:您後来没有再送方先生进使馆?
林: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建国饭店方先生住处,没有人接。一直到方励之夫妇後来经
过英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离开建国饭店之後发生的故事。那天晚上
十一点钟,同样是那两个美国使馆的人来到建国饭店找方励之夫妇,说乔治·布什
总统邀请他们回使馆,方先生一家三人就进使馆去了。
独立知识份子的自我定位
亚:对方先生进入美国大使馆这件事,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论,有的赞成,有的反
对,有的惋惜。甚至不久前还有人在感叹中国失去了一个产生自己的“曼德拉”的
机会。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林:我知道很多人批评方励之,说他不应该到美国使馆去,有的中国人还批评他不
应该“低头”。对这种批评我有很大的不同意见。我觉得一个人求得自己的生存是
自己的权利,方在中国有那么大的勇气,个人已经付出了很多。许多旁观者自己不
去冒险,却在评论别人,质问人家为什么不做谭嗣同,这种批评我非常不喜欢。至
於说如果方不进使馆,被逮捕,坐牢,变成南非曼德拉式的英雄,也有可能,这样
今天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大概也会大得多。我不赞成的是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去批评
采取行动的人,那种像观众评论演员演戏演得好不好一样的看戏心态。
亚:中国政府以此来贬低方励之,这另当别论;公众舆论和民运队伍中的批评与惋
惜,似乎涉及到对所谓“英雄”所具有的一般人权的尊重,其实英雄也有选择做不
做英雄的权利,何况方先生本来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天体物理学家,而不是政治家。
林: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衡量他人,一般也没有错,只是很多人不理解方励之
本来是一个科学家,他想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自由地表达
他对政治和社会的看法。他对自己的定位一向是这样的。记得他刚从英国到美国时
,有些人希望他出来当民运组织的领导,而他在普林斯顿时说,他不想作一个职业
的政治家,异议政治只是他的副业。许多人因此对他表示失望。
亚:据我所知,方先生在天体物理学上也是有所成就的,一九八五年他所获得的国
际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奖也是中国天体物理学界在这个领域中的最高奖,不过在一
九九零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技术记事》中,方先生所有的得奖项目都没有
记录。
林:我们这里的一位副校长也是天体物理学家。有一次我与他一起打球时闲聊,他
说方励之脑子非常清楚,写的文章显示出方很聪明,但是从七、八年前的文章看,
聪明似乎不是化在点子上;现在看来,方的聪明越来越用到要害的地方了。方从使
馆出来之後,经过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直到现在在亚利桑那做教授,
能够触摸到天体物理学最尖端的问题。
多元化的社会里的自由知识分子
亚: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您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由知识份子。我想与您讨论
一下,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做到既对社会保持深切的关怀,又维护自己学术研究的超
然立场?对於中国知识份子来说,这历来是一个大问题。
林:我觉得能够做到。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又经常写文章,发表书评,还喜欢
批评政府,但不是消极悲观地对待社会。政府喜欢不喜欢我的批评对我来说不太重
要,我比较不在意政府如何看待我。当然这也和环境有关系,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
社会里,我与政府唱反调,普林斯顿大学不会解雇我,政府也不会迫害我。相反,
我唱的反调还有市场,有些杂志也就是喜欢刊登与政府唱反调的文章,这就是多元
社会的好处。
亚:您是否认为现代知识份子的社会作用要在与政府即官方保持某种联系,甚至要
在具有某种官职的状态下才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林:当然不是。在美国知识界,尤其是搞政治学的人认为有可能到华盛顿去做顾问
,能够劝政府或总统做些什么,是很光荣的。他们也在发挥作用,不过不会像我那
样把批评意见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如果我也在政府作顾问的话,那些喜欢刊登批评
政府文章的杂志就不会喜欢我写的文章了。
毛泽东:自私狡猾;邓小平:“棉里藏针”
亚:您在美国和英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对李志绥医生所写的《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以
及邓毛毛所写的邓小平传记的评论。依据您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您对毛泽东与邓小
平总的印象如何?
林:李志绥的书反映了毛泽东的自私和狡猾的方面。尽管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对毛已
经是看透了,但还是对书中披露的有些事情感到吃惊。毛竟然是如此霸道,如此残
酷的一个人。我认为作者掌握的基本上是第一手材料,我在读书的时候觉得可以接
受,不能说这本书不真实。这本书中记载了那么多细节,如果是编造出来的话,在
细节上总会露出虚假和伪造的痕迹,或者自相矛盾的方面。中共官方说这本书是假
的,那么完全可以拿出真的来予以反驳,可惜我没有看到;当然,作者的笔记在文
革中被销毁了,光凭记忆,任何人难免有小差错。
邓小平这个人我不认识,看了邓毛毛的书,我觉得有一种将许多别人的材料堆在
一起的虚假的感觉。作者依据许多借用来的材料编出一本大书,虽然不能说完全是
像编故事一样,但它在真实性上给我的感觉不那么直接。我很难评论邓,但是总的
感觉是,作为一个人来说邓要比毛正常一些。
亚:您对邓毛毛这本书的书评的题目是“棉里藏针”,您读书很仔细,在书评中还
集中列举了邓小平作为“钢针”一面的事实。
林:“棉里藏针”是借用了毛泽东有一次劝邓的话:“不要作钢铁工厂,要棉里藏
针”。我的文章标题是编辑起的,不过我在文章中用了这句话,我对邓的印象是有
点“棉里藏针”的味道。在邓毛毛的书中,作者无意之中反映了她的爸爸的残酷方
面,其中有战争年代因为一个下级军官偷了一包面条而下令将他马上处决;一九五
零年进军西藏的时候消灭了五千七百名藏人。联系到邓一九七五年批准军队以武力
镇压云南穆斯林的反抗直至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屠杀,似乎也很自然。
希望一个文明自由的中国出现
亚:不久前您访问中国大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这是什么原因?
林:中国政府说“林培瑞自己知道原因”,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我入境时持有进入
中国的合法签证,到中国去的目的也是学术上的。前几年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
大学合办暑期训练班,每年把一百二十多名美国学生送到北京进修汉语,一九九四
年我做过美方的班主任,明年这个职务又轮到了我,今年我打算到中国去做一些准
备工作,顺便作一个公开的演讲,题目是“汉语和英语日常用语中的比喻”。我想
这些事情不会构成不让我入境的原因。回到美国,我找到我们校长,他答应帮忙,
写信给国务院,问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不仅是林培瑞一个人的事情,也是普林斯
顿大学关心的事情。学生办的校报也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还发表了一篇头版文章
报道这件事情。
亚:是不是您最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中共政府?这跟您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没
有关系吧。
林:多年来我得罪中国政府的地方确实不少,但是到底是哪一条在这一次入境问题
上起了作用,我确实不知道。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还不至於如此,因为这些
文章都是我在《美国之音》上面广播过的。《美国之音》要我每一个月在他们那里
发表一篇短文。在中国政府判处魏京生十四年徒刑时,我在《美国之音》上公开提
出批评,我猜想这也许是我这次不能入境的原因。我在纽约、伦敦的英文报刊上发
表了许多涉及中国社会的文章和书评,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毕竟还是外国人写
给外国人看的,对中国人影响不大。而《美国之音》广播到中国大陆,这个影响就
不一样。我在《美国之音》的文章都是我自己直接广播的,在广播完毕时我总是说
一声:“我是林培瑞”。
亚:作为一个对中国大陆文化有相当了解的美国学者,您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在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及其未来的前景有什么见解?
林:对江泽民,我最初的印象是认为他是有点像华国锋一样的人物,觉得他比较无
能。大约在最近一两年来,又觉得他并不那么无能,而是相当聪明。在首都钢铁公
司事件的处理上,把邓的力量搞下去,巩固了自己的位子。当然我说不上喜欢他(我
对所有政治家的初步的反映都是不太喜欢的),不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读了《九十
年代》上发表的江泽民与沈君山的三次谈话纪要,我觉得江泽民很自大。他说只要
他坐在这个位子上,中国就不会如何如何,完全是那种人治的、唯我独尊的腔调,
我听不惯。当然我很难对我不了解的人加以准确评论。
九三、九四、九五年我都去过中国大陆,甚至一年去了两趟。根据我的观感,中
国的情况还是有进步的。九十年代初期北京街头的气氛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台北
的街头。一九七三年我到台湾去过,气氛类似,从街道的发展到人群的表情。在北
京的出租车上与司机聊天,几乎是一致的看法:现在还不错,但又很困难;钱比以
前多,可是还不够。好话听得到,牢骚也不少:物价很贵,贪污厉害。出租车这个
天地是比较放松的,可以讲真话的。不过我只到北京,其他落後的地方没有去过。
我从《纽约时报》也可以看到关於中国贫富悬殊的报道。
亚:您是“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还担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董事长。对於
海外的中国民运组织活动,您也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如果您愿意,请您谈谈对现时
流亡在外的中国民运组织、人权组织或学术组织的看法。
林:“中国人权”组织做得很不错,在它掌握的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做了很多事情
。与它在一起的”亚洲观察”也是做实际事情的组织,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权
的现状暴露给全世界看。“中国学社”在法律上是非政治的学术组织。我想海外中
国人组织要作为团体“打回去”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倒是怎样与国内
保持联系。我喜欢“美国之音”这样的广播,就是因为它可以把海外的消息很快传
递到国内,中国的变化最後还是要依靠中国国内人士的努力。
亚:您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顾问已经有几个月了。您认为我们的刊物在哪
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在文字的使用上,还有哪些缺少推敲,不够讲究的地方?
林:杂志办得很好。我不敢说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看得不够。我对英文文字在使用
的精确上很敏感,对中文就不敢说有那么敏感了,好一点差一点的文章,我不一定
看得出来。我支持你们从事的可贵的工作,我在贵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
广阔文明的中国正在崛起。我相信这一点。
亚:与您的谈话非常愉快。感谢您提供了那么多精彩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