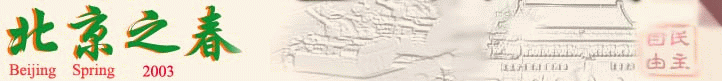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
曹长青
【编者按】本刊八月号发表了曹长青的文章,对胡平关於八九民运的观点提
出批评,胡平在十二月号上作出回应。现在曹长青又投来一稿再作批评,特予刊登
。批评的前提是理解。建议大家读一读各方先前发表过的观点(包括胡平那篇“八九
民运反思”)。我们相信读者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胡平围绕着“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一“八字诀”做了好几年的文章,并
以此为依据评价八九民运的成败得失。在上期《北京之春》上,他继续撰文批评学
生当年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策略失当,没有“见好就收”,同时批评郑义和我对
他这一说法的异议。但实际上胡平的“八字诀”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式
的八股文字游戏,如同“一国两制”般根本无法操作。如果依这种八字八股指导中
国的民主运动,不仅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人们纠缠於所谓策略,而不
去分清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下制定策略,尤其是忽视中国现实最需要的“指出皇帝
赤身裸体,面对暴政勇敢反抗”的原则精神。而且,以“八字诀”策略来批评学生
,实际上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否认“知识人”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
浅薄和反抗上的怯懦。
一、在批评魏京生不懂策略的背後
近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好几位民运精英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贴
大字报公开指出邓小平独裁的做法是“激进”、“不策略”。胡平公开撰文这样说
,现为纽约“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跟着附和,而郭罗基则在香港《争鸣》上撰文
指责∶“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
对的方面。”(九五·九·)魏京生在狱中,以及出狱以後,从来都没有发表任何
言论指责别人当年“太温和”,不勇敢。为什么这些民运精英们却不约而同地主动
批评起魏京生来?我一直不得其解。近来才想明白,原来在他们批评的背後,是想
传递这样的意思∶当年我们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但我们懂得策略,不直接
指出罢了。胡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把它说得很直白∶“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
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
”
且不说这种攀比和不服气有多么自负和俗气,真的比较起来,他们确实比魏
京生逊色。例如胡平当年所写的《论言论自由》,立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
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解释的,
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同样张贴在
“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而郭罗基当年最“
出格”的言论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刘青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编辑
,这本刊物的宗旨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些人都属於当年较早的觉醒者,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没有人想去
否认,我几年前就曾在《中国之春》上撰文对胡平当时能写出《论言论自由》给予
很高评价。但是他们今天硬是声称他们当时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只是出於
策略,才不直言说出。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这种理由成立,那么谁都可以声称
,我几十年前就比哈维尔和昆德拉想得还深刻,但我就是不说。这显而易见是无法
服人的。
虽然魏京生的文章在理论上并非十分系统和缜密,但他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
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清的真实。发现一个简单的真实的能力是远比解
说哲人已有的理论更需要智慧,也更深刻。魏京生不仅指出了邓小平正走向独裁,
也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当时公开质疑了邓小平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
。同时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这一要求,本身就已涵盖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刘宾雁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反思的,一九九一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
“人权会议”上指出∶“一九七九年以後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迟难以摆脱对於中
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这是中
国人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发落後於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这
往往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刘宾雁没
有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的言外之意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
能认识到公开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共产主义从
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
缺乏胆识公开谴责专制者,而喋喋不休於“策略”的现象,在中国知识人的
传统中有悠久的历史。在皇朝时期,儒生们两千年来苦思冥想的都是“策略”,即
怎样谏言,才能使皇帝听得进去,从而使昏君变成好皇帝,而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有
智慧质疑皇帝制度的合法性。知识人们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寻找统治者能够听得进
去的“进谏”策略,而从不把精力用来思考“皇帝新衣到底有没有”这个根本性的
原则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黑体{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根本就对原则不清
楚,所以才反来复去围绕着策略打转转儿。}
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知识人中仍很普遍。很多改革派知识分子写的
文章,不管开放到什么程度,都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更不要说号召人民
推翻这种暴政。一些当事者对此解释说,这样做是出於策略,为保住再“说话的权
力”。\黑体{但保持说话的权力,和说真话的权力是不能比的,说了多少假话,都
不能和说一句真话相比。讲究策略的理由的背後,实际上是对真实缺乏发现的能力
。}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时至今天还在撰文期望与共产党“朝野双方
良性互动”,对於这种幻想,我在“学生与天安门”一文中已予以批评(《北京之
春》,九五.八.)。而自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时至今天还在大谈民运人士
要“守共产党的法”,理由是“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誓不两立
、推倒重来。”“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引文同
上)但他至今还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共产党
不是美国的民主党。
时至今天,这些人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水平还是这个样子,而十五年前
他们的深刻程度怎么可能不比魏京生逊色呢?
而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像中国知识人这样热衷於策略,他们从一
开始就说真话,捍卫原则。例如早在一九五七年的《新阶级》中就否定了共产党的
吉拉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共产党,这
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索尔仁尼琴在一九七四年就写出“让
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哈维尔一
九七八年发表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虚假的意识
形态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
规则,揭露游戏本质”。因此哈维尔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
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按照中国某些理论家的标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人当年的举动
都属於“激进”,“不策略”。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没能保住“以後再说话”的权力
,而且当时也很少有民众呼应。但为什么恰恰在这些“不策略”的知识分子所在的
国家,共产党被推翻了,而在知识人讲究策略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存在呢?对此,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明确的回答∶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
的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
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
渴望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
事实时,表面上看是单枪匹马,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
在播种到人心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
民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
是在结束整个“新衣皇帝”制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
服的好皇帝。这种勇敢者的深刻和宝贵之处在於,他为人民重新审视皇帝提供了一
个“视角”,使人们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正如哈维尔
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的,“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着身子”,“单枪匹马、‘没
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
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样的“体制外”的独立思考,和单枪匹马的勇气,
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
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
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魏京生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单枪匹马与独裁者的
直面抗争,当时没有呼应,已应惭愧,但人们可以理解;今天不像哈维尔那样给予
高度赞赏,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反而还要主动批评这种中国人中罕见的
智慧和勇敢,并指责为“激进”“不策略”,愚顽至此,没人出来痛击才是怪事!
(关於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我写了一万余字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
”一文,已发表在十二月号的香港《前哨》月刊上,这里不再多重复。)
二、“见好就收”是八股文字游戏
抛开上面讲的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勇气,退一步讲,即使从
策略的角度,“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是一个无法操作的“策略”。因为什么叫
“好”、什么叫“坏”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它有点像共产制度中的“好人”和“
坏人”的概念一样,带有先天的随意性。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今天夸他是“好人”
,明天这个人又被定性为“坏人”,因为以“好”与“坏”这样的词作为衡量标准
太抽象,缺乏具体的测定尺度,最後的结果自然是统治者的喜恶成了标准。胡平的
八字诀理论也有这种随意性,例如他列出八九民运中有六次“好”的机会,而学生
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特别强调了第六次的“大好”,即五月十八日报端发表
了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停止绝食的讲话。设想人们真的按照胡平的理论
,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後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
认定的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的“见好就收”的“好”的标准带有多大
的随意性。这种以抽象的词汇作为策略标准的方式,只能给理论发明者居高临下随
意仲裁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上却是纸上谈兵。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为什
么见到胡平所认定的“好”而就是不“收”的原因,因为人们心中的目标,不是胡
平那种随意性的“好”,而是当局收回完全违背事实的《人民日报》“四·二六”
社论。这是人们在社论发表後一直十分明确的目标。对这样一个低得不能再低了的
要求,当局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下了戒严令,调动军队摆出镇压的阵势。在这样的
蛮横面前,人民怎么可能“收”呢?
胡平在《争鸣》和《北京之春》上两次不厌其烦地全文抄录赵紫阳的讲话,
以此证明这就是“好”,因为共产党让步了。但任人皆知的事实是,在当今共产党
的权力中心,说了算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赵紫阳的讲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
撤回“四·二六”社论,更没有说他的讲话是邓小平的意见。而中国人清楚的是,
“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写的,而掌握大权的邓小平始终没有表示要
改变这个定性。这就是人们不“收”的根本原因。而胡平事隔七年之後,还搬出当
年赵紫阳的讲话来证明共产党已让步,会守诺,但赵紫阳最後连自己的乌纱帽都没
有保住这一事实,比什么都更能证明这种“诺言”的无效性。一个发出诺言的人已
被朝廷罢免,人们还要以他的诺言来证明朝廷是可信的,这不是荒唐的逻辑吗?
同样是民主运动,原苏联的情况就不是以“见好就收”这种模棱两可的理论
指导的。例如当时“八人帮”政变被挫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被拘禁地回到
莫斯科,他表示要严惩政变者,全面改革共产党并保持苏联不解体。按照胡平的理
论,这是比赵紫阳的讲话要好得多少倍的“大好”,苏联人就应该“收”了,谋求
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的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了。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
们即使见到戈尔巴乔夫许诺(实际上也已实现了很多)这么多的好,但就是“不收
”,而是一鼓作气推翻了共产帝国,获得了自由。他们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
们心中没有那种随意不定的“好”,而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
我们再看最近世界媒体广泛报道的南韩的例子。在全斗焕当总统期间发生了
“光州事件”,屠杀了几百平民。但事件发生之後,南韩逐步有了民主选举,而金
泳三当选总统後,实行“阳光法案”,厉行制裁贪污和腐败,使南韩成为亚洲民主
富强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在电视上,报纸上,仍然不断看到南韩学生与警方激烈冲
突,他们可不是像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那样温和,而是拿起铁棍和石头与警察搏斗,
几年来冲突流血不断,引起世界瞩目。有些中国人不解,南韩已经那样富有而民主
了,为什么韩国人就不懂得“策略”,不知“见好就收”呢?因为韩国人的心中也
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好”,而是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是只要不制裁“光州事件”
的主要凶手,就不能“收”。正是这种坚持原则的抗争,才使屠杀平民的主要责任
者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最近都被逮捕,等待审判。
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所以是“八股文字游戏”,除了它
的随意性之外,另一个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操作。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最多
时在北京就达百万以上,胡平根本忽略了这场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人民争民主
要自由运动的自发性特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胡平当年从纽约回到北京,站在百万
游行队伍面前疾呼“见好就收”而无人理睬的尴尬场面。不要说胡平,任何人在当
时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而胡平的“见坏就上”更是
完全无法操作。我不知道在“六四”屠杀之夜,胡平用什么智慧能使民众迎着枪口
往上冲?
退一步讲,胡平的这种理论不要说在有百万民众的天安门运动中无法实行,
即使在只有几百人的海外民运中也操作不了。例如,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
,胡平都在其中扮主要角色。在一九八九年初的第一次分裂中,胡平正任职“民联
”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主要创办人王炳章的民联常委职务。主要是因
为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将被上海公安局释放的民运学生杨巍捎带私人信件和资料,
此举被认为是杨巍被推迟释放两小时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请假[自请停职]一年
以缓和冲突,避免分裂。按照胡平的理论说,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王炳章的
错误并不是他赞成共产党或是中共特务这类性质的问题,但胡平并没有“见好就收
”,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後来又开除了他的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
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到美国,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
裂”的报道。稍後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由於内斗,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发生於一九九三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刚
从国内出来不久的王若望已报名竞选主席,因不满徐邦泰会前许诺当他的副手,但
在会上临时又变卦竞选主席,并有用“假代表”拉票现象,而当场宣布退出竞选,
引起会场骚乱。当时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有成
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着合并变成了取消,对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
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
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於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也退出
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这场分裂给海外民运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恢复。如果说王若望刚到海外
,对民运可能因此分裂的严重後果还不是很了解,他的退出竞选还情有可原的话,
而胡平作为已来到美国多年,又担任两届民联主席,而且十分了解与王炳章的分裂
对民运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是专门研究民运“策略”,提出“见坏就上”理论的主
要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严格地说,使海外民运从根本上伤了元气的两次重大
分裂,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胡平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在第一次
他就没有“见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没有“见坏就上”。但时至今天,胡平对这
两次他身在现场、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事件应负的责任没有一个字的反省,人们看
到的却是他不遗余力地指责有百万民众之多的天安门运动如何没有“见好就收,见
坏就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胡平的八字理论,在这样几百人的海外民运活动中都无法操作,甚至连这种
理论的发明提倡者本人都不能实行,这种理论不是八股文字游戏又是什么呢?
三、八九民运的真正经验教训是什么
但是这种“见好就收”的理论是批评不得的,因为只要一批评,就被胡平指
责为“全盘否定策略的意义”,似乎胡平的“八字诀”涵盖了一切策略。其实,没
有人要否定策略的意义,人们要质疑的是胡平这种无法测定标准的策略的随意性和
不现实性。
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有没有策略不当的问题,有的。但这个“策略失当”不
是胡平一直强调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而恰恰是知识分子们没有明确而坚定
地站在学生和市民这一边,更没有发出人民只有与专制政权抗争到底才能迫使统治
者让步的信号,因而导致“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只剩下了力量单薄的几千学生。
设想,如果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直能保持百万人的规模,如果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
能够有胆识地联合起来,投身天安门运动,站在抗争暴政的前列,以他们的道德勇
气和力量唤醒更多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并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底,八九民运很
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
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原苏
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长期不断地向人民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没有智慧
,也没有勇气向人民指出共产党是邪恶,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专制的思想,因而在当
时的北京,人们既没有意识到只有坚持抗争才能夺回一点权利,更没有认识到应该
提出结束共产党统治的诉求。所以八九民运以人民流血,专制没有结束而收场。当
年叶尔钦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不到三天,有七十年历史的苏共帝国就崩溃了。这不
是叶尔钦个人有多大魔力,也没有什么民运组织的精密策略,而是萨哈罗夫、索尔
仁尼琴等思想先驱者长期向人民传播的“共产主义是邪恶”的真实在人民心中扎了
根。所以当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们就揭竿而起,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
制。
因此我认为,天安门屠杀的责任完全在於共产政权,而学生没有任何责任,
根本不存在因学生不撤离广场才导致屠杀的策略失当问题。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说
∶“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於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
,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
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么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
规矩!”胡平把这段话指责为“共产党语言”。而胡平这种在无法有力地反驳别人
时,就指责别人是“共产党语言”的手法才更像共产党的论理方式∶他没理可讲的
时候就说对方“态度不好”,而回避问题的要害,转移人们探究是非的注意力。
胡平对这句所谓“共产党语言”举例批评说∶“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下车
没锁车门,窃贼就不会把你的车偷走。你却勃然大怒,说不论我锁门不锁门,不是
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做人的规矩。对於这种不切题的回答,别人还能说什么
呢?”而实际上胡平的这个看似颇有道理的比喻才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切题。因为天
安门运动的情景不是车主疏忽使车被偷的问题,而是一群强盗公开抢劫了居民的财
产。因为小偷既是被动的,又是理屈的;而强盗既是主动的,又是理直气壮的。被
抢的人中有人跑到强盗门前游行,要求索回财产,但却被强盗施以暴行。胡平认为
,双方都有责任,居民的责任是在与强盗对恃时没能在施暴前“见好就收”,因此
失掉了与强盗形成“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我认为这种“朝野双方良性互
动”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强盗和被害者之间没有“朝野”关系。强盗之所以敢
於施暴,恰恰是因为敢於在强盗门前坚持抗争到底的居民太少。为什么坚持抗争到
底的人太少,就是因为居民当中那些有文化的人,没有智慧发现强盗是绝不会把财
产还回来的本质,因而也谈不到把这个真相告诉人民,更谈不到号召所有的居民起
来推翻强盗制度。所以对那些坚持抗争到底的人,不仅不应指责,而应高度赞扬,
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精神。
因此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
党。”这是胡平从我的文章中挑出的第二处所谓“共产党语言”,他认为这是“绝
对化的武断”(有不绝对化的武断吗?),并嘲讽地说∶“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
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後的今天,曹长青为什么还要讲出这
种话?”这点正是我和胡平观点的根本分歧。胡平和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和东欧
的变化。胡平认为这种变化是“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而我认为共产党从来就
没有改弦更张过,而是人民起来推翻了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以共产党性质建立的全部
政权。迫使那些不管今天还叫“共产党”或改了名字的原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不完
全放弃了共产党的专制、公有、垄断新闻和军队、剥夺人民政治权利的共产党本质
。例如我们看到原波兰共产党人在最近的大选中虽然取代了瓦文萨而当选总统,但
他不仅公开谴责共产党,而且政治主张与瓦文萨一模一样。在任何其他国家,那些
原共产党人,要想再得到政权,也必须在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实行民主自由、通
过选举执政。这一点本身已证明,这些组织从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
。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那种“本质”已被结束。换句话说,具
有原共产党本质的共产党已经死亡。
同时,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没有
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张”,而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个共产国家
政权被推翻之後发生的。也就是说,\黑体{如果有“改弦更张”,前提条件是共产
政权被推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着,绝不能寄希望於在共产党
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着权力的时候,它就能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全世界的
范围内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样“改弦更张”的例子,怎么中共就是个例外呢?根据
在哪里?
胡平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来反驳我的“共产党的本
质永远不会改变”之说,这等於是在向中国人发出错误的信号∶共产党在不被推翻
之前,就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正是胡平的这种原则不清,而导致他提出“见
好就收,见坏就上”这种模棱两可、目标不清晰的所谓“策略”;也正是这种原则
不清,导致胡平提出与共产政权“朝野双方良性互动”这样荒唐的政治诉求。而这
种原则不清的最大危害是∶它误导中国人继续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结果只能是延长
共产政权的寿命,而由此延长人民失去自由的痛苦,这显然与胡平所期待和努力的
目标正相反。
在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被人民推翻至今已经有五、六年的今天,中国的知
识分子们还要为“共产党的本质会不会改变”这样的常识而争辩,这不仅是知识分
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民运的悲哀。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於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