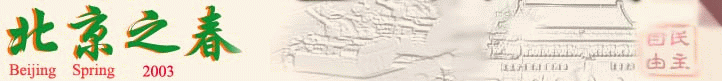批评与讨论首先应当注意逻辑和态度
--评曹长青先生《知识份子与共产党》
沈渭修
读《世界周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日所载曹长青先生《知识份子与共产党——
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一文,多有不同之见,愿借贵刊一角略
予表达。曹文以对“有影响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作比较,来解答“为
什么东欧、俄国的共产党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的问题。既然申明是采用比较的
方法来立论,那么无论作者是学者还是记者或专栏作家,都应该遵循比较研究的基
本规范,才能使立论有说服力,这些规范其实并不多么高深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常
识,论者只要留心就不会流於随意进行比较评价的偏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遍观
曹文,读者不仅大可质疑构成其理论基础的那些逻辑方法的假定是否任意率性,而
且也有充分理由怀疑作者据以作出评价的态度是否公允平和。
曹文的第一个假定是暗含的关於比较参照系的假定,即无论是原苏联、东欧还是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作者看来都是一样的,至少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致影响到对知
识份子认识水平的考察,这一假定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承认对社会人事的比较与
自然科学的比较不是一回事,後者可以有绝对的参照系,例如根据同一温度标准我
们可以检验出不同金属具有不同的熔点,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就只能建立或选
择相对的隔离和抽象,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首先要求作者表明他是如何进行这种隔
离与抽象的,他所选择的方法与标准对比较研究的结果有什么影响。曹文将各国的
共产党政权及其殊异的社会历史条件视为同一物并以之衡量各国知识份子的认识水
平,规定面对着同样的共产党政权唯独中国知识份子的表现不及他人,这未免失之
武断。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发生和存在有着相当不同的背景、
理由和表现形式,它们与本国人民及知识份子的历史关系也各有其特殊性,涉及很
多复杂方面,这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不要忘了这些政权之间也曾秘密地和公开地互
相排斥和批判,即使按照曹文的思路以专制暴政为其共同抽象,这种抽象也不足以
作为一个共同参照进行比较分析,因为一旦进入认真的具体的比较,我们就会进而
要求参照系也必须具体化,比较的方法本能地反对笼统和含混。举例而言,我们不
妨套用曹文的方法设计这样一种比较:拉美各国大都在十九世纪仿照美国确立了各
自的民主宪政制度,而这些制度後来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因又各有不同,倘若我们硬
将它们简约和同一化并以之检验若干“有影响的知识份子”的认识水平,来解答为
什么民主制度在美国得到稳定发展而在拉美各国却频遭军事政变,这样比较出来的
结果即令我们认为独具慧眼,却又如何取信於人呢?
曹文的第二个假定是明确的关於比较样本的假定,即“仅仅从有影响的知识份子
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来比较,就可以对上面提出的为什么作出基本解答”。这一假
定也不能成立。首先,读者无法像作者一样不加论证地完成“仅仅从……就可以…
…”这一逻辑跳跃。凭什么仅仅有影响的知识份子的认识水平就可以提供基本答案
,所谓“有影响”的标准又是什么,读者根本无从推断作者这一论点的根据何在。
其次,作者在文中对这一论点作出了相当牵强的经验解释。例如,著有《新阶级》
一书的古拉斯被作者誉为最先对共产党政权进行系统批判的有影响知识份子个案,
但是人所周知南斯拉夫正是东欧目下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政权,作者也未向我们提供
波兰、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有影响的知识份子的
任何个案,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的终结方式不仅各不相同,而且这
些不同方式对於解答曹文提出的“为什么”绝非无关紧要。此外,曹文在选择所谓
“有影响的知识份子”作比较样本时,很难让人不以为是在削足适履、自取所需,
以苏联东欧为例,有影响的知识份子远不止於曹文中所述及,甚至其典型类别也不
能被述及者所完全代表,著名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知识份子固当别论;著有《让
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问题》等重要作品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即被研究
者认为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齐名的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人物,此人在“八
一九”政变失败後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率先谴责叶利钦宣布共产党非法,曹
文自然是将此类知识份子作为左脚趾削去了。另一方面,即以中国“有影响的知识
份子”为例,严家其先生自流亡之日始便一再论称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王若望先生
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则更是严责有加,而他们也都成了曹文刀笔下的右
足趾。再如,曹文轻易地论定当年中国的右派知识份子的言论“都没有超出对共产
党发牢骚的范畴”,这显然只能自暴作者披阅和采证范围的有限。
曹文的第三个假定是一个操作性的假定,即判断知识份子认识水平的技术标准乃
是考察对象所发表言论中与共产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语词表面关联性。在
稍具生活经验和理论素养的读者来看,此一形式上的假定未免故作幼稚,曹文认为
,唯有公开地、正面地、激烈而不妥协地批判共产主义、质疑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
知识份子,才具有高深的认识水平,反之,不论出於何故,则都是对共产主义和共
产党抱有幻想。被曹文所列为警惕和批评样本的各国知识份子的真实个案究竟如何
,这里篇幅所限姑且不予逐一讨论,只想指出思想史上的一个常识提请曹先生注意
:从格老秀斯以降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份人都不曾采取公
开地、正面地、激烈而不妥协地批判中世纪神学的姿态,然而人们并不以此来评断
他们认识水平的高下和对社会变革影响的大小。对於作品的表达形式,除了所谓“
王杨卢骆当时体”这一古人早已明辨的寻常事理而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在。追
求自由诚属人类本性,趋利避害又何尝不然,否则我们何以解释专制制度在人类历
史上如此长期而多样的存在?社会大众间如此,任何处於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启蒙思
想家和“有影响的知识份子”也无法超脱人性自身的二律背反,都只能在一定限度
下尽最大可能地表达并力求广泛地传导其思想,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复杂社会方程
。相形之下,曹文反复诉诸“皇帝的新衣”,这则著名的安徒生童话恐怕不是没有
来由的。读者难免不因而揣度作者对同化的特殊偏好与其行文推理方式之间是否有
着某种关系。我们知道,童话之所以叫做童话,正因为读者一般来说是思考能力尚
未发展健全的非成年人,它与现实在概念上是相对立的,或曰非现实的。再富有寓
意的童话也是童话,它的经过提纯的简单场景和逻辑还不足以表明用来剪裁和解释
复杂的现实成人社会。
说及态度,首先难免使读者质疑的是曹文对待中国知识份子和原苏联、东欧知识
份子所采取的区别态度,如果说我们本来对英语中“区别”与“歧视”可以用一个
语词来表达,而对两者之间的语意过渡尚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曹文的态度很难不使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无须过渡的标本,这样说并非想厚诬曹先生,我们愿意推想曹先
生苛责本国“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是出於恨铁不成钢,但是我们必须要求,任何严
厉的批评如果是善意的,就应本着推己及人和察诸具体背景的态度,任何不怀偏见
的人应当看到,中国知识份子近数十年历程所凝结的精神成果和所建立的思考坐标
,不仅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本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且也反映了各国知识份子
同样的精神追求和思考原则,作为有着共同经验背景的国人,我们本应更加珍惜这
些实质性成果和坐标,而不应该以一些形式上的差别得出曹文那样明显偏颇的答案
。在曹文所批评的对象中,尤其令人难以理解其用心的是对刘宾雁先生和胡平先生
的指责。作为两代知识份子有影响的代表,刘宾雁和胡平的经历、角色和成就各不
相同,但是把他们作为具有独立思考人格追求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坐标性人物应不过
分,如果说刘宾雁更多地体现着中国知识份子秉持道义良知的执着与诚恳,他的言
行作品甚至於他的姓名本身在当代中国人民中所享有的巨大人格影响并不逊於那些
被曹文称誉为“世界级”的知识份子;那么胡平则更典型地代表着中国知识份子理
性思考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他的几乎是炉火纯青的熔经验分析和语义分析於一炉的
思辩和表达方式已经构成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史的重大贡献。且不论两人的其他作
品,凡是认真读过刘宾雁《走出幻想》和胡平《写在世纪之交》的人,都会难以将
他们对中国知识份子自身经验的真诚反省与曹文断章取义的指责吻合起来。当然,
坐标性的人物并非完美,并非不可以批评,在我看来,刘宾雁先生在道义立场的选
择上有着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深刻冲突,这种冲突困扰着他的思考方向,也影响
着他如何真正“走出幻想”;胡平先生则是在自身表现方式上有着行动者和思想者
的顽强纠葛,这种纠葛虽然在一定方面为他的思考提供了某些刺激性活力,但同时
又分散了思考所必须的专注力从而影响了其成果,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反省和思考
抱持更大的关注和期待,却没有权利轻率地将我们不甚喜欢的某些表述随意曲解而
後定性批判。
其次还应谈到作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曹文视马克思主义为罪恶之源,称共
产主义为全球性的邪恶运动,并且因此而激烈批判一些与他持不同态度的中国知名
知识份子,尖刻地鄙称他们“加入过邪恶不後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密切关系以及後者在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已为世人所目睹。
这是无庸遑辩的。另一方面,某些(绝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对这种关系和失败
采取与多数人不同的反省方式甚至立场,这不但是应当允许的,而且对於丰富和深
化人们的认识也是有益的。曹先生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
在批判别人的立场时则不宜取过分简单化的态度,言及马克思主义与专制暴政两者
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见仁见智的话,至少也并非像曹文认定的那样简单,例如,
智利的阿连德政权不仅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执政後也没有建立专制暴政,倒是
以军事政变将之推翻的皮诺切特政权被普遍认为更合乎专制特征。曾任卡特政府国
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一九八九年论及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时,便特别强调
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不可忽视的人道价值,不错,美国前总统里根确曾多次以邪恶
指称共产主义。然而另一位总统布什在一九九一年与莫斯科私人企业家座谈时发表
的见解却更加意味深长,他说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人性是不可改变的,他并没有断
言那是朝哪一方向的改变。曾长期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纲中一直保留将马克
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来源之一,也是社会历史和人类思想复杂性演变的一例。历
史并未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论定的那样已告终结,人类社会与思想的演变可能性远
未穷尽。因此,对他人的思考以至信仰报以宽容和开放才是比较健康的态度,素以
对马克思主义持不妥协立场著称的余英时先生在为《邓小平帝国》一书作序时曾有
过这样的持平之论:“和本世纪无数抱着自由民主理想的中国知识份子一样,阮铭
先生最初是由於误会而加入了共产党,最後则因为了解而离开了它,无论是加入还
是离开,其中所体现的知识份子的良知都是同样可敬的。”不同的读者对於余先生
所使用的“误会”一词也会有不同解读,但谁都不难体察他善意地理解别人这种可
感风范。
最後则是关於作者为文论事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写作态度。读曹文,很难不令人产
生读檄文、读判决书之感,曹文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独断论的、居高临下的、以气势
吓人的宣判态度,在海外华文媒体中独树一帜,相当令人瞩目,我并不否认文章做
法可以有此一类。但是作为读者,总还是希望不要把冠之以“比较”这样带有分析
性的文章与判决书做得没有两样。真正从事比较分析的作者,态度上应当是平和公
允的。即便是写作判决书,在我们所处身的英美普通法制度下,判决书的写作要求
和风格也是态度平和,证据充分、分析细致和推理严密的,曹先生或许以为这种盛
气凌人是以其价值态度的正义性为後盾的。不过我还是相信,多数有着民主素养的
读者更会赞同本世纪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关於“我所奉行的正义就是宽容的正义”这
句格言,在进行批评和讨论时比所谓“义正词严”更重要的是心平气和地遵守逻辑
规则。曹先生或许还认为坚持这种写作态度正是体现和验证着言论自由原则,我不
知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只是提供了一种有关法律义务的底线,它不仅理当
与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达规范相辅相成,而且也并不排斥活动者接受一般道德
感或道德意愿(如前文提到的推己及人等)的约束,按照已故美国法学家富勒的说法
,这种关於意愿的道德虽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却与法律的普遍含义相关,当有人
未能达到这种道德要求时,我们不是控告他而只是加以惋惜甚至蔑视,法律固然无
法强迫一个人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优良程度,道德却应有这样的要求,批评言论是否
构成诽谤是一个如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问题。我显然不认为曹文有涉此一层
面,但若就道德层而言,读者则有理由对曹先生写作态度的优良程度抱以较高期待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读曹先生的文章,很难相信他果真像自己申明的对马克思主
义那样深恶痛绝、对民主自由那样真诚向往,因为正是他的作品态度和风格最难使
人不与被他批判的那种共产主义实践发生联想,而此种态度与风格若得以盛行,绝
难想像那会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局面,人所共知,构成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尊
重和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曹先生当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个人的写作事项
与风格,但是这种选择游戏如若一再有意无意地妨害他人的选择权利而不稍加自律
的话,那至少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