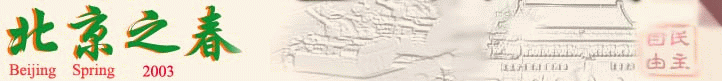自由民主主义,还是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
——《告别革命》评论
顾昕
这本以对话录为体裁的书,基本上记录了李泽厚自一九九二年流亡之後的一些政
治和历史见解,但它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
首先,这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并不是探究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旨在表达一种意识形
态立场,即“反对革命”。具体而言,这本书的主旨是对近现代中国强调革命、贬
低改良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重新评价,为改良(改革)翻案。同时,生产这种“翻
案”性质的“历史学话语”的目的之一,就像中国历史上(例如最近的文化大革命中
)的种种“翻案史学”一样,是为当下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提供理论
上的论证,同时也暗含了对当代中国海内外的民主运动的反对。
第二,由於上述主旨,这本书极少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进行经
验的讨论,而主要是对“革命”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
革命”可以说是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无论是经验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研究。但
是,在对革命进行价值判断(亦即进行规范性的讨论)时,这本书的作者自外於国际
学术界,对革命有关的研究置之不理。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的中
国倒不奇怪,但是令人不解的,现在是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而且本书的两位作者均
在国外。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不少中青年知识份子对这种对於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置之不理的学风加以痛斥,提倡学术规范化,同国际接轨。从规范化的角度来看,
李泽厚、刘再复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极低。
第三,不能说对话体裁有碍高质量的学术写作。但是,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却
是以北京人“侃大山”的方式在讨论问题。不仅论题漫无边际,而且前言不搭後语
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刘再复在正文第六页上批判西方社会压抑人的个性,使人
成为广告和技术的奴隶;而在第九页上他又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国家的发
展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人潜力的基础上而且获得了成功的国家。”人们不禁会问:一
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地方,其潜力又如何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此外,作者在少
有的几处文献引用时也不严谨,例如在第289页上,刘再复在谈到“天人合一”的概
念时说它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义》:“以人类合天,天人合一”。实际
上,此处原文应该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第四,这本书中有不少地方是自吹自擂,例如刘再复在该书的序中援引甘阳的话
吹捧李泽厚比哈贝马斯还了不起,而且强调甘阳说此话是认真的。在另外的地方,
该书又对大陆另外一些文人进行攻击。这类攻击恐怕只有对大陆知识份子界的各种
意气之争有切身了解的人,才会觉得有趣。
既然本书的学术价值很低,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对此书进行深入
的评论。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即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来讨论一下李泽厚
“反对革命”的看法。笔者认为,李泽厚虽然作为世界级的思想家还不够格,但是
他却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反对革命”的看法在一九九零年代
的文化中国世界中,是一个颇为时兴的看法。在中国大陆,所谓“新保守主义”(中
国特色的“保守主义”)盛行。相当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们热衷於证明中国式的“渐
进主义改革路线”优越於发生在东欧和俄国的民主化道路。在海外,不仅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受到贬抑,就连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开始受到各种非议。清王朝末期
所进行的立宪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也在一九九零
年代初发表文章,严厉检讨了近现代中国知识份子激进化的倾向。总之,主张渐进
主义蔚为风气。那么,李泽厚“反对革命”的看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是在什
么思想框架中产生的?或者,他对於政治和历史的看法,同他在一九八零年代发展
的所谓“主体性实践哲学”是否有思想上的关联?这些观念史上的问题,还是值得
讨论的。
就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笔者已经在拙著《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
识份子》(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後,笔
者又撰写了题为“Subjectivity, Modernity and Chinese Hegelian Marxism”(主
体性、现代性与中国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论文(发表在近期的Philosophy E
ast and West上),进一步讨论了李泽厚的哲学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契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其宗旨是为中国现代性的确立建立一个哲学基础。在这个话
语中,处於中心位置的是一个整体主义式的“审美——实践主体性”概念,它同时
包含人类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又包含人类客观的物质生产、政治制度、历史发展
等等。在这个“审美——实践主体性”中,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
知识与道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等等,都完整地统一在一起。这个大统一俨然取
代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理念”,以及卢卡契思想中的“总体性”(totality)。
它具有浓厚的目的论的特色,整个人类历史在李泽厚眼里被看成是最终走向这一人
类目的的“历史积淀”过程。在这个黑格尔——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康德
作为第一个全面提升了人类主体性的思想大师而受到李泽厚的高度重视。但是二元
主义者康德在他眼里又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黑格尔和马克思;这就是说,康德的主体
性思想必须要由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补充、修正。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李泽厚也发现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审美——实践主体性”思想,
即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於对审美主体性的
高扬,只要对这些精华进行马克思主义式(不言而喻,这当然是李泽厚自己的马克思
主义,而不是中国官方正统、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就可以为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建构提供思想原料。笔者称李泽厚的这种传统观为“
审美新传统主义”。
对以上的概括,除了一些细节外,很多论者都表赞同。但是,很多海外的华裔学
者往往愿意认为,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出於政治考虑,一旦他们
脱离了没有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他们就会转而信奉自由主义。那么,一九九二年
李泽厚流亡海外之後,其思想是否有很深刻的改变呢?对这一点,台湾学者黄克武
,基於对本文所评论之书以及李泽厚开始流亡生活後在海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和
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良,不要革命’”(发表在《中国时报周刊》美洲版,
一九九二年)的解读,持审慎的肯定结论。黄克武认为,李泽厚自一九九二年以来,
已经开始摆脱他以前的一些黑格尔主义式思想框架,接受自由民主思想;但是,这
一过程是缓慢的、不彻底的。黄克武解读李泽厚的概念框架是一个所谓“转化”舆
“调适”之两分法(dichotomy),由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最先
提出。依照这一框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想传统(可能全世界的政治思
想传统)被大体划分为两个类型:即转化型和调适型。转化型的知识分子主张以一套
高速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世界,以达到“拔本塞原”的目的;而调适型知识分子则
倾向於认为现实主义,主张小规模的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革命,反对不切实际
的全面变革。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属调适型的,而欧洲大陆政治
传统,即从庐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则属於转化型的。前者是改良主
义的,而後者崇尚革命。
一九九四年黄克武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梁启超前後期的思想变化进行了研究,认
为梁启超在一九零三年前後经历了一个从拥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参见其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九四年二月)在一篇即将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题为“论李
泽厚思想的新动向:兼谈近年来对李泽厚思想的讨论”的文章,黄克武断定李泽厚
正在经历与梁启超类似的思想转变,即从转化型思想转向调适型,也就是说从黑格
尔式马克思主义传统转向密尔式自由主义传统(Millsianism)。他从李泽厚的新作(
尤其是《告别革命》)中发现了一些“新动向”来证明他的观察。最重要的证据就是
李泽厚明确地反对革命,颂扬改良(改革)。李泽厚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自由、民主
、多元论,认同民间社会,赞扬邓小平的以及他所继承的中国的“使用理性”的传
统。所有这些言论似乎都证明李泽厚在放弃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式的转化型革命传统
。
黄克武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海外知识分子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知识分
子的思想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於是会产生不少一厢情愿式的看法。依照笔者的
观察,黄克武的结论值得商榷。问题的关键是,黄克武的分析框架过於僵硬,不足
以让我们理解思想世界的复杂性。转化型和调适型这种区分,表征英国和法国政治
思想传统的区别是勉强可以的,但是却不足以表征德国思想传统的复杂性。事实上
,就我们所关心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传统而言,所谓转化型和调适型思想传统中的
一些要素可能同时存在於一种思想体系之中。黑格尔主义就是如此。黑格尔主义包
含了历史目的论、乌托邦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认识论等成份、这些显然属於
黄克武等所说的转化型思想类型。但是由於其辩证法,黑格尔主义同时包含革命性
和保守性两个特征。从历史上看,黑格尔的思想在其身後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
黑格尔主义右派,另一个是黑格尔主义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後一种思想
发展中得以孕育。黑格尔本人,尤其是晚年,似乎也很少有革命的热情,乃至Herz
en曾经嘲笑黑格尔不敢到政治的海洋中去搏击,而只是在美学的内湖中游水(大意)
。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改良的分支,即通常所谓的“
修正主义”,或称“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E
·Bernstein)。虽然,修正主义式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不同,但是以某种
方式把两者捏合(不是有机的结合),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在下面时叙述李泽厚式的
捏合。简言之,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反对革命的立场,并不同坚守黑格尔主义式
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矛盾。渐进主义同转化型思想并非不相容。黄克武等似乎忽略了
某种渐进主义式的转化型思想之存在的可能性,这样他在李泽厚新著中看到了接近
英美式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在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中照样可以存在。
首先,我们谈李泽厚对经济的看法。在李泽厚的“审美——实践主体性”概念中
,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这被李泽厚视为“实践”的基础方面
,虽然他自己的哲学著作更多地喜欢讨论哲学、美学等等意识形态问题。这样,他
赞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经济主义的解释,视为“吃
饭哲学”,同时认为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告别革命》,
第15、18页)。由於李泽厚简单地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差别理解为前者以政治为本,
後者以经济为本,所以他依照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毛泽东,赞
扬邓小平(《告别革命》,第二章)。
像许多深受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份子一样,李泽厚对现代经济的
运作和经济学几乎是一窍不通。依照辩证法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他想当然地认
为,只要抓住经济这个根本,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从苏联、东欧到毛泽东的中国
,其根本问题,就是所谓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在他看来,搞计划经济、国营经济
,就是抓政治,而搞市场经济就是抓经济。只抓政治,不抓经济,显然违背了马克
思主义经济主义的原理,李泽厚当然会反对。李泽厚还把这样的指控用在袁世凯身
上,指责袁世凯“根本无意於建设,只一心想当皇帝”(第70页)。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简单化。事实上,恐怕没有人
相信苏联、东欧的领导人和毛泽东不想抓经济。问题在於,他们当时都认为,以市
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计划经济则会更
有效率。同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仅能带来更高的效率,而且还能带来更大的
平等。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看法并不显得荒谬。世界上有许多杰
出的头脑赞同这样的看法。甚至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彻底崩溃,在中国也已
经面目全非的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制度要比当前任何一种资本主
义国家(包括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存的经济制度更为有效率,更重社会公平,因
此更为可取。但是,李泽厚却像大多数事後诸葛亮一样,认识到市场对於经济的重
要性,於是他进一步把抓经济同重视市场等同起来(断定袁世凯主观上不关心中国的
建设,至少无法获得历史史料的支持。实际上,没有一个皇帝,哪怕是昏君,不希
望他的王朝国泰民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泽厚对市场的运作有真正的、哪怕是肤浅的了解。他反对
“完全的竞争”,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以计划经济为辅”,“多种所有制形式
共生”等等(《告别革命》,第113,43页)这种大空话同已经过时的、必须在旧书店
中才能看到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看法一模一样,同陈云派的说
法也处於同样的思维框架之中。事实上,中国大陆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家,包括所
谓“体制内的经济智囊们”,几乎完全完全抛弃了这种中国马克思主义式的经济学
思维。
我们前面提到,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也包含经济的层面。但是,由於他
对经济学不在行,於是他只能用极为空洞的“辩证法”把修正主义者的经济主义观
点同他自己运用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对美学、哲学和文化的讨论捏合在一起。如果说
他在後一方面的某些见解还有一些意思(但也矛盾百出)的话,那么他在前一方面的
讨论可以说大多是陈词滥调。
第二,关於历史必然性的看法。李泽厚在其一九八零年代的著作中就有不少表面
上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在其近作中,这类说法似乎更多。他更多地谈论个
人和偶然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并且批评
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一书强调“深层历史结构”对历史事件的决定
性作用。(《告别革命》,第36—39页)这些言论被黄克武视为李泽厚力图摆脱黑格
尔式的历史决定论,而走向自由主义的证据。但是令黄克武不解的是,李泽厚对显
然具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历史积淀论”深信不移,而且李泽厚也一再宣称历史必
然性是存在的。著名美籍华裔教授邹谠先生也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二
月号)上撰文,赞扬李泽厚和刘再复关於历史偶然性的看法,并比附於当今政治科学
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但是邹谠先生对他们两人对历史必然性的重视却不加一词。
实际上,如果了解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李泽厚上述的言论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这样的辩证法论调在大陆中学的教育就有了。在
这种教育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不同的方面,但是没有人彻底否定历史必
然性的存在。一般而言,必然的一面被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
补充,但是过於强调必然性一面就会被一些“思想解放”的人士抨击为“教条主义
”。李泽厚有关看法,完全是在这种辩证法式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框架中自然产生的
。他自己就说,“偶然”与“必然”是历史学的中心范畴,云云。(《告别革命》,
第38页)。换言之,李泽厚对历史必然性的“抨击”,完全是在黑格尔主义式马克思
主义内部的一种见解,同西方自由主义者(例如卡尔·波普尔、伊赛亚·伯林等等)
反对“历史必然性”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不一样。因此,在这方面,笔者完全看不出
李泽厚有向所谓自由主义调适型思想传统转变的迹象。
第三,关於历史的目标和实现历史目标之方法的看法。黄克武承认,在历史的目
标上,李泽厚还有某种乌托邦主义的成份。事实上,李泽厚对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给
出全面系统的阐述,但是他对审美——实践主体这一概念的描述,基本上可以视为
对其目标的具体解释。简言之,这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境
界,是没有人的异化的境界。像很多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达到这一最终的目
标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理想国”。西方社会也
“处在种种严重的异化状态中”(《告别革命》,第6—7页)。但是,这一目标毕竟
是存在的,而且李泽厚显然认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实践哲学”为人类走
向这一目标提供了哲学指南。
李泽厚不仅确定了人类走向的目标,而且还就社会政治层面,指出了达致这一理
想社会四个程序性目标:即“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李泽厚特别指出,这四者是大致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大致的时间(历史)顺序。
”(《告别革命》,第24页)有不少人(例如郭罗基先生)反对这四个程序,提出各种
别的方案。他们的批评,至多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为他们都是历史必然性观念的
坚定信奉者。
从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泽厚的渐进主义根本没有丝毫脱离黄克武
、墨子刻所说的“转化型”思维方式。李泽厚不仅告诉了我们“转化”的目标,还
告诉了我们“转化”的具体步骤。他对人类的理性,或者说对於他自己的理性,有
着海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令人遗憾的是,李泽厚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方
面的素养太差,否则他说不定会写出一本类似黑格尔《法哲学》(或译《权利国家哲
学》)的书来。在其新作中,李泽厚没有说清楚上述四个程序为什么是“逻辑程序”
,为什么应该是“历史顺序”(在这一点上,邹谠先生在其文章中对李泽厚和刘再复
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但是令人遗憾,邹先生没有看出他们的这一看法的历史哲学基
础。)。
最後,关於英国式经验哲学和自由主义问题。李泽厚在他的书中,包括这本《告
别革命》,经常表示他自己重视英国的经验哲学,重视海耶克、波普尔的思想。他
甚至说,“少来海德格尔,多来点波普尔”。(第53页)这一点似乎可以被用来证明
他有从转化型向调适型转向的趋势。但是,可以说,李泽厚对这些思想的重视仅仅
停留在口头上。他对海耶克、波普尔等人的了解,停留在口号层次。李泽厚从来也
没有就他所理解的英国经验哲学(李泽厚对这个词的用法含混不清,不知道它究竟指
谁的哲学;一般用法是指休谟、洛克、贝克莱的哲学思想,但是李泽厚对这三个人
一向是特别不以为然的)、海耶克思想、波普尔思想等等给出哪怕是粗略的说明。但
是,一旦在他们那里发现什么符合其胃口的东西,李泽厚马上能把他们装进其黑格
尔式马克思主义的架构之中。这一点不令人奇怪,记得有人曾经嘲笑说,在黑格尔
体系中,手套可以变成兔子。那么往黑格尔的筐子中装东西总比变兔子更容易。这
样,李泽厚新著中有较多关於“自由”、“民主”、“民间社会”、“个人独立人
格”等的议论,也就不奇怪了。其实,现在人们在谈论“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
”)时必谈黑格尔。
事实上,李泽厚的基本思想同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最值得重视的是,李
泽厚对於英美自由主义(从密尔到海耶克和波普尔再到伊赛亚·伯林)中最重要的一
个睿识,即思想的可错性(fallibility),也就是墨子刻教授所说的“悲观主义认识
论”,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一点,黄克武认为是李泽厚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此外,
李泽厚经常口头上赞成多元主义,但是他却明显持伊赛亚·伯林所反对的“价值一
元论”,认为所有美好的东西终究会融为一体,而且就在他自己建筑的“审美——
实践主体性”之最高境界中。如果我们了解到李泽厚思想的黑格尔主义特性,对黑
格尔主义有更多的了解,并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他已经开始接受英国式的自由主义,
那么这些表面的矛盾,根本就不构成矛盾。
以上讨论,全部针对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approach)来了解李泽厚关於历史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言论,并没有涉及对李泽厚“反对革命”之看法的评价问题
。关於这个评价问题,笔者只简单涉及一下。首先,李泽厚的看法并不稀奇。笔者
在一九九零年出国学习之前,就在数次大陆知识份子的沙龙中听到“反对革命”的
口号。当时,大家似乎对罗马尼亚式的革命有所不满,对一九八九年学生的激进主
义也不满。笔者对这些不满没有什么异议。现在,许多中国知识份子,甚至包括从
事民运的知识份子,主张改良,和平演变,而反对搞一场革命,一下子推翻中国共
产党。高唱“反对革命”,主张“和平演变”,已经变成陈词滥调了。真正的问题
是,如何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推进中国的制度变迁。
第二,李泽厚关於革命的看法,就像许多喊“反对革命”之口号的其他知识份子
一样,十分简单。随便举例,我不清楚他们对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是否也不满。
在他们看来,“革命”似乎必定意味着激烈的社会动荡、乃至血流成河。作为规范
性(normative)的讨论,许多“反对革命”的人连一个“革命的类型学”都没有给出
。李泽厚也是如此。
第三,我们尽可以贬低辛亥革命,赞扬戊戌变法(改良),而且我们也可以同意再
来一次辛亥革命式(以及共产主义式)的革命对於中国现代化是有害而无益。可是,
我们到此为止,大肆高喊“要改良,不要革命”,也仍然是於事无补。这种口号式
的高见并不能告诉我们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上种种改良都
遭受挫折,为什么中国知识份子不喜欢各种温和的主张,而去拥抱黑格尔和马克思
。如果我们不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仅仅是热衷於进行重新评价、翻案,
那么我们的见解永远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上。
李泽厚对於五四时期的思想史曾经提出一个有名的“启蒙压倒救亡”的说法。既
然他反对革命,他为什么不对五四启蒙运动中激进主义勃兴、革命热情高涨的思想
原因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呢?难道这些现象仅仅是由救亡这一外在政治原因造成的
吗?难道同五四知识份子选择性地接受西方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潮没有关系吗?难道
这些选择性的接受同中国传统观念(不见得是孔子思想,还包括各种中国非正统思想
)的影响没有关系吗?顺便问一问,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快八十年了,现在的中国似乎
没有日本人要割让青岛的救亡问题了,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不大情愿接受西方所谓
调适型的思想传统呢?
一本书的价值在於回答真正的问题,而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在这个意义上,《
告别革命》并不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之所以要评论它,是因为出版这样的书,在中
文世界中似乎是屡见不鲜,而且有时这种书的作者由於某些历史性的、或地理性的
机缘还被不少人奉为“思想家”,从而使思想史的真实不能彰显。□(李泽厚、刘再
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