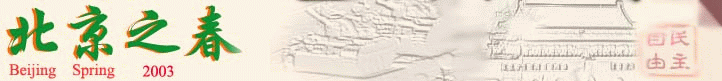反右派运动,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四十岁以下的读者未必知道是怎么回
事。概括为一个简单公式的话,那就是:
一个人说了几句话,批评现状,或批评中共某项政策,或仅仅批评某一个基
层干部。那些话兴许有一些情绪,但也可能全然心平气和。甚至并非当众发言,而
是“向党交心”。总之,并无恶意。
说话的人,还是经过伟大领袖号召和鼓励,本系统、本单位党委领导再三动
员和劝说,许诺“言者无罪”,这才开口的。
那批评纵使再激烈几分,也不会超出他所说的那种现象的严重程度。
说话的人,按照中共的“阶级分析”,也不属敌类,甚至对这个党的事业做
出过卓越贡献。
然而就因为这几句话,这个人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
此丧失他拥有的一切,成为社会主义的贱民。
是不是象卡夫卡笔下的故事一样荒诞?然而这就是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现实
,从此,中国便进入长达二十年的黑暗时代。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做出抉择。
这是不是一种必然,或一种不幸的偶然?
一年以前,即一九五六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天空显得异常晴朗。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它的第八年历史时,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城市里男人
忽然穿起了西装,女人身上也有了颜色,甚至穿起旗袍。电台里播出了阔别多年的
西方古典音乐和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北京的一家电影院开始为大学生放映未经翻
译的西方电影。
人群中也多了一些欢声笑语。在七年的紧张——战争、阶级斗争,无尽无休
的会议之後,中国的肌肉似乎骤然松弛下来。在政治之外也可有一点私人生活,革
命也给个人利益让出了一点位置。
同人有关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在大学中不是已开始恢复
,就是在酝酿之中,哲学已解禁到康德和黑格尔。
法治提上了日程,立法工作加紧进行。律师重新出现。一些重大宪案在认真
复核。
新闻媒体打破多年禁区,开始了对於社会阴暗面的批评和揭露。文学走出了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设定的歌功颂德的疆界,干预社会,把
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本身。出人意外的是居然未遭到压制或抵抗。
同一年前相比,中国简直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政治打
击的搜索对象比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任何一次运动都更加广泛。在北京的那个特别炎
热的夏天里,人们身上是热汗与冷汗交流。经过一九五一年以来的几次大清冼之後
,挖掘新的敌人已不那么容易,积极分子们必须编织“反革命集团”了。
一九五六年的宽松,显然又是毛泽东在那里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但也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在苏联,斯大林死後开始的自由化已进入第四年,
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震惊世界的揭露斯大林肃反罪行的秘密报告而达到
高峰。这个报告文本在中国被列为绝密,只有十三级以上干部才能看到,本来苏联
和东欧的变革之风吹到长城脚下,风头就大大减弱。但这一次却至少在中共党内中
上层引起了大震荡,使开明派愈觉中国也非变不可,保守派则不能不有所收敛。
同一九五六年表面的稳定和繁荣形成对照的,是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一九
五三年起提前搞社会主义以来各种政策弊端所造成的恶果已显示出来。“社会主义
大改造”在这一年刚刚突击完成,生产力遭到的破坏已在城市生活中反映出来:物
价高涨,副食品短缺,农民开始流动。工人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五十余起。肃反扩大
化在党内、机关、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造成的愤怨远远超出历次政治运动。
这样,在中共“八大”上,党的最高层才出现了向毛泽东挑战的动向。刘少
奇和邓小平借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之机,强调集体领导,在新党章中删去
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的“毛泽东思想”,在
“党员义务”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认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种种
问题是毛泽东的“冒进”造成的呼声明显加强。这一动向,使毛泽东震怒,但也没
有办法,只能忍耐一时,另谋对策。
这时,毛泽东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斯大林的问题虽然被赫鲁晓夫以“个
人迷信”的形式提出,实质上却是一整套主义制度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而中国一
九四九以来几乎全盘照搬,也造成了类似的恶果,这是一目了然的。一九五六年当
时中国若想改弦更张,拥有比东欧各国更有利的条件:中共在中国统治的基础要深
厚得多,从而不会因改革而危及政权。东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人民视为苏联
的代理人、本民族的叛徒。中国则相反,把中共看作民族救星。作为一个大国,中
国对苏联具有更大的自主地位,不会象南斯拉夫、匈牙利或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
伐克那样受制於苏联。
我相信当时许多中共党员是曾如此期待的。因而那年夏天听到毛泽东关於“
十大关系”的报告传达时,我才会兴奋若狂,以为毛泽东在经济政策上创造性地摆
脱了苏联模式:“中国终於找到了一条自已的道路”。年底,“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发表(知道是毛执笔),对於他维护斯大林(“功大於过”)虽深感失
望,却仍以为他不会重走斯大林道路。
出於对毛泽东人格与个性的无知,也由於低估了中共内部的保守力量,从而
未能料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会起扭转乾坤的作用。我猜想很多人当时都因此而对
中国前景作出了过於乐观的估计。
大骗局
如若不然,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我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同人听到毛泽
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时,就不会欢欣鼓舞到发狂的程度。
二十几年以後重新翻阅当年的笔记,就感到不解了。在那次谈话中,毛并没
有完全掩饰他的起初思想和意图。比如对於知识分子的蔑视,比如对於後来成为反
右最先打击对象的钟惦/及其“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分量很重的谴责……。
也不是全然没有疑惑。一九五六年三月毛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我正在东
北采访,从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的宣传界党的领导干部那里听到毛的讲话内容。同
一个讲话,竟然会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定毛确想让人来“放”,帮助中共
整风;少数人则相反,觉得毛的讲话中已透露他另有企图。比如关於陈其通等人从
“左”的方面对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下文艺界自由化现象的攻击,多数人信以
为真,少数人则嗅出了另一种味道:毛讲不是真正反对陈其通等人的立场,不过是
嫌他们打草惊蛇,泄露了他的锦囊妙计!
我那时属於糊涂的多数,虽不敢全然否定後一种想法,心里却本能地愿意相
信多数人的反应,甚至因此而猜疑後一种想法是出於那些人本身对於鸣放的抵触。
直到三十年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未能识被这个骗局,以为毛
的“引蛇出洞”的阴谋是在鸣放开始後意外地发现竟有那么多人攻击和否定他的政
绩以後才改变主意,决定反击的。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的“党内老干部十个有九个反对”他的鸣放方针,也令
人以为他是站在革新这一方面的。保守势力反对自由化也是个事实,我就亲自见到
省市委书记对於反官僚主义的抵制。然而谁能想到毛泽东是这种势力的头子呢?
关於这个问题华民先生在最近问世的《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中依据
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的大量言论,证实他从头到尾是在玩弄阴
谋。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四处游说,劝知识分子打消顾忌,大胆地“放”,同时
频频向“自己人”打招呼,“让那些牛头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民主人士的错误
批评“越错越好”,“要让他暴露、後发制人”,“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
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简直就是
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是不错的。
党内并不都姓毛
有一个人(就我所知,也只有这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识破了毛泽东这个阴
谋,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同毛作了斗争的,那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
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阴谋,而是用了一种令毛泽东都难以问罪的巧妙办法
:当毛泽东四处“点火”时,他按兵不动。(五七年一月,陈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泽
东十分恼火的文章,邓拓一拿到,就把它发排到头版头条)。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
守,对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为然。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实大错了
,而实际上他却是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警戒他们不要上毛泽东的当。而毛
泽东却只能骂他麻木,不善於领会他的意图(岂料是领会得太深了),先说是“书
生办报”,後来又骂“死人办报”,反右後终於将他调出人民日报。有一件令我感
恩的事,也能看出邓对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采访时,“左叶事件”出来
了。我有感於中国记者的使命同他们的地位之不谐调,在一个兴奋得不能入寐(鸣
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里,一口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记者这一行”
,寄给邓拓先生,再无下文。六月底,反右开始後的第一次首都新闻界“座谈会”
(实为对右派的讨伐会,第二次就轮到我了)上,邓拓先生在休息时间把我拉到主
席台後,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里,以目示意,一言未发。那也就成了我
们的诀别。我成了右派以後,再也不能见他了。
五十年代中期,象邓拓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多少?主张变革的力量同保守
派的力量对比如何?没有人做这个研究。据我的观察,在党的宣传部门,在新闻出
版界,文学界和教育界,前一种力量肯定已占优势。(这同六十年代以後大不一样
。)关於党和政府的其他部门,由於总的说来干部特权现象还在初期,官员腐败尚
不严重,倘晓以大义,又由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人物出面,这个党在经过一番较量之
後接受一条改革路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党内虽无真正的民主,但党内干部有胆识者仍能享有一定政治自由的空间。
有的事在六十年代以後是无法想象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刚刚得意洋洋地宣告社
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浙江省永嘉县一位二十一岁的县委副书记竟然敢於说出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於包产到户”。这主张居然得到中共省委书记林乎加的赞同,
在“浙江日报”上白纸黑字公布出来,还决定先在温州地区试点,迅速铺开。无独
有偶,在广西的一个县里也出来一位县委书记叫王定的,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後来
,这两位自然双双被打成了右派。
一九五六年夏季,“中国青年报”实行的全面、大胆的改革,首先自然要靠
社长张黎群和全体编委,但没有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人民
文学”事实上的总编辑秦兆阳那一年敢於发表一九四二年以来第一批批判、揭露性
作品并公然配发“这样的作品,我看期待已久了”这样的编者按语,是需要大的勇
气的。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支持无疑十分重要,也还要主管文艺的中
宣部副部长周扬至少并不反对。
从反右的“战果”中也能窥见一九五六年党内确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支持变革
的。从中央司法部、高级法院到各省的司法厅、检察厅,一大批老干部,有一些还
是二十年代的老干部,被打成右派。新闻单位编辑、记者中右派的比率一般在百分
之三十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直至百分之九十,其中大部分是党员。
斯大林给苏联造成的灾害是太触目惊心了,那里的改革已进行四年,对照中
国政治、经济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走上同一条改革之路呢?这
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当我们估量一九五七年中共党内情况时,不能忽略反右派
运动(以及二年以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从组织上到思想上给中共造成
的极大创伤。不能忽略这创伤是两方面的,一是开明力量的被清冼,一是“左派”
党棍的繁殖。
匈牙利灵感和中国的发明
中共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八大,所做的各项决议,据李志绥先生所写,
“令毛泽东大为震怒”,“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
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他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
行动。”
那年十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即匈牙利人民与党内改革家发动的改革运
动演化为武装起义遭到血腥镇压,震动世界。在中国,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全部真相
始终严密封锁,我当时在外地采访,从官方报纸上得到的印象只是最後几天布达佩
斯街头冲突中“暴徒”如何残酷处死公安人员的情景。
毛泽东却有条件了解整个东欧变化的全部真相,东欧的政治变革,最早从南
斯拉夫开始,那是由执政党及其领袖铁托发起的。一九五六年波兰党的领袖哥穆尔
卡主动纠正前人的错误,都未出大乱子。只有匈牙利,死硬的领导人拉科西坚决不
改,这才酿成大乱。
然而毛泽东却不愿引出这样的结论,他对镇压比对改革更有兴趣。赫鲁晓夫
一度派苏军进驻布达佩斯,但下不了镇压的决心,又撤出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莫
斯科坐镇,力主武装镇压,苏联才第二次出兵的。中共对匈牙利人民欠下的这笔血
债,也长期隐瞒下来了。
毛泽东从未认真承认过错误。他甚至还反对别人认错。一九五七年初,他还
告诫过省委书记们绝不能象胡志明那样为越南土改中的错误下“罪己诏”。他坚持
认定,问题出在群众一边。一九五七年春夏,他还在说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不
过是“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广大群众对於新制度“感到还不大
习惯”。这时工人罢工已进入高峰,至少有七个省的农民起来“闹事”,要求退出
合作社或分社,要求供应粮食等,而毛泽东仍然认为是“思想问题”,共产党的政
策没有问题!
匈牙利事件为所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放弃斯大林主义
的机会。东欧各国在苏联控制下不能自主,以致只能是小改或不改,中国有条件独
自行动,中共“八大”已显现这种意图,然而毛泽东却不干。他要利用匈牙利事件
去实现他自己的意图。那就是把改革浪潮和群众的反抗压下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於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
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
在中国发生匈牙利式“反革命暴乱”究竟有多大可能?刘少奇认为只有在四
个条件下才可能:“我们犯长期的路线上的错误”;“处理方法错误了(压制)”
;“反革命利用”;“党内有人领导”。第一个条件确已存在,但关键在第二个条
件,第三、四个条件则尚未出现。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永大纱厂工人发动罢工,手段还相当激烈:把厂方人
员扣留起来作为人质,不解决问题不放人。刘少奇决定“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
报”派人采写和报道。我就是带着这个使命去上海的。这次采写的稿件若能报道出
来,就能使全国人民和中共全党看到那场罢工全然是中共的错误造成:工人被当做
工具,无力保护自身起码的权利;地位比公私合营前资本家时代还不如。基层党组
织已变质,党员享有种种特权,已成为剥夺工人因而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因而,
有反资本家传统的这些工人们把矛头转向从前领导自己斗争的共产党组织。这种恶
变,是在一九五五至五七年不到两年之中完成的。
毛泽东的态度却相反。其实中国的问题早已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并不需要“
鸣放”,你去动手改正就是了。比如肃反扩大化,已是共识,你去平反就是了。苏
联平反了百万件错案,非但未乱,反倒更稳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冒进”问题党内
高层也已定论,只是毛泽东一人反对,因而“八大”上只能吞吞吐吐:既要反保守
,也要反冒进。南斯拉夫和波兰都解散了合作社,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必
解散,把大社改为小社,或回到低级社有何不可?……
面对社会的动荡,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有两个选择,不是改,就是压。毛泽东
既不肯改,就只能压了。但是怎么个压法呢?动用武力去分别镇压各地农民、工人
和学生?那只能激发全国动乱。这时,毛泽东独出心裁,发现了世界政治史上前无
古人的办法:捞到一个政治理由,从政治上采取兵不血刃却能一举压服全国的措施
。这就需要一个敌对力量提供打击的借口,然而可惜正如“中国大逆转”作者所做
的分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有协助中共改正错误之心,却无推翻中共政权而代之的
任何打算。没有,难道不能制造吗?这就是“鸣放”运动的奥秘所在。五七年四月
,毛泽东在杭州告诉省委书记们:让他们放!攻得过火,就让牛鬼蛇神出来闹一闹
。(後来又说: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同时暗示:现在
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後高。如果党内外一起讲,戏
就唱起来了,这样就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在那个舞台上,毛泽东要导演的,就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猖狂
进攻”的戏,戏一开台,发动一场铺天盖地的运动制服一切人的机会就到了。
余音袅袅
反右派运动中首先是右派,其次是具有起码是非感的所有中国人,良知、人
格和人性都受到一次大虐待,大摧残。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是非颠倒,都有受冤枉的好人,然而这一次波及的是非
却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害与国家的兴衰。况且,怎么可能所有提出批评和意见的人
都错了,还不是一般地错,而是——人民公敌!
没有一个右派相信自己是右派,但在强大压力下绝大多数人又不能不在自己
的政治死刑判决书上签上自已的名字。也没有几个人会料到,他会在贱民般的命运
中;度过二十年岁月。六亿人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人想到承担反右派运动厄运的
不仅仅是右派及其亲属。一年以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接踵而来的
是大饥荒,然後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将在这场“革命”中完成他九年前开始的政
治自杀。
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各种後果,非本文所能论及。只想提到一点,即中国人今
天精神上、道德上的严重退化,原因除经常性的制度问题以外,恐怕要追溯到一九
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影响。
四十年前铸成毛泽东大错的原因之一,是稳定与动乱关系上的一个错误逻辑
,似乎纠正错误会削弱他本人的权威与中共统治、从而导致乱局,而镇压或压服倒
可以维持稳定。毛泽东亲自试验的结果是反右派运动固然稳定了局势,却使危机进
一步深化,先是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大饥荒,继之便是文革大动乱。现在以江泽民
为首的中共当局高唱的“稳定压倒一切”,走的还是毛泽东的老路。毛泽东在世时
的毛泽东路线尚且最终埋葬了毛泽东本人,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其结果
为何难道还需要猜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