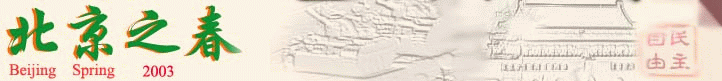五月三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在主权即将从伦敦转移到北京的香港,它的新
闻自由将会面临怎样的前景?这在世界上不光是新闻从业员关注的问题,而为一切
关心自由和民主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人士所瞩目。这也不只是一个有不良人权纪
录的政府是否会履行自己的承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讲,它关系到人类自由和民主
的理想、事业是否能守住一片重要阵地。
就在这一天,香港的三十七家传媒机构的五百二十位中外新闻工作者,在《
苹果日报》上刊出联名广告。他们说,“香港市民一直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
由,其中新闻自由更是香港社会及经济赖以成功发展的一大要素”,而尽管香港《
基本法》列明香港市民於主权移交後继续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然而,他
们担忧,特区政府“会立法削减我们现时享有的自由。”因此,他们“在世界新闻
自由日,距离香港政权移交还有五十九天”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致
力保障香港的新闻自由。”具体说,要求“当局”须以国际法律标准落实《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不干预表达的自由,并承诺不会对传媒施加压力
;在制定或修订任何牵涉到新闻自由的法律时,不削减现有的自由,反而应该增加
香港的新闻自由。
这一呼吁,措辞相当平和、合理,但已有新闻界人士指出,即使这样温和的
声明,也可能不仅为当局所拒纳,反而会被按图索骥式地报复。此说并非无端猜测
,而是有先例在前。香港新闻界上一次联名公开信发表在几年前,後来,名列其上
的记者曾被新华社禁止去千岛湖事件采访。
当然,这类处罚从中国当局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
”,《明报》记者席扬系狱多年,更不用说仍在狱中的高瑜、吴士琛了。
也是在五月三日这一天,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世界十大传媒敌人的名单
,江泽民名列第二,其中特别列举例子称,“江已明确香港在北京接手後新闻自由
将会大大受限。”
从近年北京官员的言行来看,保护记者协会的判断是很有根据的。中南海的
“理论”有时就是跟常识和普遍的逻辑开玩笑。
就拿江泽民本人来说,去年他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强调,香港过
去的繁荣,并不是象有人说的“归功於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体系”,而主要是
香港人民创造的,同时也是与中国内地的支持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分不开的。
其实今天“香港人民”的大部分就是各时期大陆逃亡出来的各种“难民”及
其後代,为什么他们留在老家的同胞仍旧贫穷、落後,并且至今还有人要不惜生命
危险逃来香港,以致要劳驾人民武警不断举行反偷渡演习以阻吓人民?一样的中国
人,两边的最大不同难道不是政治制度及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体系吗?
至於说“改革开放中”内地和香港究竟是哪方支持哪方呢?在资金、技术、
管理及劳力、土地等经济发展的诸“生产因素”中,就稀缺程度而言是哪方更需要
对方呢?
其实江泽民那时真正要想讲的,是贬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司法、新闻”体
系,但这样一来,不是把自己放在“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体系”的对立面了吗
?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经做而大概又想在将来在香港着手做的。因为谁都
知道,这些体系是跟他们的命根子“一党专政”不可兼容的,故必先除之而後快。
实际上,香港在北京正式接管前新闻界已经开始“变了”,根本等不到五十
年。不少传媒负责人在报导和言论上不得不收紧尺寸,生怕得罪中方,这就是所谓
“自律”。有的一改过去的面目和声音,尽量迎合“北大人”,是为“转/(方向
盘)”。更有人自我解嘲地说“/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用来转的嘛!”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不无嘲笑地提到,当拿破伦从流放地杀回巴黎的一段时
间内,首都的报章提到他时,每天的标题都在变口风。今天,历史好象在东方重演
。但不管怎样,北京还得每天向外界保证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无论北
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从中可见,以更宏观的角度看,自由和民主还是占着上风
,仍是主流。
就是在香港,仍然坚守自己信仰阵地的,不仅有那些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名
呼吁的人,更可喜的是,还有些青年学生,在新闻自由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刻,毅然
挑选新闻作为自己的专业、职业和事业。从他们年青而无畏的表情中,人们不难读
到明天的璀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