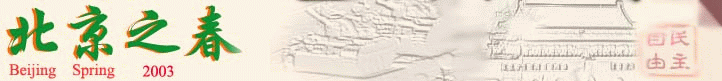三月下旬的华盛顿还有点春寒。
“阿人,你知道吗?杰弗逊说,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不懂英文,你看
看这里写了些什么?”
我与战友李卓人来到了美国总统杰弗逊的纪念馆,这里既庄严又可亲,馆内
灰白的墙壁看似森冷,但翻开历史,这里有自由、民主追求的理想。
我来自香港,我忧虑这些追求、这些理想会日渐减退,日益受到封杀。我站
在纪念馆前恋恋不去。
同是工会人
是个樱花盛放的季节,大伙儿都嚷着机会难逢。在驱车前往樱花园的当儿,
刮起大风。下车时,大家都被吹得摇摇晃晃。我们都以为会花飞满天、一地落叶。
除了风声、树枝的晃动声、人声外,树上一朵朵微红小花,竟没一朵掉下来
。这个光景令我怔怵不已。柔弱纤细的樱花,竟可如此坚忍不拔,韧力可嘉,人类
枉有强健躯壳,但也会随风摆动。是人的力量有限,还是人太被动?
美国的工会人士受尊崇,他们都以做工会人为荣,这是我在美国访问工会时
的深刻感受。香港工会人像吃草出奶的牛,回报少,但仍很拼命。作为工会人,我
对如此迥异的待遇有点感触,尤其是九七主权即将移交,在以社会主义工人当家作
主的中国领导下,工会人的情况会改善吗?我当然感到悲观,我的朋友韩东方,在
大陆的许多工会朋友,都是活的见证。
在美国,我见到工会朋友、传媒朋友、政界朋友,他们都问你希望美国人做
些什么?别人说我们要“唱衰”香港,这不过是个笑话。我告诉他们,我和李卓人
,在香港是有代表性的,我们都是通过选举而获得香港市民支持的,我们对香港是
有清晰承担的。
到美国去的人,还会络绎不绝,也许董建华也会去,但只要你们见到其他人
时,还记得我们这一班仍在香港争取民主人权的人、我们这一班从民主选举而来却
被强权活生生地剥夺了代表权的人,我想,我已达到目的。
心痛令斗志更强
我已飞到加拿大,马丁、华叔还在三蕃市努力筹款。忽听到他们被人围攻、
漫骂的消息,我好心痛。
“无奈这批民族败类……美其名曰访问筹款,实则到海外来摇尾乞怜讨得外
国主子或不明真相的人的欢心而给予一点赏赐。”
“我们奉劝那些历史的渣滓们,你们这种赤裸裸的汉奸、卖国贼的行径已丧
失一个中国人的资格。赶快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不是太侮辱了捐款给我们的热血同胞了吗?这种文革式批斗用词,怎么还有
颜面在今天拿出来用?
过去的经历,使我们习惯了逆流而上,笑骂由人,痛心之余斗志更加旺盛,
我确信今次筹款一定成功。
到达多伦多,马上问捐款情况。存进银行的捐款只有六十加元,购买晚宴席
的人数也不理想。我马上打电话给朋友,四出呼吁。我只能说,人未到,热情未来
,但经过大家多番奔走後,六十席晚宴爆满,收费的论坛及座谈会分别来了千多人
。
深夜做完电台节目访问,回到住处,是广州的星期日清晨五点,我习惯星期
日打电话给母亲。
母亲的牵挂
九十岁的妈妈传来亲切的声音:“你在加拿大呀?不要回来啦,不要回来啦
!”,心里实在难受。
妈一生经历战火、离乱、斗争,没有一天开心过,生下十几名子女,只剩下
我们四兄弟姐妹,父亲不到六十岁就给公安吓死,那真是个荒诞的回忆:我们是个
资产阶级家庭,每次政治运动来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来到我家。那年爸有病入院
,在医院碰到一名街坊,他是右派,大家打了一个招呼,一个说我住楼上,另一个
说我住楼下,右派翌日给公安拉走,爸第二天就给吓死了。
妈从来怕事,还有点自卑。邻家的孩子来敲打我家的门,他们的妈不是责骂
自己的儿子滋扰人家,而是骂资产阶级的门不要敲,妈反而叫邻家的孩子随意敲打
我家的门。
记得有一年,政府动员女青年到海南岛与驻守当地的军人结婚,妈去开会,
哭着回来不让妹妹去。开第二次会时,大会说谁不许自己的女儿去海南岛的就站出
来。阿妈吓得不敢出声,但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不幸之中之大幸,妹妹当时患甲状
腺肿大,逃过这次灾难,她後来也嫁得如意郎君。
八九年三月,我们在北京要求释放魏京生的信给扣押,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我
的名字。妈听不清楚,以为我被扣押,吓得她半死。之後我下广州见阿妈,她叫我
不要“搞野”,她的担忧我了解,但我的行为思想却很难令她明白。她叫我留在加
拿大,她希望我平安,她也可安心。
我好惭愧,我无法令九十岁的阿妈无忧无虑地度余年,心里时常对阿妈说对
不起。
我的香港心结
我碰到的加国移民,有做逃兵的感觉。我说,移民不需要给自己理由,每个
人面对专制政权都有忧虑,反而是还留在香港的人要有他的理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结,我留在香港有我的心结,在加拿大的活动,大家高唱
《狮子山下》、《东方之珠》时,都哭作一团,不管是去或留。
在多伦多的电台节目中,有听众打电话来说我不是中国人。
在关心中国问题上,我绝对是个前线组织者、参与者。早在六七十年代,我
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我参与保钓事件、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我亲赴日本抗议军
国主义复辟,在靖国神社、在日相村山富市出现的终战和平纪念集会上高举抗议横
额。我不明白听众的指责的理据,不过,对不明所以的指责,由它去吧。
粤剧伶人梁醒波曾对我说,有人问他是什么人,他答:“我是新加坡华裔。
”他希望有朝一日青天白日旗的太阳内装有五颗星。他的愿望反映了海外华人对中
国的冀盼。
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中国人,我将香港放在中国的前面有特别的意思,因为在
特别的历史背景下,在一国两制的运作下,在香港我们有特别的身份:建立民主、
自由、法治的香港;无疑地,我对香港前途的关心,多过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关心。
另外,作为香港中国人的特别的质素是:不趋炎附势,不献媚权贵。
在美国,朋友会问如何量度九七後香港发展的好坏。有人会说是看是否落实
法制,有人定的准则是言论自由,又或是民主制度如何。
这些具体及详细情况,外国人不会知道,也很难跟进香港每一件事。我看,
最简单的衡量准则,是李柱铭、司徒华、刘千石、李卓人、刘慧卿的参选资格是否
失去,游行集会是否受到限制,言论与行动是否遭受禁止。□
(原载《明报》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