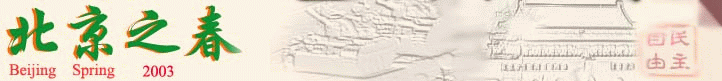本年度诺奖得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Wislawa Sxymborsks)经历过二战
的炮火,从欧洲文明的废墟中站起来之後,一度认同迅速取得政权的波兰共产党并
采用官方倡导的甚至是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她很快就对斯大
林式的极权统治感到幻灭,天主教的忏悔意识使她获得新生,并以犬儒主义的反讽
开始对现代的野蛮和文明进行微妙的解嘲,最後终於以其杰出的反讽术获得诺奖殊
荣。尽管她的诗歌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看看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裂变,对
於曾经同样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束缚的中国作家来说,是
颇有启发意义的。
在文明的废墟上低沉地歌唱
战後的四十年代,辛波斯卡最初在她所在科拉科夫市的报纸《波兰日报》上
发表诗作,第一首诗是《我寻找词语》,时年二十二岁。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
年,她在这家报纸发表了将近三十首诗,开始在波兰诗坛崭露头角。这些早期诗作
大都描写二战中波兰被德寇占领期间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饱经战乱得以幸存的脆
弱的女性,表达自己对民族的负疚感,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忧患和哀伤之情。
辛波斯卡充当了这场历史灾变的见证人和诗的喉舌。瑞典诗人普勒耶尔(Ag
neta Pldijel)在《辛波斯卡题照》一诗中将辛波斯卡誉为历史的预言家卡桑德拉
:
你这营营蜜蜂般的卡桑德拉
试图在废墟——我们习以为常的废墟上为我们歌唱。
卡桑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的女儿,爱慕她的日神阿波罗赐予
她预言的能力作为礼物,由於她的负情,阿波罗以神力对她进行报复:尽管她的预
言将被未来验证,但人们再也不会相信她。她预见到特洛伊将被希腊攻陷,但人民
不听从她的警告。亡国之後,卡桑德拉沦为希腊联军的战利品,作为女奴,最後被
残酷杀害。辛波斯卡在她的《卡桑德拉的独白》中的女主人公在废墟上的内心独白
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
这是我,卡桑德拉。
这是我的灰烬下的城邦。
这是我的权杖和预言书,
这是我的充满怀疑的头。
辛波斯卡早期的《废墟上的歌声》,每一首诗单独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评论
界太大的注意,但是,一九四九年,当辛波斯卡想集结成书,作为她的第一本处女
诗集出版时,其阴郁低沉的情调,遭到官方的评论界的严厉批评,成为共产主义阵
营的雇佣文人的靶的。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规范下,批评家指责
辛波斯卡的诗歌对於普通的劳动人民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她对战争的描写过
於病态地迷恋於人们的内心的创伤,对於新生的欣欣向荣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来说,
这些作品不宜出版。结果,横蛮的政治干扰最终取消了她的出版计划。
自我调整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五十年代初期,不少波兰作家和诗人已经踏上了不归的移民之路或流亡的漂
泊旅途,例如後来於一九八一年在美国获得诺奖的诗人米华殊(Cxeslw Milosx);
另一些诗人,例如後来诗名比辛波斯卡更大的赫伯特(Zhigniew Herbert),对斯
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抗衡是所谓“内部移民”——沉默,或“为抽屉写作
”,以求将来的某一天出版。但是,辛波斯卡既没有必要流亡也不甘於沉默,她重
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态度以适应官方的要求,开始写作政治上正确的或至少没有政
治错误的诗歌。波兰文学史家勒维尼(M.G.Levine)在她的《波兰当代诗歌》中谈
到这一点时颇有微辞。
辛波斯卡自我调整後的这些诗发表在两本诗集中,即一九五二年的《我们活
着的理由》和一九五四年的《问我自己》。这两本诗集被当时评论家视为最富於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这些诗歌中,她的单向的线性思维使她像许多中国
作家一样,以脸谱化的模式写叙事诗,“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叙坏人完全是坏人”
。这种模式,用西方的美学术语来说,就是不能登“悲剧”之最高的艺术殿堂的所
谓“情节剧”(mdlodrama)的模式,惩恶扬善的模式。例如在《老劳工妇女》中,
诗人描写一个年老的妇女讲述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苦受难的生活,她本来就在
悲惨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工作,可是由於怀孕,连这种工作机会也被剥夺了,被解
雇了,她一度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成而得以活下来,却导致胎中的婴儿流产。在
《关於一个战犯的歌》中,诗人愤怒抗议将纳粹战犯从盟军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在
《来自韩国》中,诗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韩战争,尽管她无法亲眼看见,却以一
个目击者的视角叙述美国士兵残酷地挖掉一个韩国老百姓的眼睛的故事。爱憎鲜明
,或诗人的感情的强烈的直接介入是这些诗歌的显著特点。
勒维尼在《波兰当代诗歌》中是这样评价这些社会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的:
“在这些选集中诗歌倾向於刺耳地表达一种对旧次序,对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主
义者的宣传所攻击的当时的其他目标发泄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非常不如辛波斯卡
的一九五六年以後的诗歌”(M.G.Levine:Contemporary Polish Poetry,Twayne,1
981,p.93.)应当补充的是,这些作品同时非常不如她四十年代的处女作。
这些作品中的悲惨的故事可以使读者想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
品。辛波斯卡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人还谈到她在某些方面属於十九世纪,在
另一些方面则属於二十一世纪。当然,在她身上更多的仍然是属於我们二十世纪的
东西。她属於十九世纪的东西也许有好几个方面,她自己语焉不详,但她与十九世
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联系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在《可能性》一诗
中写到各种两相比较她更喜欢的事物时,有一行诗说:《喜欢陀斯托耶夫斯基,更
喜欢狄更斯》,狄更斯就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出生贫苦的
对贫苦的弱者充满了同情的人道人主义者。可见,辛波斯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其主要方面是在揭露而不是歌颂。她所揭露的是资本主义的野蛮,帝国主义的野蛮
。在她的作品中,似乎还没有为波兰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作品或以艺术的形式来阐释
官方政策的应景之作。这一点,无疑要高出许多当年的中国诗人。
告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生
辛波斯卡的这两本诗集从此奠定了她在波兰官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一
九五六年,随着斯大林的神话的戳破和苏联文学的“解冻”,波兰文学也开始“解
冻”了,这股政治冲击波像雪崩一样席卷了波兰,激发了波兰作家的惊醒。他们反
思马克思主义,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辛波斯卡谈到她的学生时代曾经攻读波兰
文学和社会学时,她说:“那时社会学几乎不存在,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还
要社会学干嘛?社会学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我在社会学院只学了一年。”(
见《中央日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可见从那时开始,她对教条化的马克思
主义已经生了厌恶之情。
一九五七年,辛波斯卡终於以诗集《呼喊耶提》将她自己从官方所鼓励的政
治倾向中解脱出来,她重新回到自从四十年代以来使她魂牵梦绕的战争题材,实际
上这也是对那些曾经严厉批评她的共产主义御用文人进行反攻和自我辩解,重新认
同自己在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前的政治观点、诗的美学主张和艺术风格。她回
顾自己的童年,回味她从小受到的天主教文化的熏陶,共产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文化
的冲突在她的心灵深处展开了。在她的创作生涯中,这部诗集对她一生最重要的一
点是,她开始在某些诗作中表现了反讽的态度,尝试相应的表现手法,而这正是她
不断探索日趋成熟以致今天能获得诺奖殊荣的最鲜明的艺术特征。
在她“解冻”以後的诗集《诗》中,有一首题名为《新生》的诗,最鲜明地
反映了诗人的创作态度的历史性裂变。诗人坦然承认,她由於一度相信被共产主义
的统治集团谴责的人们真的是卖国贼或叛徒,因此自己犯了同谋罪,对不起那些无
辜的人们。她宣称,在这些牺牲品面前,她曾经没有尽到自己道义的责任给予帮助
,她现在更加相信诗歌是一种毫无益处的东西,因为诗歌已无法对那些无辜的死难
者给予精神补偿。
作为从来不曾直接介入政治的诗人,辛波斯卡无疑也没有直接参与迫害那些
被官方指控为卖国贼或叛徒的,然而,回归宗教的负罪感却使她萌生了如此强烈的
忏悔意识。这一点,与许多曾经直接参与各种政治运动、迫害同僚却从来不曾忏悔
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真是霄壤之别。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负罪感,才
能忏悔自己的“同谋罪”呢?
当然,尽管诗歌不能对死者给予补偿,但它还是能对生者给予抚慰,成为忏
悔的宣泄口,救赎的精神媒介,不断走向“新生”的自由的象征。这个主题,後来
贯穿在她的诗歌中。例如在《有些人喜欢诗》中,诗人直接表达了她对诗歌的社会
功能的看法:
诗——什么是诗呢?
有许多站不住的解答
在这个问题前面倒下。
我总弄不明白,紧紧抓住
仿佛它是救赎的栏杆。
诗人所说的“站不住的解答”无疑包括被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把诗歌和一
切文学艺术作品视为单纯的斗争武器或宣传号筒的解答。
在现实生活中,像在诗歌中一样,辛波斯卡虽然不直接介入政治,但她开始
真诚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了。
一九六四年随着波兰官方的教条主义的文学理论被创作界和批评界的进一步
否定,辛波斯卡也否定了她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当她回顾自己的创作
历程,编选她自认为依旧具有艺术价值的诗歌时,在一九六四年的《诗选》中,她
仅仅从早期的《我们活着的理由》和《问我自己》中选择了九首诗入集。而其他的
新的诗作,大都表现了野蛮与文明的对抗,或恐怖主义与道德关怀的对抗,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和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及人类难以沟通的孤独的悲剧感
。从情节剧到悲剧的转变,这是最富於复杂进程,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到了
一九七零年,在她新编的自选集《诗》中,早期两本诗集中的作品一首也没有入选
,可见她对自身的否定的彻底
对斯大林的野蛮的鞭笞
在标志诗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裂变的诗集《呼唤耶提》中,有许多诗篇
涉及文明的价值的问题,诗人展示了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文明对野蛮的否定。在《
来自一次不曾进行的向喜马拉雅山的远征》中,她将斯大林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野
蛮的暴君之一,喻为传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邪恶的雪人耶提(yeti)。这种异类
,或说是远古时期的原始人,或说是半人半熊的怪物。在这首诗中,诗人首先展示
了构成现代文明的一系列平凡事物,例如面包、字母和简易的算术。接着她采用反
讽的对比将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高度文明的成就,尤其是文学艺术的成就,与斯大
林个人的罪恶、历史的暴力进程并置在一起:
耶提,在我们中间
并不可能只有罪恶。
耶提,并非一切话语
都是死亡语句。
我们继承希望——
健忘的礼物。
你注意到我们
如何在废墟中生育孩子。
耶提,我们有莎士比亚。
耶提,我们拉小提琴。
耶提,当黑暗降临
我们打开电灯。
邪恶的雪人融化了,我们看到了斯大林这头赤裸裸的野蛮的俄国熊,但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辛波斯卡的一颗带着忏悔和真诚的为文明呼唤的心。
那些野蛮的专制统治者,也许永远不会忏悔,但他们终究会有像雪人一样融
化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