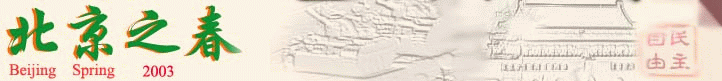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访上海著名民运人士张先梁
继王若望、林牧晨、杨周、傅申奇之後,上海又一名民运人士张先梁先生被
“允许”赴美探亲医病。他刚刚出狱三个月,病体尚未康复,但当他与我紧紧拥抱
时,我感到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从他的身上传递给我。两年前,我曾经阅读过他冒
着风险从狱中带出的上诉书和“狱中诗抄”,被这位硬汉子感动。当我更多地了解
了上海民运人士那些有理有节又坚持不懈的斗争事迹後,对他们又多了几分敬仰尊
重,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多地了解上海的民运人士,我在张先梁先生抵芝加哥後
访问了他……
警车直送虹桥机场
笠:前两个月就听说你要来美探亲,後来又听说中共当局不给你护照,现在你终於
到了芝加哥,与您的女儿相聚。真为你高兴。
梁:我是今年六月七日从上海大丰劳教营释放出来。出来後我就向中共公安当局提
出了探望女儿的申请。这之後一个月,我太太的护照如期拿到了,而我却被拒绝了
。原因是,我在出狱後向上海的民运朋友发出了一个通讯录。这本通讯录是三年前
,即我被处以劳动教养之前完成的。为此,中共上海警方非常恼怒,说我这个通讯
是上海民运人士的名单,我发出这个名单的目的是串联民运人士与政府对抗。我据
理反驳:我们有权利保持联系,交流信息,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他们无奈,但又威
胁我说:你的出国护照我们有理由不批准,原因是因为你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有可能
造成危害。我回答他们说:如果印发了这样一个普通通讯录就使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那么说明这个国家本身就不安全。这就象一个破大厦,本身要倒塌了,你们硬说
是我推倒的,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们在无言可答的情况下,就自己找到了个台
阶说:据调查,这本通讯录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就算了,以後不要再搞了。在这种
情况下,我向美国大使馆提出让我妻子先去芝加哥看望女儿,我就不走了。上海警
方一听说我不想去美国了,马上就把护照送到了我手上。我很快办好了签证。美国
政府的态度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笠:看来你是一个令他们头痛的人物,当听说你不想出国了,当局又马上把护照送
到你手上,这是否有“驱逐出境”的意味?
梁:是的,他们在我出狱到出国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对我进行了严密监控。我外出被
跟踪,与我来往的朋友受到他们的威胁。有好多朋友因为到我家看我而被公安局警
告,有的还被威胁要为他们工作,帮助公安监视我,我深感自己的安全毫无保障。
几天後,我接到了女儿为我订的飞往芝加哥的机票。我准备在九月二十九日赴芝加
哥探亲。
笠:您出境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梁:有的。九月二十八日,在我要走的前一天,上海警方派人来我家,他们要求第
二天我和妻子必须坐他们公安局的车子去机场,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我拒绝了。
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为了避免发生麻烦,为了“保护”我,他们要送我去机场。我
说:你们要“送”,我无权拒绝,我欢迎。但我绝不会坐你们的车。如果你们认为
我触犯了哪条法律,你们可以出示逮捕证,我跟你们走。争执到後来,我坚决表示
,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坐你们的车,我宁可不出国了!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走了。九
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叫了三辆出租车,准备和为我送行的民运人士一同去机场。当
时来了许多民运人士,有余和亮、周建和、商坚城、蔡桂华、倪锦彬、章学麟、耿
心光、徐纪成、徐济人、王涌刚、张汝隽、周其冰等。还有三位被捕民运人士的家
属,他们是,鲍戈的母亲,姚振祥、姚振宪的妻子,还有我的兄弟姐妹,我妻子的
亲朋好友。正当我们依依话别时,十几名公安人员冲进我家,把我的家挤得满满的
,三辆警车停在楼下。为首的一位姓杨的警官要求我出去谈几句话,被我拒绝了,
我说我正和朋友们告别,我没有时间。他们一再地纠缠不休,坚持要我出去,我不
理他们,让他们让开,因为我要收拾东西。半个小时後,他们仍坚持要我出去和他
们谈话,主要内容仍是坚持让我坐他们的车。我坚决不同意,我说:如果你们是将
我驱逐出境,请你们出示相应的法律文件,如果你们要逮捕我请你们出示逮捕证。
你们可以用手铐把我带走,但我绝不坐你们的车去机场。他们说:只是请你到公安
局谈几句话,不耽误你的飞机。而且再三保证只是谈几句话而已。我坚决拒绝。当
时空气非常紧张,来送行的民运人士和家属都非常愤慨,据理力争。我坚决不走。
他们没办法,一个警官说:好,你们一定要这样,那我们也没办法。他拿出两张“
传唤通知书”。我一看,这两张传票时间是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但是没有我和
妻子的名字,是两张空白的传票。我当时就提出质疑:这两张传票是给谁的?他们
说:要你在上面签字。我拒绝签字。民运人士纷纷站了起来,与警察争辩,我的朋
友王涌刚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随便带人走?公安人员很紧张。他们说:
你们不要管这种事情,希望你们保持平静。我们保障把张先梁带走只问几句话就回
来,不会误了飞机。你们也可以继续送行。说了许多好话,我的朋友们生怕误了我
出国,大家表示可以跟他们走。他们又坚持拿走我的行李,又坚持将我的护照和机
票带走。我说:你们不是问几句话就回来吗?机票就不用带了。他们表示不放心,
把我的手提包拿走了。我和朋友们一一握手告别,知道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
到他们。朋友们坚持等在家里,还有许多民运人士还未赶来。
笠:显然,他们是将你押走,不让你和那些民运朋友道别。
梁:是的,当我和妻子上了车,车子一路飞弛,没有去公安局,而是直接奔向虹桥
机场。我质问他们;你们不是说去公安局吗?为什么把我直送机场,他们根本不回
答我。他们把我和妻子带到机场派出所,在那里把我羁押了近四个小时。与此同时
,几十名民运人士,亲朋好友以及仍在坐牢的鲍戈的老母亲,姚振祥和姚振宪的妻
子都从我的家赶到虹桥机场,但直至我上了飞机,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至今想来
仍很难过。
在机场派出所,我一再向他们质问,并要求出去见送行的朋友。他们说,他
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无能为力。他们说这种做法是预防性的,完全是为我好,等等
。我抗议说:“这种做法是践踏人权的。”他们说:我们将你送上飞机你会更方便
。我说我不需要方便,我现在要和我们亲友告别,这是人之常情。我妻子也苦苦哀
求说:“我们这一去说不定哪年哪月见到亲人,你们也是人,难道不理解我们的心
情吗?他们表示要向上级请示,但一去就不复返,直至飞机要起飞时,他们才回来
,护照和机票拿在他们手,十几名公安人员把我们团团包围,由机场工作人员对我
们进行侮辱性的搜查,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开,连朋友送的礼品、我给女儿带的上海
月饼都要打开检查,因为检查的时间太长,飞机迟飞了十几分钟。上海公安当局这
种做法完全是违反人权的,是对公民人权的践踏。
五年铁窗生涯磨炼意志
笠:像这样践踏人权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上海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这
是一个制度问题,您能否向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你自己?
梁:好的。我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出生的,我的祖父张世鎏,字舒良,原上海商
务印书馆的编辑推广科长,曾编辑出版了英文的韦氏大字典,後担任过上海交通大
学的校长,由於祖父去世早,家道中落。我依靠自学读完了安徽淮南矿业学院。但
我喜欢写文章。
笠:是什么促使你投身民主运动的?
梁:当然是共产党的残暴。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间,我在上海民主墙张贴了一
些杂文和诗歌,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後来北京的民主墙运动被邓小平镇压,魏京
生被捕。上海的民主墙转入了地下。但一九八三年共产党将我逮捕,上海中级法院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为了给我罗列
罪名,法庭说我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了七十二篇反动文章。在为自己辩护时我据理
力驳说: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张贴了七十二篇“反
动文章”这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我希望政府将我的“反动文章”登在报纸上,让人
们看看这些文章反动到什么程度。当时连法庭给我指定的律师都认为证据不足,但
我的案子已是内定的。我从上海第一看守所被押送到提蓝桥监狱,後来又被送到白
毛岭劳改农场服刑。五年的监狱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也坚定了我做共产党反对派
的信念。
笠:共产党的反对派大多数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没坐过牢的人也许对共产党
的黑暗还了解不深。一旦投入监狱这种认识很快就有了质的飞跃,所以说,监狱是
民运的“大学”,这一点也许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梁:五年的铁窗生涯证明了您所说的。对待暴政,你不能一味服从,用理性的、非
暴力的、不合作的办法去对抗你才能争取到你应有的权利,哪怕是一小部份。五年
後我被刑满释放,释放後受的骚扰更多。我们不得不把活动转入更隐秘。一九八九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後,上海公安局找我,让我替他们工作,理所当然被我
拒绝,当时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要搬家,搬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
,当然也被我拒绝。我说我女儿快毕业了,她想分配到我所在的静安区工作。他们
说:“如果你不为我们工作,哭的日子在後头呢!”果然,两年以後我女儿不仅没
分配到静安区,而且连户口也没落下,成了一个“黑人”。我女儿就读於北京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才生,曾被评为上海市十名优秀学生干部之一
。毕业时分到上海市科委,但还未报到又被改变分到了矿区工厂。这使我很愤怒。
後来我们开始上书黄菊市长,接着又出现王妙根事件,上海民运人士又一次联合作
战。
上海人权运动的新发展
笠:我听说过这个事件,您是否能详细做个介绍?
梁:当时就我女儿被改变分配方案的事情,上海民运人士都很气愤,联名上书市长
黄菊,对此事进行抗议。在这种压力下,黄菊派人下去调查,并为我女儿报上了户
口,但工作仍不能解决,後来她去广州工作。一九九三年四月份,上海东亚运动会
召开,上海发生了把民运人士王妙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事件。王妙根是一九八九
年民运时上海工自联的领导人之一,八九年被捕时上海的《文汇报》和电视台都报
道过他,後释放。在东亚运动会之前,王妙根被警察殴打後抬头抬脚扔出派出所。
他在愤怒之余,在派出所前,用刀砍断了自己的四根手指表示抗议。上海群众纷纷
指责派出所的残暴。当时警方压力很大,也很害怕,答应解决这个问题,但忽然反
脸,将王妙根押入精神病院。医院的医生对王妙根非常同情,他们偷偷打电话告诉
我王妙根所在的病房和床位。我和另一位民运人士梁庆衡一同去医院探望王妙根,
发现他非常正常,神志非常清楚。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被警方从家里无理带走押
进精神病院的经过。我们也向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和医生询问王妙根的病情。他们吱
吱唔唔讲不出什么病。事後,我向上海的民运人士通报了王妙根的情况。大家认为
,如果漠视政府这样的践踏人权,我们连一点生存的安全感都没有。每天都会被恐
惧包围,说不定哪天失踪或进了精神病院。大家除了轮流去医院探望王妙根外,都
采取了各种方式营救王妙根。公安局唯恐出意外,便把王妙根转移到了上海市公安
局的安康医院,长期关押。为此,我们上海民运人士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政
协、公安部、司法部上书,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王妙根,公安局说王妙根因为砍断
了自己的手指就是精神病患者的表现。我在上书中写道:如果说王妙根因为极度气
愤砍断了自己的手指是精神病患者,那么请问文化大革命中跳河自杀的老舍先生是
不是精神病患者?文化大革命中跳楼致残的邓朴方先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这封信
在各新闻媒体以及政府部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就在六四四周年到来之前,我直接
到市公安局,要求立即释放王妙根先生,并且担保王妙根不会发生影响东亚运动会
的事情。但公安局拒不答应。我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那我郑重告诉你们,今年
六月四号,我们将在上海人民公园召开一个会议,在会上我要讲到王妙根问题。公
安局大怒,强迫我取消这个会议,我说不放人会议绝不取消,这个会我们开定了!
六月三日,公安人员闯进我的家,将我强行带走,并且把人民公园封锁起来
,任何人都不让进,但会还是开了。我被传讯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六月四日夜,由
我女儿张冰把我保释了出来。我回到家後,各国记者和上海民运朋友纷纷打来电话
讯问情况。一个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来电话约明天晚上七点到我家采访,我同意
了。我没有想到,只是这一次记者预约的采访(尚未被采访),使我整整坐了三年牢
。
再入囹圄
笠:您能介绍一下您第二次坐牢的情况吗?
梁:好的。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下午五点左右,上海市公安局派人闯进我家,将我
强行带走。那一天是我生日,妻子准备了许多好菜,我提出让我和家人吃完饭再走
,但遭到拒绝。就在我被押上警车时,那位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刚巧赶到。
我被捕後,上海的民运人士十分愤慨,就在第二天,我妻子同女儿到上海公
安局提出质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民运人士举行了
绝食抗议,鲍戈、王涌刚、杨勤恒和龚星南在上海市政府门前进行了绝食,上海公
安局出动警察把他们四人分别送往不同的公安分局,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绝不妥
协,坚持绝食。而且,上海其他的民运人士纷纷进行抗议,写信上书,找到新闻媒
体透露我被捕的情况。
笠:上海民运人士这种团结斗争的精神真令人钦佩,通过新闻媒体把事情公开会对
斗争更有利。
梁:是的,当时“美国之音”以及许多报纸进行过报道,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上海民
运人士为保障自己免除恐惧的权利的一次大规模活动。
笠:您能否将上海民运的情况向读者做一下介绍?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有
多少人还在狱中?
梁:上海民运的力量主要是从七八、七九年上海民主墙运动延伸下来的,当时有这
样几个比较大的组织,一个是“民主讨论会”,主要代表人物是乔忠林、龚星南、
温定凯(温元凯的弟弟),另外一个是《海燕》杂志,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可思、林牧
晨等,还有一个是《科学民主报》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和桑坚城、宋昌如、余和亮、
周连和,还有傅申奇的《民主之声》、杨周的人权协会等等。当时乔忠林、龚星南
、王辅臣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投入了监狱。後来我们就转入地下,八三年大多被
逮捕,傅申奇被判了七年,我被判了五年。八九民运发生前,我们大多数刑满释放
。只有傅申奇关在里面,我们都采用不同方式支持大学生的民主运动。自我女儿分
配受到不公正对待我们上书市长黄菊取得胜利後,我们又一次上书要求释放民运人
士傅申奇和张汝隽。信是林牧晨起草的。我带头签了名。我们愿意为他们担保。这
次上书不久,傅申奇被释放了。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为此警方很
恼怒。我送王若望先生去美国後,公安人员将我拘留二十四小时,罪名是上书攻击
人民司法制度。在此之後,我们在淮海公园等地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准备进一步采
取行动。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民运朋友家聚会,法国《解放报》记者富兰克林去采访
,第二天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并永远不许他到中国采访。一位日本共同社记者高
天庭子也采访过我们,中国政府竟然把她说成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记者。高
说,我采访过蒯大富等等名人,从来没事。一采访你们麻烦就来了。由此可见,中
国政府把民运人士当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
笠:据您所知,上海的民运人士还有多少关在狱中,他们的现状如何?亲人和孩子
怎么样?您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梁:现在关在监狱的还有杨勤恒、鲍戈、谭子华、戴需中、韩立发、姚振祥、姚振
宪、李国涛等等人数非常之多,这是我们已经掌握的,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那就更多
了。而这些人大多是三年劳动教养期。他们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而且很多家
属连通知书都得不到,亲人便无影无踪了。现在警方随便抓人,有的只给个口头通
知。最典型的就是姚振祥和姚振宪,他们的妻子告诉我说,他们的亲人被带走时只
给了个纸条,写着罪名:偷渡嫌疑。但过了几个月後才口头通知他们被劳动教养,
姚振祥三年,姚振宪两年,罪名变成了“翻录传播黄色录像带。”
笠:这手段太卑鄙了。
梁:是啊。他们的妻子跟我说:她们常年与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
是正直的人,况且他们的家中连录像机都买不起,怎么可能翻录黄色录像带?这罪
名简直是莫须有。
坐穿牢底亦风流
笠:这种下流手段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好在人民已经不再那么轻易地相
信他们。比如说周封锁,他姐姐本来想帮助他逃出西安,後被警方逮捕。他们便逼
迫周的姐姐承认是自己“大义灭亲”,揭发了弟弟藏身之处。当时还真有许多人相
信,等封锁从牢里放了出来,事情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您能否向我们谈一谈你在
劳改营里的情况?
梁:我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被捕,先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在特别审讯室,将
我连续审讯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要求我不再接待外国记者。又要求我揭发其他民
运朋友,被我严辞拒绝,於是他们发给我取保候审通知书,後来又升格为监视居住
,把我转移到上海康复医院,这是市公安局的疗养院,对我单独关押,用了一个班
的武装警察看守我,另外还有三个公安人员。当时我哈哈大笑:我乃一介书生,何
需大动干戈?他们不许我换洗衣服。当时天很热,我身上的衣服都臭了,我抗议无
效,只好采取绝食斗争。主管我的警察从家里赶来,同意我洗衣服。我要求三条:
一、应该保障我的正常生活。二、每天给我放风。三、我有权读书读报。後来他们
答应了两点,只是不答应给我放风。但他们也提出要求,让我揭发其他民运人士,
我拒绝了,於是他们恼羞成怒,发给我劳动教养通知书,我被判三年劳教,将我押
到了劳改集中营。
我当时被关押在“严管队”,他们对我进行非人的折磨。第一,他们逼迫我
面朝墙坐着,一天坐十几个小时。第二,他们让我在大太阳底下出操,还让你做高
难度动作,每天暴晒几个小时後,衣服会被汗水湿透,你会头昏眼花,另外他们有
许多的办法摧残你。看管我的队长姓程,叫程欣欣。我们多叫他程猩猩,这人特别
残暴,为了要恐吓我,他故意轻手轻脚走到我牢房前,然後突然怪叫一声,或走到
你後面一声不吭站着,你一回头就吓一跳,他为了造成这样恐吓的效果,便把皮鞋
换掉穿上布鞋。楼道有灯光,他怕我发现他的影子便把灯泡拧掉,在这样故意的折
磨和恐吓後,我的心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是严管队的一绝。他们每天只发两杯
水,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当时我一言不发,我心想,如果我被你们压垮了,我就
不配做一个民运战士!
笠:那么你用什么办法对付这些折磨?
梁:我写诗。没有笔也没有纸,我就写七言诗,因为容易上口和记忆。不管是出操
、罚坐,我都用大脑写诗,然後把它背下来,比如第一天写一首,第二天就背了下
来,就这样一点点背,诗积累越来越多,待见亲人时,我趁着看守不注意便把诗写
在小纸条上,然後想办法带出来。
笠:当时《中国之春》发表了你的一些反映狱中生活的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吧?
梁:是的,当时我给这些诗起了一个名叫“笼中吟”,这些诗给了我许多鼓舞。比
如清明节时,我就吟了一首《清明》:
满天菲雨满天愁,
广场血水满地流。
老谱袭用十三年,
黑白颠倒几时休。
“革命”坦克街头过,
“暴徒”尸骨均无收。
年年清明年年雨,
可怜白发哭乃儿。
我当时被关押在一坐破楼上,我给自己的牢房取名为“不羁楼”,我在楼上
正好看到队长的办公室,那一天他们在惩罚一个犯人,把那个人吊起来,只让脚尖
沾一点点地面,然後四个警察用四个电棍一起电他,一个队长嫌不过瘾,便在犯人
身上浇上凉水说这样通电效果更好,当时我看到了忍无可忍便向他们抗议,他们走
过来,命令我回到牢房里去,不许看。我说: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你们不是说
对劳改犯要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吗?你们
就是这样对待的?!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他们威胁我:你再看我们就用电警棍电你
!我说请便!我要看看你们是怎样用电警棍对待我的。我站在这里是在牢房里面,
我没有走出牢房,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看?警察没办法就用对讲机告诉楼下,赶
快把人放掉,因为张先梁在上面看到了。他们就把人带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施暴。後
来中队和大队的领导找我解释说这个人打架,不惩罚一下也不行。我说他如果真的
违犯了纪律,打了架,你们可以处罚他,也可以加刑期,但不能用这种残酷的手段
摧残他,这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他们说:我们不会把他搞残的,我们知道搞到
什么程度!这些流氓。
为此,我又吟了一首诗:
囚中病魔有良方,
遥看难友吊西窗。
白皮白纸谈“人权”,
无医无药“回龙汤”……
我诗中的“白皮白纸”系指中共发表的“人权白皮书”,“回笼汤”是指我
自己的尿,在大丰劳改农场,由於我被关进小号,长期见不到太阳,得了风湿关节
炎,还有心脏病和严重的前列腺炎,他们不给我治病,我无医无药,後来只有喝自
己的尿,我甚至在自己的尿中尝到头一天吃的菜是咸还是酸。这是一个古老的疗法
,我整整喝了半年多自己的尿。後来浑身浮肿,生命受到威胁了,他们才将我送进
劳改医院。还没治好,他们又把我送回到劳改营。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我的囚室
就是一个大铁笼子,无窗无门无阳光,冬天到了,寒风刺骨。为了活下去,我每天
在小小的囚室里跑步,做俯卧撑,当春天快到时,我吟了一首立志诗,诗是这样写
的:
江南江北几度秋,为争人权失自由。
万里夜空孤飞雁,千仞冰峰草露头。
秃笔纸头皆搜尽,似割喉管恨不休。
丈夫未遂凌云志,坐穿牢底亦风流。
笠:这些诗是你用血泪写成的,真希望您能将所有的“笼中吟”整理出来出版。我
想问一下,在狱中这几年,你一直坚强不屈,後来终於把牢底坐穿了,但是你有没
有因为压力或不得已做过你不愿意做的事?
梁: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劳改营里,我不断上诉,甚至把上诉书捅到了
海外报刊上,当时劳改营的警方压力很大,他们让我撤回上诉,我坚决不从。有一
天他们找我说:上海市公安局长周达人特批你女儿出国了,你有何感想?另外他又
说:你的上诉马上就驳下来了。你如果撤回上诉,你女儿出国会顺利一些。当时为
了自己的女儿,我被迫答应不再上诉。他们很高兴说:那就这样说定了,不许反悔
。接着就让我见到了女儿。在接见室里,我告诉女儿:你快去办出国护照吧。女儿
说:他们不可能让我出国。我说:他们已经告诉我了。女儿含着泪问我:爸爸,你
是不是做了交换?我听了心如刀绞,但一想到女儿因为不断为我呼吁,也受到警方
监视跟踪,处境也很困难。为了她能获得自由,我不得不违心地做了这件事,但为
了不给女儿心里增加负担,我说:没有这件事,你快走吧,好好读书。上海市公安
局主动给我女儿办了护照,三天就解决了,在我女儿即将赴美之际,陈猩猩队长突
然找我谈话,他逼着我撤回我的上诉。我说,我已经答应你们不再上诉。他们不同
意,一定要马上撤回上诉。他们纠缠了我三个小时,我仍不同意,最後他们阴险地
说:你不要忘记,你的女儿现在是一只脚在飞机上,但另一只脚却还在地上!我知
道就是我女儿登上了飞机,他们也会把她拉下来,就像林牧晨一样。所以我忍着泪
水答应撤回上诉,他们让我写:“我在市公安局领导对批准我女儿出国的感召下,
在劳改队领导的帮助下,我决定撤回我的上诉。”他们欣喜若狂,马上让我签名,
押手印,我按手印时心却在哭,那感觉就像“杨白劳”一样。回到牢房,我痛哭失
声,我前前後後坐了八年牢,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都坚强地挺了过来。但我又
是一个爸爸,是一个经常坐牢对妻子和女儿没有尽到责任的人,这也是我对女儿的
一点补偿吧,而这补偿却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张先梁先生哽咽着说不出话)
永远做共产党的反对派
笠:您不要太难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民运人士也是人,我们和所有的
人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为了他们即使献出生命我们都舍得。我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
绝食时写给自己只有十五个月的女儿的遗书中曾写到:爸爸和叔叔阿姨们所作的就
是为了你们生活得更有尊严,我们就像一群清道工,用生命把路扫得更干净,更平
坦,让你行走而不致跌倒……我想,您所做的一切人们全会理解的,这更说明我们
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梁:这三年的劳改营生活除给我带来一身病痛外,也给我心灵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那时我患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皮肤病、心脏病,我靠锻炼和喝自己的尿直到坐穿了牢
底。出狱後上海的民运人士帮我找医送药,现在又重新活了过来。我只有一个信念
:为了中国能摆脱专制统治,为了中国能迈入民主和自由,我永远做共产党的反对
派,只要一息尚存,便不会停止。
笠:您的勇气令人钦佩,您以上的谈话也会鼓舞海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您能否
谈谈中国的现状以及您对海外民运的看法,我们身在海外的民运人士由於离开中国
时间长了,对每一个刚从中国出来的人都有要听听国内情况和对我们本身的看法,
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哪些事情做得是好的,哪些还有待改进。
梁:好吧,我先谈第一个问题,我对国内的民运情况尤其是上海的民运情况比较了
解。这几年,当局对上海的民运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逮捕人数之多在全国也数
一数二的。但上海的民运人士一直没有屈服过,我们一直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
现在表面上看来改革开放了,一些人富了起来,对民主不那么关心了,但从我接触
到的无论是民运人士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或多或少地向我表达了加速政治民主化
进程的心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下,
将不得不逐步地改进政治形态,人们相信民主选举会逐步实行,在野的政治力量会
逐步壮大。很多人向我谈到这样一个看法,在中国除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大党之
外,第三股势力是正在逆境中掘起,那就是民主力量。人们对这股力量寄予很大的
希望,都认为共产党已经很臭很臭了,国民党在大陆已失去了影响,人们对民主力
量抱有希望,问题是民运力量怎么联合起来,怎么得到人民的认可,怎么减少内部
摩擦。这是人们的希望。
笠:我们民运力量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理念是一个已被世界证明了
的好东西,共产党貌似强大但不代表永远强大,我们现在弱小但代表未来。问题是
我们在道义上是否被中国老百姓信任,民运领袖的个人牺牲精神和个人感召力如何
?你对此有何看法?
梁: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一九九三年以後海外民运的分裂和争吵使我们国内的
民运人士很难过,许多人也表示对海外民运的失望。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国内民运人
士对自己目标的追求。因为现在国内这批人已是久经考验的老民运战士了。从另一
个角度看:海外民运还是起到了它应具备的功能。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海外民运力
量的营救和帮助,我在狱中的处境会更加艰难,因为顾虑这些,当局还不敢对我下
毒手,有时也表示些姿态。比如,允许我的妻子去探望我,带些吃的给我,这些同
海外民运的工作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是有关的。
笠:您能否谈一谈您到美国後的打算?
梁:主要是探亲。能和我女儿团聚我很高兴。另外我希望亲眼看一看美国这样的社
会运作,我也希望有机会同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帮助过我的非政府组织进一步接触,
也希望有机会向海外民运组织及非政府的人权组织表达上海民运人士的希望和要求
,有可能的情况下使上海民运同海外民运的联络渠道能畅通。民运同仁不应有门户
之见。我可以这样说,国内民运人士对海外的任何民运刊物,比如《中国之春》、
《北京之春》以及《中国人权》等,国内都非常喜爱,但就是苦於看不到,我经曾
经收到《人与人权》。你们的工作极富有价值。问题是怎么疏通这个渠道,让刊物
大量地进入国内。
笠:现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均已进入了电脑网络,估计在大中城市的传播
会大大加强。
梁:是的。我们上海的民运力量加上我个人的想法基本上形成了这么八项主梁:一
、言论自由;二、新闻自由;三、废除反革命罪、废除劳动教养,保障人权;四、
释放一切政治犯;五、为六四平反;六、将每年的六月四日定为中国民主节;七、
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放弃一党专制;八、欢迎海外华人及政治流亡者回
国共商国是。这是我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我和
上海的民运人士都会为此目标奋斗到底!
笠:我想,你们这八项主张也代表了海外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愿望,谢谢您接
受访问,并祝你在美国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