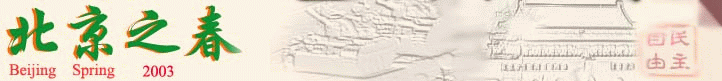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采访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自由亚洲电台《不同声音》节目播出了该台对中
国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先生的采访。
谷季柔: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曾因担任天安门运动学生对话
代表团的常委而遭到监禁。出狱以後经常发表宣场民主理念的文章。一九九五年,
他又响应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的号召,参与了宽容呼吁书的签名,要
求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江棋生在北京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畅谈他对社会
、国家的使命感,而且他待一会还要给大家高歌一曲,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现在就
让我们来听一听。
谷季柔:江棋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不同声音》节目。不久前,就是美国副
总统戈尔还有议长金里奇访问中国期间,中国的警方对您加强了监视,而且有一阵
子把您带走了。是不是请您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呢?
江棋生:在戈尔访华期间,他们派人对我监视和跟踪,在戈尔访华最後一天
,他们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半,估摸着戈尔睡下了,他们把
我送回家中。而金里奇议长率代表团即将到达北京的前夕,他们把我带离北京,到
了河北易县。
谷:他们有什么理由把您带走呢?
江:理由当然是很好听的啦,“咱们是打过多次交道的了,也算是朋友啦,
春暖花开,咱们找个地方轻松轻松,放松放松,去旅游一下。”
谷:去旅游一下?他们真的带您去旅游了吗?
江:这倒不假。由他们找了一家宾馆,一直到金里奇代表团飞到上海以後,
三月三十号,他们从河北开车把我送回北京,呆了整整三天吧。
谷:您觉得他们带您去玩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吗?
江:哈哈哈!玩是玩,但主要目的当然是不让我和金里奇代表团的任何成员
有当面交谈的机会吧。
谷:这次他们去了几个人呢?
江:四个人。
谷:四个人接待您一个人去玩?
江:对。不过,应该说句实话,他们这些陪同人员还是注意礼貌待人的。
谷:那您有没有同他们谈谈您的感想、您的想法呢?
江:有时候我谈,我说我对你们上头作出决策的人采取这样一种隔离我的措
施,我觉得是不符合法律的,但是对你们这些在第一线执行陪同任务的人我能表示
理解,因为你们是吃这碗饭的。在三天里我们天南海北谈了不少。
谷:当您对他们说:您也知道,他们陪您去玩目的是为了与外宾隔离,他们
有什么反应呢?
江:他们不能明确地认可,但是也没有办法反驳。
谷:这种情况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江: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以往的话,就是在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
克林顿夫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往往把我弄到派出所隔离起来。
谷:那么这次您知道还有哪些人被警方带走的呢?
江:我听说在戈尔访华期间,包遵信、周舵他们也被带到一个风景区小住了
几天。
谷:如果在金里奇访华期间您没有被带走的话,您本来打算采取些什么样的
行动呢?
江:我自己不会有太多行动的。但假如金里奇代表团他们打电话到我家里,
希望到我家里来看看,我会表示非常欢迎的;或者他们要我到他们下榻的宾馆聊一
聊我也是会去的。我想这是法律给予公民的权利嘛!至於执政当局这么害怕不同的
声音,我觉得很纳闷,你只让人家接触官方的一家之言,岂不是偏听则暗?你也让
人家听听民间的不同声音么,这没有什么坏处。
谷:当局是否认为把你们同外宾隔离,外宾就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的想法了呢
?
江:我想主要还不是这一条。主要是这个政府它很要面子。假如一个外国的
官方代表团,或者在他们眼里是官方代表团(在我看来议会代表团并不是官方代表
团)居然让他们见到了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件事情本身官方心理上会觉得很过
不去,觉得太丢面子似的。主要是这种心态在作崇。
谷:在您被带走期间,我曾经同您的夫人章虹女士通过电话,她好象以前也
经历过您被带走的情况,她好象蛮镇静的啊!
江:对对对!见怪不怪了。家里警察敲门是常事。我常常开玩笑地对朋友说
,象我这种人应该算中国最自由的人,就是说平时我心里只有基本的法律管着并没
有什么单位管我,要管就是警方,警察我并不怕,因为我没做违法的事。这是一个
自由。第二个自由是思想上的,在中国大陆境内,我大概是最自由的人之一。我跟
朋友说,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就是属於先自由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起码思想
自由,我觉得自己在努力实行,言论自由我自己在努力争取。当然,享有这些自由
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警察经常上门,而且在楼下也看护得特别认真。不过这么一
来,又弄得我们楼的住户挺感谢我。为什么呢?由於警察经常光顾我住的楼,我们
楼自行车基本上没有被偷的,另外也没有溜门撬锁的,我住的十九楼没有一家被溜
门撬锁的,所以楼里好多居民都挺感谢我。有人还对我说,你的规格真不低。就是
说这里保安措施还是挺强的。
谷: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待遇吧。
江:我估计在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之间,警察少不了在我家的周围转悠
,另外我出门他们还得跟着。
谷:这些年来您发表了很多民主方面的主张,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和
想法。
江:我八九年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学位,那么我介入了当时的学潮和民运。众
所周知,这样一场运动被当局开枪镇压了。镇压以後我也被投入了秦城监狱。虽然
我在学潮期间是学生对话团的成员,但我这个人思想上的觉悟是很晚的。说句实话
,我一直到六月三号的下午,都没想到这么个政府会向人民开枪。六月四日的早晨
,我才确切证实他们开枪杀人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完全觉醒了。那么,作为
一个觉醒了的人,你要再装糊涂那是很难很难的了。从那以後,就弄通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已经这样大的改变面貌
了,而我们中国却为什么还发生那些我以前根本意想不到的事。後来我把自己的思
考通过发表文章的方式陆续表达出来。而你敢於表达就是触犯了禁区,触犯禁区他
们当然不能容忍,於是我就得到了被法外监控的待遇。这么多年来,我一方面关注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另外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
说我比较关心六四死难者家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良心驱使我做的。你们大家
都知道的人民大学丁老师、蒋老师就是跟我一个系的,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谷
:丁子霖女士前些时候接受过《不同的声音》的采访,她诉说过她的这段经历,听
众中有很多回响)。另外,我出於关心,也帮助过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我还不停地给在狱中的胡石根先生寄书。除了以上三件事之外,我当然还
得谋生,自力更生。
谷: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和许良英等人发表宽容呼吁书的情形?
江:九五年,联合国有一个国际宽容年,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在的中国大
陆,整体上宽容都很缺乏,尤其体现在官场,他们根本不知道宽容是什么东西。作
为许先生来说,他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史,近十多年来又认真研究了现代人权与民主
理论,他在西安朋友的提议下,很认真地起草了这份宽容呼吁书。我和许先生也是
朋友,是忘年之交啦。这个宽容呼吁书至今我仍然认为是写得好的,也是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官方对此没有正面反应,既没有答复许先生,也没有答复我们签字的人
,反而却把其中一些签字的人,象王丹啊,刘念春啊,投入监狱,而王丹和刘念春
,尤其是念春,现在身体状况很差,令人担忧。我觉得官方的做法很差劲、很不理
智。我自己在宽容呼吁书上签字是良知认可,我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
谷:总共有多少人签名呢?
江:应该是四十五人。
谷:那么您这些年来对政治犯的家属非常关切,请您谈一谈政治犯的家属他
们的生活情况。
江:政治犯的家属一般就是母亲或者妻子,由於她们的子女或丈夫被关进了
监狱,作为一个家庭,经济收入起码差了一半。很多政治犯家属都是一个母亲、一
个子女这样艰辛地度日,有的还要抚养老人,另外还要往监狱里送书、送钱。花钱
不见少,但是收入则明显减少,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谷:政府对他们是否有政治性干扰呢?
江:据我了解,如果家属不吭声一般不会去干扰;但是如果家属觉得正当权
利受到了侵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後,那么政府往往就会去干扰。
谷:但是,中共官方最近一再强调中国没有政治犯呢!
江:他们把那些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和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人说
成是触犯了刑律的人,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成了刑事犯。但在我看来,这
些所谓的刑事犯就是政治犯,因为,这些政治犯在民主国家做了同样的事情,根本
不会构成犯罪,根本是一个公民完全可以做的事嘛。
谷:那么中国最近修改了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改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你
认为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松动的可能性呢?
江:完全不是。在刑法中特别有那么一两条我认真看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在第104之後又搞了第105条。在我看来,第104条第一款完全
包容了第105款,因为“颠覆”就是“暴力推倒”的意思,“推翻”当然也离不
开暴力。这样,第105条第一款就是多余的,而它的第二款稍作改动後可以相应
成为第104条的第三款。於是整个第105款是多余的。而现在把它搞出来,只
能理解为是通过篡改“颠覆”、“推翻”的本意而拿来针对人民的非暴力言论和行
为的。所以我觉得,立这一条是专门用来惩处通过言论、文章、文字表达不同政见
的人,给他们加上罪名。果不其然,在魏京生、王丹身上就反映出来了。他俩都是
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据我看来,他们根本不危害国家安全,第104条套
不上。但是他们都被加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而非暴力能
颠覆什么政府?颠覆就是推倒啊,推倒是用暴力推倒,哪有用嘴巴能推倒的呢?所
以第105条就是用来迫害批评政府的人和主张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人,用来剥夺
老百姓和平方式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所以说修订刑法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松动倒是
更巧妙了。
谷:那么在这种高压控制之下,像您作为一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生活上受
到这么大的压力,那您为什么还继续选择走这条道路呢?
江:我想人总应该有信仰吧,我想一个人如果有信仰、有理想的话,他们人
生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人当然要温饱,但光是温饱的话那跟动物的区别并不大。人
还要求人格的尊严,人还要求精神自由。那么我想,我既然作为一个人的话,如果
为了精神的自由付出一些代价,我觉得值,要不我就不太像人,不太像人的话多活
十年也意思不大。刘宾雁说过一句话:“乌鸦老吃死尸肉,乌鸦你活个六十年;老
鹰却吃鲜活的,它假如活个三十年,还是老鹰活得有意思嘛。”我的意思是,人,
还是要为自己认准了价值观活着,最起码要做自己的主人嘛。现在都快二十一世纪
了,这里还紧着宣传什么大救星啊,救世啊,缺了谁地球就不转了?现在还在宣传
这套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渺小的。我觉得自己第一关心的是要活得像人个人。每个
老百姓都能活得像个人,中国才有希望。我常常觉得可惜的是,当我和普通老百姓
聊天时,他们中间不少人总说自己是草民,总感到无能为力。其实他们可以往前走
一小步,从草民向公民方向走一小步。他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什么时候草民不草
了,草民变公民(不是暴民,也不是主人)了,中国就有戏了。
谷:听说:“六四”以後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能否请您谈谈在监狱里的情
况。
江:八九年九月九日,我被投入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也怪,平生第一次站在
高墙电网之内,心中却并不恐惧,反倒是有些莫名的激动和好奇。心想小说和电影
里的东西,这回果真摊到我头上来了!由於每个大学都有人被抓到秦城,我们在一
起便又开始了新一轮思考和探讨,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收获不小。秦城可
以说是一个大学校吧,我们算了一下,我们是秦城第八期学员,第一期就是胡风。
到了八九年十二月上旬,我们发明了一个敲打暖气管传递消息的办法,因为我们都
懂英语,英语字母是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敲出了字母就有单词,有了单词就有
句子,於是就跟发电报一样,敲半小时都没问题,基本上各个号的情况都能彼此及
时通报,广泛地沟通。
谷:谈些什么话题呢?
江:什么话都能谈。武警和管教他们听不懂,也拿我们没办法。总的来说,
我在狱中心态比较平衡,主要是读书与思考。当失去自由的痛苦和思念亲人的痛苦
出现时,我要自己去想六四死难者,去想那些可能会判重刑的人,要自己不为自己
的处境瞎操心。九一年二月,我在临出秦城时,在牢房里的卫生间门上深深地刻了
两句话:“小住秦城暂作客,不妨随处一开颜”。的确,我和难友们几乎每天晚上
都是要唱歌的。
谷:在秦城呆了一年半,并没有达到改造您的目的啊!
江: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思想这个东西通过监狱恐怕根本不解决问题。思
想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思想的交锋、通过说理才能解决。
谷:那您为了理想、为了目标牺牲了个人的物质生活,忍受牢狱之苦。
江:我觉得追求政治权利、追求其他人权,和享有一些经济和社会权利,这
是不矛盾的。虽然我的生活恐怕还到不了小康,但没有任何人看到我是愁眉苦脸的
,都说我活得比较潇洒,而这不是装出来的,我内心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持不同
政见乃是我自己认的,心里挺踏实,没有必要不开朗。所以在生活方面我并不感到
苦。
谷:您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虽然很艰苦,但是您很能从中找到快乐。
江:我觉得我不悲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确真有一些人能够真正
了解人权理念,能够率先作自己的主了。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刚才的话,我大概是最
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生活的人之一了。我不用说违心话,我不用担心人家给我穿小鞋
,我不用去讨好上司,不用去行贿,不用去送回扣,不用去应酬,不用去累在那些
不应该累的地方。我这是最大的解脱。我当然是冒着高风险的,因为我搞这个事业
,警察经常上门,但是久而久之也就那么回事,我也以平常心对待他们。我在北京
生活是比较丰富的,跳舞跳得还可以,乒乓球也打得不错,还游泳、下棋、旅游。
谷:您在压力之下还能保持这样乐观的态度真是不容易。
江:毕竟社会不同了!我想社会的这点进步也是通过老百姓一点一滴的努力
造成的,也包括我的一点努力。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比较大胆了,很多我们
首都师范大学的普通老百姓就当着警察讥讽他们,说他们警力不够,到我家来干嘛
?吃饱撑的。说得警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胆子不是大起来了吗?以前谁敢说啊
!
谷:这些年来老百姓有很大变化,您认为政府方面有多少进步呢?
江:从官方的理念来说,没有什么进步,社会有一定的进步。因为中国社会
与国际社会扩大交往以後,国外的东西通过电台、通过媒体和资料进来,我想中国
人民也会比较。一比较就容易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於是就出现我认为的“中国社会
的自我解放”。
谷:您认为,民间的这些进步会不会逐渐起到作用促成整个政治制度的改革
呢?
江:会。民间的这种影响就象浪拍堤岸似的,看着一下两下不管用,但是民
心所向总会管用。要是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被唤起的话
,最後会汇总到使掌权的人也会动摇和别无选择。我想这一天是会来到的。只是我
们的明天不能靠等,要主动推进。
谷:您希望在中国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呢?
江:那当然是民主自由啊,这是没得说的。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么。具体说
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因为政治民主化以後最
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人权,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
,包括他们所说的生存权、发展权。这是要保护的。第二,民主化以後,国家权力
的运作得到有力的监督,老百姓会说话,你干得不好,我不要你了。那个时候老百
姓才谈得上有真正的监督权,社会考验相对说来比较公正,比较清廉。经济自由化
,文化多样化,军队国家化,社会才能真正繁荣稳定,得到有序的发展。
谷:邓小平去世以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那么在民
主政治发展方面您对江泽民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江:我只能劝告他,应明了现在的世界民主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谷:那您认为共产党里头的改革势力有多大影响呢?
江:虽然现在主要掌握政权的人不主动搞政治改革,但这不等於这支队伍里
头人权理念和民主倾向不在增长。在共产党里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不少人才
,他们也明了人心所向和现在世界的民主潮流。所以我认为他们会逐步有作为,我
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很看好的。
谷:您刚才说喜欢唱歌。
江:我唱一个“涛声依旧”吧。□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