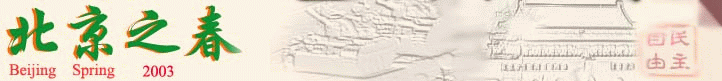伟大的母亲
一 平
一
“不是年青的纪念年老的倒是年老的纪念年青的……”。
每逢这段日子,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使我悲哀,使我不安,似乎有
所歉意在那沉郁的哀痛之後。日子一天天地逝去,一年年地逝去,我竟不知如何面
对那些死者,纪念那殷殷的血迹。虽然,我也总是掉过头去,让身後的时光遮去记
忆和血痕,似乎我由此可以轻松,不见那些不散的魂灵。但时间的流驶却周而复始
,即使我掉过头,却也必又重逢。
记得我离开中国之前,特意去了广场,仿佛有一番心意要诉说,要留在那里
,寄予他们。四周已经寂静,深夜铁兰的天空高远而冷峻。那些星,像不瞑之目,
追责、发问;也像字迹,硬朗,永铭。而那些灵魂在夜空中游荡,阴郁、凝重,对
应地上不见的血痕。它们未有归宿,不会安息。是的,这个世间可以被污七八糟地
遮掩,涂改,甚至被霸占,但是在其之後是一个永恒的、由无数的生命祭奠的世界
,那里必呈现生命的真理和血色。於是我明白,这广场实是中国民族的祭坛,那矗
立的碑石连接着天地之间的鲜血和星光。那夜死去的生灵,即是为中国的未来和希
望所奉献的牺牲。人的历史一向是以人的生命和血来祭祀的,耶稣也只是一个事例
。“神”对人索要的这一残酷而残忍的代价,只是证明人的“道”的神圣性,人存
在的道义和法则乃高於人的生命。为此我不能不尊重那些已作为牺牲的死者,尊重
他们飘行不息,以至义愤,怨斥的魂灵。
他们的血流了,但是却没有对他们的祭奠——当然是不许,这是中国的悲哀
。仿佛他们的血白白地流失,干竭、消逝……
二
几年前,我在国外一家中文杂志上读到她的名字——丁子霖,知道她的事情
,同时也读到她那封著名的信。阅後,我沉默了许久。那位十七岁丰华正茂的青年
,带着他的天真和许多梦想,骤然倒於血泊,不知道那枪弹射在何处,也不知他死
前的悲哀和思念。如此年青的生命,一颗刚刚闪烁光泽的果实,竟然倒下了,也许
还没触摸过爱情,还不知道世事的艰险、权力的黑暗。他不会知道,理想的光照耀
着他。这生命的死已是悲哀,但更多的悲哀则留给了他尚在世的母亲。世上大约没
有比母丧子更大的悲哀。一个中国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
和意义。十七岁的儿子,正是把母亲一生的奠基变为骄傲和信心的时候,但是……
。她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怎么经过那最初的几个日日夜夜?我想到柯勒惠支的那
幅著名的版画《母亲》,我也想到鲁迅纪念柔石的那篇文章,是的,又一位母亲献
出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母亲,而那一夜,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母亲、妻子、家庭
?自然,那些屠杀者永远不会去想那些母亲的悲哀,他们在人性以外。
那一夜,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记得那个夜晚,西单剧场前,一个杠着红旗
冲在前面的学生,他头上扎白布带,一次次地冲向军警,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
杆红旗在前面舞动。我不知道他最後倒下没有。枪声中,有人在不远处倒下,於是
便有一些人去救护,又有人倒下,又有人去救护……。枪弹、火光、坦克履带的轰
鸣……主道冲开了,人群围堵在侧面的路口,以至後面呼喊,高唱国际歌,那歌声
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它也有高尚和尊严。
如果说六月四日,中国的权力是残暴的,那么其後他们就是卑鄙与卑下了。
他们杀戮无辜者,然後施以“暴徒”的恶名。他们欲以说明他们杀得有理,和被杀
的可恶。这是古来屠杀者的逻辑。不仅如此,他们甚而开动国家机器胁迫人们拥护
他们的“平暴”——也就是拥护他们的屠杀和暴虐。这无非是往每个人身上涂染血
迹。杀了人,还要逼迫民众向死难的尸体上弃吐痰液,这是怎样的权力者和屠杀者
?这是十七世纪清兵入关以来,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再一次精神的侮辱和践踏。他们
是如此地习惯於强制与暴力,不仅强暴於人们的生活、行为,也强暴於人们的精神
、道德和思想。一个民族的意志、勇气、精神、良知就是在这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
地强制与暴力中被摧毁的。他们暴虐、侮辱、践踏、毁坏自己的民族是如此坦然、
自得、习以为常。
如同以往,这个权力依然是得逞了。那么多的名人、学者、教授、作家、以
至“民运领袖”……,纷纷出来表示拥护、支持、省悟、甚至作证……。大大小小
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单位公开表示拥护、认错,或口头、或书面。虽然是被迫,虽
然是违心,但终是屈辱,是抹於死者血迹上的污痕。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谅解,但其
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的基本姿态,则即可悲了。它起码证明一个民族良知的被
摧毁(当然这是中国权力近半个世纪暴虐的结果)。知识分子由祭司演衍而来,而
本质是民族文明与命运的祭祀者,这就是它的良知功能。但是当无辜者献上的生命
和鲜血,却没有祭奠,而且……我为死者感到一种被出卖的羞辱。就算是一个普通
人,我们无能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抗议,但还可以表示自己的沉默。我们怎么会怯懦
到那种地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大。中国权力的威慑恐吓,对於中国人已
入骨髓。这是中国权力对中国民族的根本毁害。
三
我没有想到在这场民族鲜血中,最後来承负祭奠之责的是位女子,一个献出
自己儿子的母亲。
当中国的学生、市民英勇地流了鲜血,中国的大多人却掉头推卸、屈从的时
候,她却挺身而出维护死者的血迹。她不是作一个知识者,而作为一个母亲而站出
来。她仅仅是一位母亲,而她的对面则是这个世界最庞大、蛮横的权力,它不仅掌
有军队、警察、监狱,也控制十数亿人的舆论和观念。她的勇气和那位阻拦坦克车
队的穿白衬衣青年是同一的。儿子的死,已使她无所畏惧,无论是敌视、恐吓,甚
或监禁的威胁,都使她义无反顾。她已献出了儿子,无惜再献出自己。简单的母爱
告诉她,儿子是无辜的,他的死需要昭雪。但是当中国已无公义,人们纷纷背叛死
者,屠杀者又对之施以恶名的时候,她的爱与愤升腾了,她孤身起来抗议屠杀,维
护儿子的血迹、荣誉和尊严,维护儿子所献身的理想。没有比这更伟大的母爱。她
的爱和血迹一起扩展,她在黑暗和恐怖中,进出一个个死者家庭,找出那一个个被
弃置与覆盖的名字,珍重地交与历史和未来。她与死者同在,与死者的血迹、尊严
同在。给死者以清白,给善恶以公正,给中国以道义,她为倒下的儿子而要求。她
或许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走上了民族的祭坛,为中国的这场鲜血而祭奠。我们并不
希望流血,但是它已经流了,就应该有所价值和意义,而不白白地消失。他们是为
了中国的未来、希望,为了一个道义、公正、人性、民主的中国而死。他们以自己
的生命为这一理想的牺牲。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还他们荣誉与尊
严。使她们的理想成为中国民族共同的生存原则,它高於个人,也高於现实的利益
,丁女士说:“今天我活着,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尊严
,这是以我的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是我
儿子生命的延续。”这就是牺牲与祭奠的意义。每一个死者都是中国的儿女,他们
的血理所当然地应该流回民族的躯体,给她以希望、勇气、信念和意志。中国当代
历史的悲惨命运,应由他们的死而改变。是的,“一个能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民族
,才是一个有希望创造未来的民族”。但是,反之,在历史上的鲜血中,一个民族
只是更怯懦、世故,远离理想和道义,那么它就没有未来,它的未来只是沉陷和完
结。
四
丁女士在一封信中说:“我不能要求刽子手忏悔,但作为一名死者的家属,
我有权利要求学生领袖们反省。”她有这个权利,学生领袖们面对这个母亲应该有
所反省,这是“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一部分(至於屠杀者,那是另外的事,那是
罪行,是需要审判的)。政治应该接受理性,在任何状态下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都不
应受个人情绪所控制,尤其不该将政治个人化,政治行为关涉国家、社会、民众的
命运和生计,其对此应有高度的责任感。政治家没有权利要求、鼓动,让民众去殉
难,无论是出於什么信仰和主义,这违背人道原则。
我请丁女士原谅,在这里我还要借用同一封信中的另几句话“我是一个大学
教师,不懂什么政治,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大概这就是她说的曾经的“愚昧和沉
睡”。应该反省的不仅是学生和学生领袖,更应该是我们——四十岁至六十之间的
这两代人。本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责任主要应是由我们所承负的。但由於我们“
不懂”“也说不出来”,年青的学生便自觉地来承担民族的命运了,虽然他们还并
不具有这种能力和经验。
中国的社会比不得西方,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更多地负有民族命
运的责任,关心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来传统。当代,中国权力对
知识分子的迫和摧残,本质上就是剥夺他们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的权利,消灭对其
构成互解威胁的力量和因素,以维护它的极权性。“不懂”“也说不出来”(实际
上是推卸)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的现实状况,其社会与政治权利由被迫的被剥
夺,已衍为自愿放弃。知识分子除了做附属的权力技能工具,它的独立、尊严、思
想及它的正常的社会功能均已被消灭。其结果就是一个民族良知的丧失,文明秩序
的丧失。而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也就形成了他们的没有社会权利、位置,没有独立精
神,没有尊严的屈辱人格。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不懂”“说不出”,是一个
可悲的人格与权利的丧失过程。
自然,我们可以放弃,有一千种理由,但由此我们也把混乱和不幸留给了後
人。那本来是我的责任,却由下一代所承担。我们给予儿女以生命,使他们来到世
上,但是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使他们有希望、有前途、有信
心,健康、合理生活成长,这已是悲哀,但是如果我们进而也放弃这种意愿和努力
,那就是失职了。生命就是这样简单,它不因为我们的逝去而逝去,我们的一切或
幸运或灾难,或文明或野蛮,却会转予後人。由此,我们没有理由更多地责难学生
。既然我们不能给社会以公正、道义,且已放弃,那他们就去做了。他们流的血实
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由学生的血也反省自身,这也是“吸取历史血的教训”
的一部分。
丁女士是由儿子的死则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也就是由放弃而走向承负
了——伟大的承负。她实在是一个榜样。事实很清楚,极权社会就是剥夺每个个人
,使个人隶属为权力的仆隶和工具。我们接受这个权力,就是接受它对我们的剥夺
和控制,我们只有在“愚昧”和“沉睡”中才能忘记我们的屈辱和痛苦,忘记我们
作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麻痹我们对这的恐惧和愤恨。这场血应该是一个转变,
它应使我们看清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的屈辱道路,看清我们的现实处境,看清强
权下我们人格的欠缺、扭曲及精神的丧失,尤其是看到我们对中国社会所承负的义
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在这种承负中,我们才能拯救、改变自己,才能复兴这个民族
的良知与文明。由此,那些死者才得以告慰,他们的血才能在民族的身全中重新新
鲜地流淌。
五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报导,刘念春、周国强、高峰为抗议
中国权力迫害异议人士在狱中绝食。刘念春先生八十一岁的母亲,“因对刘念春所
受的残酷迫害感到悲愤”,“在北京家中陪儿子绝食”,“她誓言绝食至这种‘违
法行为’被制止为止”。这是近十天前的报导。现在我不知道刘念春诸人的消息,
也不知道那位老母亲的消息,不知他们的生死凶吉……。这是又一位母亲据我所知
她把自己的两位儿子都已献於中国的民主事业:刘青、刘念春。五十年代以来,这
一个家庭百经磨难。几十年的岁月,一个女人,母亲,已经流尽了她的泪水、血汗
、情感,承负了一切她所能承负及不能承负的不幸和灾难。现在,这位年逾八十岁
的母亲,为了维护儿子作为一个“犯人”所应有的起码权利,为了中共能对“犯人
”有点滴公道,又拿出了她最後的生命。每一个善意的人,每一个有所良心的人,
都会为之感动。我们怎么救护这位母亲?回报这位母亲……?
我不希望中国再有这样的事:由母亲的身边掠走她们的儿女,无辜地投入监
牢,或杀戮街头;不许怜恤死者,让母亲孤单地奔走呼告,且受敌意、恐吓,警察
与监禁的威胁;没有公正、人道法律,母亲为了微小的公道,而交出生命……。生
育、抚养、操劳,生活的艰辛已够沉重,不该再让母亲们承受她们所不该不能承受
的那人为的灾祸和不幸。一个民族应该保护母亲,而不是由母亲来救护民族——这
是它的耻辱。
为此,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公正、道义,有人的自由、尊严,有法律保障的民
主的文明的中国。这是那些洒下的血和母亲们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
(一九九七年六月於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