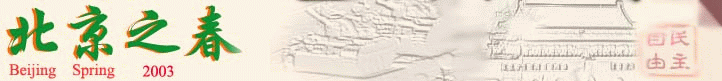自由工人的先驱(续完)
(澳洲) 方园
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令取缔“全红总”
做好杀头的准备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击退了红卫兵大杂烩疯狂进攻的“全红总”总部委员
们,顾不得一夜的紧张和疲劳,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召开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
一次总部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应变。大家一致认为,劫持王振海後立即来砸
“全红总”,是希望在“蛇无头不行”情况下一举产除“全红总”。现在目的没有
达到,中共决不会就此罢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
逃回家乡寻找安全,但难保中共不会秋後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
杀头的准备。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临时合同工争到权益和尊严。就是失败了,也可以
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
因此,大家决定作一次无记名投票,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投票结果,
与会的五十六名总部委员中五十五名选择坚持下去,一名选择撤销总部。紧接着,
大家提出应立即推选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经过选举,五十二票(不含本人)
推选我出任“五人小组”(此时只有四人)负责人;四十八票推选杨政增补为五人
小组成员,仍兼任保卫部长,其余成员职务不动。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总”总部将迁往
广州。
二、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
的准备工作。
三、总部搬迁至广州後,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
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李伯特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
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团二月一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
六、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
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二十九日我将拟好的声明送李晋喧家,请她打印和盖上公章。
三十日下午,李晋喧将打印好的声明送到我处。我一看此声明,大吃一惊。
因为这份声明与我拟的那份声明相差十万八千里。李晋喧拟的这份声明竟是宣布“
全红总”在二月一日自动解散,各地分团自行改名,参加本地区本部门的革命大联
合。临时合同工制度留待运动後期改革。
我问李晋喧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振振有辞地回答,因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
,所以她把二十四日总部会议的六项决议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的声明都送到
中央文革。她说,中央文革指示,要把声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对上对下都
有好处。
我问她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她说,难道大家还会反对中央文
革么?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吗?我很气愤地问她,组织都撤了,还生
存什么?她把脸一板,厉声问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对抗?”
我不愿多和她争论,立即叫秘书余洪珠通知所有没有外出的总部委员到我的
办公室开会,大家来後我把和李晋喧的争执向大家报告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所
有的人一看李晋喧的那个声明都发火了。杨政要李晋喧把印好的这份声明全部交出
来。李晋喧从她手提包拿出大约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敢反对
中央文革?我早就把声明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广播局的造反派组织)的同志们分
头去散发了,剩下的全在这里。”
杨政把桌子上的声明哗的一声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晋喧面前一伸,说:
对不起,请把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交出来。李晋喧急了,问大家:“大家同
意交给杨政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同意!”这一下李晋喧傻了眼了。杨政问
她:“你带来没有?”她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没有带来。”杨政说:“走,到
你家去拿。”她连忙说“不…不…不在我家……”杨政的火更大了,毛胜年和余云
庆也气得顿足,杨政大声吼:“你耍什么花招?你不交出来小心你的安全!”李晋
喧一听大耍无赖:“你威胁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么样?”杨政也不理她,叫上
毛胜年和余云庆就走。李晋喧连忙拦住他们,大叫:“杨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许乱
来!”说着和杨政拉扯起来。我上前去隔开他们,严厉地告诉李晋喧,公章印信和
文书档案是必须交出来的,如果你李大姐不愿交给杨政,可以交给我也应该交给我
,因为大家已推选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她看无计可施,才把手一摆,翻着白眼
说:“告诉你们实话吧,公章和档案我早就交给中央文革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
我宣布,从现在起我退出‘全红总’。再见!”说罢,灰溜溜逃之夭夭。从此,我
再没有见到这位大姐一面。
泰山压顶
中共看抓走了王振海整不垮“全红总”,煽动红卫兵砸不烂“全红总”,叫
李晋喧偷天换日撤不掉“全红总”,终於亲自出面了。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於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
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
采取和这个通告对立的的立场。我们又贴出大字报并印发了传单,质问中共:为什
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
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
中共看“全红总”仍然不肯就范,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针对“全红总”
发出《关於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
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
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
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
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
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
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
”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
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处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
、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
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
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
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的这个文件发出後,尚未离京的“全红总”外地委员和北京藉的总部委
员约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开了“全红总”在京总部委员的最後一次会
议。“五人小组”成员金展云、郝维奇和我一起主持了这最後一次会议。
最後的总部会议
会议开始,我们首先讨论了中共取消“全红总”的文件。这个文件中的第三
条指出临时合同工“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临时合同工和正式工一
样“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一条和“江青三条”中的
第一条接近。相同的是这三个文件都定和保障临时合同工参政的权利和平待的待遇
。不同的是官方的两个文件都不提临时工合同工的经济利益。
文件中的第四条,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三条相似,不同之处有两点:
一是不提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提”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
”,可见文件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二是把《三家
联合通告》中第二条中补发工资一点含进去了。因此,文件的第三、第四两条基本
上是《三家联合通告》被阉割後的翻版。这说明了中共为了笼络民心,对“全红总
”代表广大临时合同工所争取的权益也不敢否定,更显示了“全红总”抗争的正义
性。而正义的“全红总”却在同一文件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专横霸道
。它无异於向广大临时合同工宣布:好处只能由我给你,“革命”的特权只能由我
垄断。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争取,只能由我赐予。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国总部鉴於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
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通知分团各自更改组织名字,,进一步整
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北京分团改名後,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
织不散。会议最後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
劳动节在广州汇合。
全国镇压
会议结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红总”成员先後离去。我和毛胜年等待所有总
部成员安全转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贵阳。
“全红总”贵州分部此时已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
李伯特、杨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胜年,和我们正好错过。贵州分部由潘汉发、曹
治忠等一批老工人主持。
三月二日,我和毛胜年在贵阳看见了以牟立善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军事
管制委员会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在这份布告上,将数十个群众组织打
成“反动组织”。基中赫赫头一名的就是“全红总”。这份布告勒令被打成“反动
组织”的基层成员要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登记,而勒令各层负责人必须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并公开宣称要逮捕镇压主要头头。看来,中共并没有以取缔“全红
总”为满足。现在,中共已公然举起屠刀了。
为了保护贵州分部的广大群众,我和毛胜年到了已夺权的贵州省革委保卫领
导小组,指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
相抵触。因为在二月十七日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未将“全红总”打成“
反动组织”,又宣布参加“全红总”的群众为“革命群众”(第六条)。我们告诉
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不仅与中共中央
、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触,而且与中共的宪法相抵触。再说北京市军管会
也擅越了自己权力。它有何权力对其它省份的组织妄加判定。
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二月十七日文件後,觉得
的确与北京市军管会的“布告”有出入。他们安慰我们,要我们向中央反映,他们
也会向中央请示。 我和毛胜年则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当时许多朋友劝我们快离开贵阳去避避风头。但我和毛胜年一一婉拒。因为
我和毛胜年商量,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
好授中共的“畏罪潜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贵州分部的群众。我们还要等待正在为
我们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来,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替罪羊。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贵阳。听说我和毛年已回来,他们顾不得回家
,立即深夜赶到我家。李伯特告诉我,他们已在云南红河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这
次去北京就是准备去把王振海、毛胜年和我等接到红河。他早已买好次日凌晨到昆
明的火车票,要我和他们马上去毛胜年家叫毛胜年准备立即动身。当我们正准备吃
完宵夜出发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我家。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来执行
任务的负责人说,他们是奉中央之令来逮捕我们的。当晚,李伯特、毛胜年、杨爽
秋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
(女)、王秉忠等数十人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等均被关押。此时,全国各地
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则无法统计。
自由的火种
但临时合同工的斗争并未因“全红总”被镇压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顽强
地苦斗。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达镇压临时合同工、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
,并在六八年公开将“全红总”已被捕的负责人判刑,开展了新一波对临时合同工
斗争的残酷镇压,才使波涛汹涌的临时合同工运动,也是文革中自由工运平息下去
。
时间已过去三十年。“全红总”三十年前播下的自由工运的火种并未熄灭。
不论是西单民主墙时期,八九民运时期直至最近,都可以听到大陆工人争取政治自
由,争经济平等的声音。我本人在有所被判刑的“全红总”负责人中被判得最重—
—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了五年徒刑。贵州籍的“全红总”成员毛
胜年被判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
其中除毛胜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七年外,其他几人均坐
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帮”被捕後先後平反。这些人平反後情况如何?
倔强的湖南人杨政(“全红总”保卫部长)平反後从未停止反抗。长沙的官
僚们罗织罪名,使他几次陷狱。直到八九民运前夕,他仍然未重获自由。贵州人李
伯特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就参加了贵州“中国人权同盟”的活动,八二年赴香港定居
,在王炳章创建中国民联时期加入中国民联。李伯特以後在我的帮助下认识了贵阳
浪潮读书会的一批精英。并通过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贵州“启蒙社”的精英们筹
组了中国民联的贵州分部。笔者七八年出狱後筹建了贵州的“中国人权同盟”。八
九民运中,险些儿落入法西斯手中,现在被迫流亡海外。至於“全红总”的领袖王
振海,在八九民运前夕,笔者听说他准备在长沙筹办一所民间大学,不知现在是否
落成?
八、结语: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自由工人运动
什么是造反派
回首流逝的岁月,在无限感慨的同时有更多的反思。在长达十二年的监狱生
活中,每当看见铁窗外的明月,翻滚的思绪就会平静下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
全红总”为什么会失败?三十年後的今天回答这个问题不算太难。但还有更多的问
题值得研究。
我现在谈谈自己本文前言中提出的四个问题的见解:
(一)“全红总”在文革中的抗争算不算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它和当时的
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有何区别和联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它们的
特征是什么。
关於什么是红卫兵运动,海内外史家和论者争议不多,这里从略。至於红卫
兵的运动特征,不论是早期的红卫兵还是“红八月”以後产生的红卫兵,如仲维光
先生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一文中所说,在思想上,以阶级斗争
为纲,敌视一切不同思想,在行为上,狂热的领袖崇拜,血统论的阶级路线,群众
性的暴力行为。
其实,许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毁灭传统文化,伤害无辜人民,破坏社会秩
序,抢劫公私财产的“打砸抢”暴行,都发生在那个“破四旧”的“红色恐怖”年
代里。而红卫兵的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脏造反派头上。事实是,
红卫兵施暴的时候,“造反派多被压制迫害,哪有这种在光天化日下杀人越货而不
被惩罚的特权!红卫兵实实在在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疯狂卫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党
的疯狂党卫军。所以,对这个灭绝人性的红卫兵运动,必须痛加遣责,彻底否定。
关於造反派运动,海内外的史家和论者争议很大。因为对於造反派的定义和
评价,人们就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较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徐明旭先生有“狭义造反派”和“广义造反派”一说,徐先生言,“老造反
派即狭义造反派”,“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新造反派即广义造反派”。徐先生说:
“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邓、胡把两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对的。”
(徐明旭《也谈“文革”及“造反派”》)
刘国凯先生有这样的见解: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众中许多人带着自身的看法、感受、
思索、要求、利益去响应毛及中央文革的‘战斗号召’投身运动。尽管他们在口头
上,甚至在内心上是拥护毛,但其行动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冲击了中共的社会结构,
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击了中共的统治。藉此,我们可以继而进行判定:那些较明
显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众组织便属於造反派。”(《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
》)
仲维光先生说:
“……产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
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
他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则是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於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
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矛头所向的是权利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
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史实》)
应基本否定的“造反派运动”
如果按徐先生的“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我看可以把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诸公叫作造反派了。因为在文革中的“大闹怀仁堂”
事件里,叶、徐、聂、谭、李也曾犯上作乱斗过共干——斗过康生、陈伯达、张春
桥等人。叶、徐、聂、谭、李诸公乃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共干。但叶、徐、聂诸
公并不是造反派。徐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共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的要害,是抹杀了
在文革中斗过共干的人民群众和斗过共干的造反派的原则区别,是把在文革中人民
群众反迫害、反官僚的自发的斗共干的正义行为,等同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为权争
工具清除政敌的奴从行为,而造反派的根本特征,如刘国凯先生言,是响应毛的号
召,换言之,即是奉旨造反。徐先生先後引证并痛加遣责的如“联指”和“四二二
”的武斗,“新华工”掌权後的施暴等等,大都发生在夺权阶段。而人民群众对造
反派的鄙视和愤恨,大都产生於造反派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大搞武斗,殃及无辜
,产生於造反派想做奴隶而终做成了的阶段。至於反资反路线时期造反派们斗共干
,虽然斗得不甚文明,斗得反人权法制,但人民群众看见平常那些耀武扬威的官僚
们威风扫地,心中也有几分快意,甚至参加进去斗他一番。在这里,我不欣赏任何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行径。我只希望在一个现在仍在严重践踏人权,藐视法制的
国度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引导人区别砍下杀人犯的头和砍下无辜者的头的质上
的不同。
所以,笔者希望诸位先进看到,文革中人民群众对成为毛工具的造反派——
这些打手,帮凶的愤恨中,包含了对唆使利用他们的毛主子的更大的愤恨,包含了
对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愤恨。因此,把造反派“响应毛号召”的这一根本
特征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陆人民对文革的集体记意,或者歪曲这些集体记意。由於
造反派“响应毛号召”的根本特征,不论是在批资反路线的阶段和夺权阶段,造反
派的矛头主要指向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造反派斗某些共干的确给某些共干造成很
大痛苦。但和这些共干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来,哪一种痛苦要大一些呢,造反派
在武斗和派争中的确也伤害过无辜的人,但和红卫兵灭绝人性的对无辜人民的伤害
比起来,哪一种伤害给无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损失呢?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
反派同样留下劣迹。我认为红卫兵留下的毁灭文化残害生灵劣迹大得多。但我也决
不会因造反派的劣迹小於红卫兵的劣迹而放弃对造反派劣迹的谴责。再小劣迹也是
劣迹。我对文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给予基本否定的评价。这个“基本否定”的评价
之所以不同於对红卫兵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评价,原因是造反派运动的早期,炮
轰派的抗争确确实实冲击了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极端缺乏民主的沉
闷的社会秩序,沉重地打击了中共的官僚体制。在人民头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上砸
开一个不算小的裂缝,并从这个裂缝中闪射“极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电
光,划破了万马齐喑的寂静夜空。
站着造反的自由工运
和造反派运动相同的是自由工人运动也开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说造反
派们此时是奉旨造反,造当权派的反,那么自由工运人士则是趁机造反,趁批资反
路线之机造中共剥削制度的反。此时的炮轰派、保皇派、自由工运人士大多是没有
成型的组织。自由工运人士大多和炮轰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辩论对峙。那时中共
各地各系统的横的纵的组织和机构大多瘫痪。平常穷凶极恶的基层公安派出所、办
事处的官员和他们的爪牙——居委会的革命大妈们面对这一锅烧开的热粥也是丈二
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是中共建政後控制力最低的时期,也是空气最自由的时期。正
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为自由工人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到了六六年十一月,各地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自由工运的组织——“全红总
”也应运而生。在炮轰派和保皇派严重对峙的年代里,“全红总”被人们视之为既
不“保”又不“轰”的“四不象”组织。但很快人们就明白“全红总”提出“改革
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真实含义——“全红总”正企图解决
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时不论是保皇派和炮轰派中的一些群众,纷纷退出保皇炮
轰组织,加入这个不轰不保,但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会团体。随着“全红总
”组织的急速扩大,自由工运的声势越来越大,远远地盖过了“炮轰”和“保皇”
的辩论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红总”基本主导了当时的运动,直到来
年元月下旬“全红总”被镇压。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对已成气候的“全
红总”,毛周都准备去利用捅烈性炸药了。
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极成熟、极敏锐的搞手。他们从不敢轻视这股自发的力量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
“全红总”封闭了劳动部的次日,江青接见“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的当天发表的
。毛为这个他未曾意料到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叫好,就像他当年为湖南农
民运动叫好一样。他在叫好的同时,也想挥动他那指挥过千军万马,包括正在指挥
他的疯狂冲击队红卫兵的大手,把这股自发的力量纳入他的轨道。“全红总”不论
以它影响全国的规模,不论以它主导过文化革命某一阶段(“反革命经济主义”阶
段),不论以它独特的理论政治纲领,不论以它周密的行动日程安排,不论以它近
千万的庞大群众,不论以它的长达一百天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二七大罢工”、
“安源大罢工”、“五州运动”。巴黎公社也不过仅仅坚持了七十天),它都堪称
是一个自发的、真正的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
在“反资反路线”时期,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
是在毛周联手把自由工人运动镇压下去後,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运动才真
正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主导了文革中的夺权阶段,继而争权武斗,直到在“清理阶
级队伍”中大都被关进牛棚和监牢。轻一点的则回家加入了做家具炼气功钓大鱼的
逍遥派阵营。
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主要区别,第一在於自由工人运动有自己独立
的指导思想,而造反派运动则没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
。第二是自由工人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独立於毛的战略部署的运动,而造反派运动
是毛亲手发动的,按毛的战略部署行动的运动。第三是自由工人运动从始到终都以
争取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为诉求,坚决地反官僚特权,反剥削制度,而造反派运动
一进入它主导的夺权——争权阶段,早期那点反迫害的民主色彩尽失,甚至堕落为
压迫人民的新官僚。一句话,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根本区别在於自由工运
人士是站着“造反”,而造反派们是跪着“造反”。
独立的理论纲领
(二)“全红总”的抗争是否有独立性?“全红总”属於什么性质的组织?
从前一个问题的探讨中,不难看出“全红总”是个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运
动的独立的工会组织。因为它和所有的独立工会组织一样,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
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临时工合同工争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平等。它也和大
多数独立的工会组织一样,对政权和各种权力没有多大兴趣。它希望统治者能满足
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监督统治集团的劳动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
章制度,它代表广大工人为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抗争。它是广大工人勇敢的代言
人。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调节既得利益集团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团的关系
。
“全红总”的抗争完全是自发的和独立的。 笔者说“全红总”的抗争是独立
的。第一,它有完全独立的指导思想。“全红总”的指导思想,是包裹在马克思主
义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
第二“全红总”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纲领。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国工
业化的过程中,工矿企业根据生产规模的变化,产品的转型,季节性的原材料供应
等因素,对劳动力将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变化。有部分工人要经常流动,平衡各部门
劳动力的需求,这是社会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这种合理需求的临时合同工制度
却是不合理的。因为临时合同工制度没有保障这批处於流动中的工人的正当权益。
他们没有工龄,没有福利,没有公费医疗,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视凌辱,
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一旦解雇,就失去饭碗,妻儿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胁。临时合
同工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而工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在五四年
制定的宪法九十一条到九十八条中明文规定必须保证的。
文章说,为了国家的发展,这批工人可以为了平衡社会劳动力的需求牺牲自
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临时合同工与正式工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只有岗位的
流动与固定的差别,而没有人格和尊严的差别,也不应该有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的
不平等。工人阶级队伍不应也不能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不能在工人阶级中制造阶
级。党内最大走资派想利用“两种劳动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制造一小撮
工人贵族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来转移工人阶级和
走资派的冲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临时合同工。工人阶级和新生的垄断资
产阶级的矛盾,是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走资派是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
法西斯主义国家。如果一定要说临时合同工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那么,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文章指出,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建国十七年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中的许多
人仍为温饱而忧虑。而十七年来,已形成一个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打着“全
民所有制”的美丽招牌,占有和垄断了全民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已蜕
变为走资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闪光外衣下是一张张贪得无厌的血盆大口。在走
资派的压迫剥削下,十七年来,劳动人民不论做工务农,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经
济危机中。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而“供不应求”则是走资
派专政社会的痼疾。走资派把“供不应求”解释成购买力上升的繁荣,实际上“供
不应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资料极其短缺,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化。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贫困。“供不应求”决不是经
济繁荣的象征,而是走资派专政社会的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的阴影。走资派专政使
中国社会出现了五年左右循环一次的社会经济危机。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向走资派发
动进攻的号角,中国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来到了。
文章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结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因为时间久远,无法记忆原文。以上仅是大意。从文章大意中可以
看到,虽然受到文革的历史环境限制,在批判走资派的话语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阶级
要真正当家作主的思想内涵。
独立的行动计划
第三、“全红总”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也有自己独立的
行动日程。不论是到全国总工会两次静坐、封闭劳动部、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和游行,全都是“全
红总”自己完全独立的决定,与中共高层无关。与中共高层有关的行动只有两次,
一是进驻全总。但当时江青如果不叫“全红总”进驻,“全红总”自己早有封闭全
总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开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这两次与中共高层有关的
行动占“全红总”行动全过程中很小比例,影响不了“全红总”行动的独立性。再
说,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销毁“联合通报”,“全红总”阳奉阴违,在暗
中大量印发。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自动撤销组织,“全红总”置若罔闻,
我行我素。直到中共当局把“全红总”打成“反动组织”,“全红总”仍然没有停
止自己的抵抗。历史就是历史。“全红总”独立自主为工人争权益,将永远留在历
史上。
争取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
(三)“全红总”是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它和当时中共上层斗争有无
互动关系?
早在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年代,青年期的李伯特和我就已经注意到“工
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的出现和对立了。当时我们认为,经过六
二年以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过两三年放宽政策的养息生存,遭受过“
大跃进”严重伤害的中国大工业发育不良的畸形躯体,已经迟缓地成长起来了。“
工业学大庆”就是中国大工业形成的讯号和标志。“农业学大寨”只不过是以毛为
代表的大农奴主阶级对抗以刘邓周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反映。随着中国大工业
逐渐形成,大工业的一体两面——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成熟。占有生产资料的
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权益了。中共的社会地
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并为这个自称是无产阶级
的垄断资产阶级谋利益。因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特别是觉悟了的一员,
必须为自己争利益。
正是基於这一理念,青年时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机的准备。
文革开始前,《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已经写好。就算毛不发动文革,中共党内的垄
断资产阶级和大农奴主阶级的决裂和决斗是迟早要爆发的。所以,中共上层斗争只
能为“全红总”的出现提供机会,而“全红总”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
物。
利用与反利用
“全红总”虽然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但和中共上层斗争的互动关系是
存在的——这就是中共上层与“全红总”之间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关系。毛刘之争
在“全红总”看来是一个缺口,临时合同工制度也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全红总
”的领导核心早就计划在解决了临时合同工问题後,将提出一系列的劳动、工资、
福利、社会保险、工人的参政权、工人在企业中的管理权等等问题。而毛集团在“
全红总”显示力量封闭劳动部後,通过江青接见,就公开向“全红总”伸出了操控
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红总”去夺全国总工会的权。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
年初那个阶段,毛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毛一贯的手法是树立一个典型,取得点
上的经验,然後推广到面上去。当时,毛非常需要树一个夺权的典型。碰巧“全红
总”这时封闭了劳动部,并决定次日要封闭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一向很不讨毛
喜欢,因为毛一直认为那是搞工运起家的刘少奇的黑窝。毛是靠搞农运发迹的。他
一直对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时如果夺掉这个花瓶机构的大权,又安全又解恨
,何乐而不为?“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动作和夺权的动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经
过敏的毛对“全红总”有了一个极大的误解——他误以为“全红总”已悟了他夺权
战略的禅机,如聂元梓悟了他反当权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组的禅机一样。於是
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但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後的“全红总”并有
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毛以为“全红总”还有顾虑,所以
派出解放军——《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支左”(当时还没有“支左”一辞出
现,但毛应早有派军队“支左”的打算。),并找来了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老革命
陈乃康。广播局的亲信李晋喧也“掺沙子”掺进了“全红总”。以後在文革夺权时
期出现过的一系列花招,此时都在“全红总”提前出现了。老人家想把“全红总”
经营成他的试验田。李晋喧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过伟大领袖的战略企图——
夺权。“全红总”五人领导小组也认真讨论过是否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但王振
海和我明确表示“全红总”的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陷於苦境的临时合同工。我们不
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雇後流离失所,悬梁跳河。我们对夺权当官的确没有兴趣。
当时,《工人日报》造反派头头跑来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红总”配合他们再加
上《解放军报》的邵一海,一举夺下全国总工会的大权。这已经是不久就将出现的
“三结合”夺权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苦苦请求,告诉他们
要夺权他自己去夺。结果,这伙人还是去夺了《工人日报》的权并将之改名为《工
人造反报》。如果当时“全红总”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了全国总工会的大
权,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个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造反英雄了。“全红总”可能被
树成夺权典型了。但是,历史决不会因此改变。了不起王振海变成王洪文。
“全红总”没有成为毛的夺权工具,可能毛认为这伙人太愚钝,有勇无谋。
虽然不满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红总”去做点什么——因为“全红总”的确有些力
量。不讲全国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团,光是北京就有团员五十多万人。还不算(据周
恩来说)上百万的外地来京工人。这百万外地来京工人中大部分是临时合同工——
被解雇了无工可做无饭可吃,走投无路只有上京告御状的饥饿工人。毛当年在湖南
玩过农民运动。他深知一大群饥民聚在一起可能发生什么——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李
自成,当代的彭湃毛泽东,哪一个不是饥饿人民的“天才的创造性的”煽动者和组
织者?因此,毛想利用“全红总”这桶烈性炸药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敌人——周
恩来。
“全红总”既不愿去做夺权典型,又不愿充当炮打周恩来的工具,更可恶的
是“里通外国”——去开什么“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不可饶恕的是偷偷印发
《三家联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可忍,孰不可忍。”只
是为了顾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红总”自动解散吧。如果这次“全红总”
在高压下听话,也可省去不少麻烦。这笔账留到秋後再算吧。可是,“全红总”吃
了豹子胆了,偏偏不听首长的话,胆敢和伟大导师对着干。毛又和周再次结盟,镇
压了“自由工人运动”。周本来想把毛利用的这股祸水,反利用引它冲到毛的头上
去——这是周准备参加“全红总”召开的大会的本意。但是周去开会途中遇剌,不
说对“全红总”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欢了。特别是全国性组织本身就有夺中央
当权派之嫌。中央当权派乃打不倒的国务院总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纵容“全红总”
而不好下手。现在毛同意产掉“全红总”,周趁机把一切全国性组织包括各地造反
派组织来个一锅端。於是就有了“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後毛大为後悔,因为
他好不容易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扑灭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
份的资反路线”所扑灭,第二次被“红八月”红卫兵所扑灭)。他又来了一次大平
反,“二月镇反”变成了“二月逆流”。
不过,这次大平反中却没有“全红总”的份——历史说明了“全红总”和中
共高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镇压和被镇压的关系。
“全红总”浩气长存
(四)“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和当代中国大陆自由工运有何影响?当
前的大陆自由工运人士应从“全红总”的抗争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在於它曾独立地主导了六六年十二月至
六七年元月那一时期的文革造反运动。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谓的“大刮反革命经
济主义妖风”的那个寒冬。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自发的自由工人运动。中国工人
在改革开放中生活品质有了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场经济的建立不能依靠损害中国
工人的利益。如果中共当权者真正愿意为中国大陆工人的利益考虑的话,应该知道
自由工人运动人士决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工运人士是社会中的建设性因素
。它的出现只会增加社会的稳定力量。如果当权者能理性地顺应自然和顺应历史,
自由工运人士不构成对中共精英的威胁。因为自由工运人士在争取中国工人的权益
的时候,懂得尊重其它社会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中共既
得利益集团也应该懂得,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独占。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
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会出现“全红总”这样的独立工会组
织,何况在今天市场体制已经形成的大陆中国?过去的已经过去。生活在一个充满
仇恨的社会并不愉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们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记历史。今
天的自由工运人士应该更加清楚地记得“全红总”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国工人为了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能牺牲自己对一个稳定职业的追求,但不能牺牲自己对稳定收
入的追求。为中国工人争取他们的社会保险和争取他们在企业管理上的发言权,这
是当年“全红总”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今天年轻的自由工运
人士肩上。“全红总”当年同样是年轻一代,为了中国工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中国
工人能真正当家作主,前仆後继,奋不顾身,许多人在监牢里耗尽青春。要做顶天
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饶的奴才,这应该是“全红总”留给後代自由工人运动的
一份遗产。
为了中国大陆的自由工运贡献了青春和生命的先驱浩气长存!
愿神与我们同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