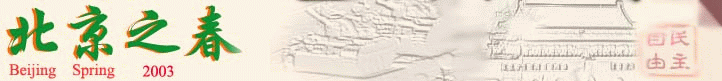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由於反对血统
论对联遭到同班红卫兵的报复。於六六年九月把我和全家强制遣送到山东阳谷县。
那是一个偏远而又贫穷的平原乡村,是山东最贫穷的北三区之一。因此古代出响马
,近代闯关东,以此来求生存。
六八年整个运动的形势趋於恶化状态,我只好和弟妹暂时收起了回北京上访
的计划。为了摆脱随着被遣返而带来的恶运以及寻找就业分配的生机,我决定找个
地方去插队。当时第一批老三届上山下乡的高潮都已於六八年初安定就绪了。在寻
找转插机会的阴错阳差之中,偶然碰到了一位在山西夏县插队的朋友徐铁猊。他当
时正准备和几位县里的知青回村。经他临时安排,介绍了一位和他同村的插队知青
袁一明给我。那是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几盒火柴、一个电灯炮,加上“袁一明
女朋友要来落户”这条贫下中农最感兴趣的理由,我们顺利地在山西夏县堡尔大队
落上了户。
没想到我的到来在第二天就传遍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大家都争先恐後地起来
看“一明的媳妇”。对於在北京长大的那一代中学生和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来讲,
一纸户口。换来的这个称呼所带给我的只有难堪,可笑和无奈。因为“当别人的媳
妇”在当时似乎对我还是很遥远的事。很长时间我都一直是他们津津乐道讨论的话
题,最终他们都象吸毒者过足瘾之後归於平静了。我和所有的知青一样,过着向贫
下中农看齐的生活,做着永远扎根农村的准备。
一个偶然的机会,县知青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得知我曾是北京中学生宣传队的
独唱演员,并参加过大型歌舞“红卫兵战歌”的演出,被他们看成是有文艺天赋的
人才。几个月後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讲解员,当时正在举办“一打三反”展览会
,同时还有另外四名知青也是从不同的大队抽调来的。每月三十元工资,住在文化
馆的集体宿舍中,吃的是集体食堂,每天接待从各村前来参观的村民和知青。
夏县从五十年代起就家家育苗埔,整个县置身於中条山上下的一片林海中,
风景极为优美,是全国著名的绿化县。六九年夏天“全国林业会议”就在此地召开
。来自二十九省市的代表,由中央拨款招待,我再次被从五位讲解员中推荐担任大
会随行的广播员,和大会代表参观绿化成果最好的公社。
不干农活,有固定工资收入,住在相对繁华的县城里……对当时环境的人来
讲已足够令周围的人羡慕和嫉妒了。
一年之後,当所有的借调工作结束後,我回到村里开始和普通知青一样干各
种类型的农活。就在这时我的假男朋友袁一明和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徐铁猊闹
翻了,於是袁一明就跑到大队去揭发我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是为了到堡尔大队来
落户才编出这样一个谎言的。大队书记听後非常气愤,当时就把我叫去质问,并宣
布不分配给我口粮。我当然一口否认,理由是因为我和袁一明吵架了,他才会这样
报复我。书记半信半疑。我立刻找到袁一明向他陈述我所处的困境。因为户口已经
迁入,我也无法再转回去了,如果大队不发我口粮,我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请他无
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他也感到他的行为对我的损害太大了,就同意了我们共同
辩解的一条理由:由於我们之间吵架了的原因……。当大队领导把我们同时叫到一
起对证时,他就按我的安排做了解释。当场书记就把怒火转向袁一明,说他是戏弄
大队领导,袁一明又害怕了,马上又改了口,坚持第一回的说法,弄得大队领导不
知谁是谁非,只好把怒火对着我们俩。我仍坚持以前的说法,袁一明为了澄清自己
又加害我,说我曾在来这前对他进行过威胁利诱,才使他改变了说法。总之最後大
队领导非常生气,说我欺骗大队,宣布不分我粮食,并一状告到了县知青办。当时
有二位领导因重视我而较偏袒我,并下令不得扣发我的粮食,使我得以平安在堡尔
大队享有和其他知青同样的待遇。但是自此以後,就埋下了大队仇恨我的种子。十
分不巧的是县安办三位负责人中,其中一位是和我同村的,此人名叫姜健,性格古
怪而又固执,是有名的难打交道的人。他在大队领导长期的告恶状之後,简直就把
我看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骗子。在他的影响之下,另外偏袒我的那二位安办领导,
也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立场。
七十年代由於一位朋友的轻率行为所引起的连锁反映,使我和很多人受到了
政治上的牵连。以北京外语学校为主体的几位西语系学生被当局以反革命集团的名
义逮捕。所有和他们有关系的人都遭到内查外调和抄家的命运。牵扯面极为广泛,
长达一年左右,我频繁地接待了从河南、内蒙、北京、山西各地来的外调人员。其
中有公安局的,也有地方的。每当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一听到大队广播喇叭喊:“
八队的林森请到大队来一趟”,就知道外调又来了。和我同时受到牵连的有和我同
村的徐铁猊以及邻村的史家大队的武树臣。後来听说县公安局把武的房子给抄了。
当时我立刻整理出所有的书信和文字方面的材料,转到邻村一位朋友那儿,以预防
来抄我的住房。
七一年此案最终有了结局,在北京已分配工作的二位原北京外语学校的朋友
分别判处七年和三年有期徒刑,另一位是打现形反革命监外执行。而其他象我一样
已被发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当时认为已被打入社会最低层去修地球了,也
就不了了之。我当时在堡尔大队的处境可谓雪上加霜,大队领导终於有了名正言顺
的理由来报复我了。
七一年春天,山东省胜利油田文工团准备接受我,当调令下到县安办时,他
们收到的回答是“林森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在农村表现不好,并有欺骗行为”,
这几条把想招收我的人吓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然告吹了。只是让我意想不
到的是:他们不知从哪儿听到那个当时所谓的反动组织“五一六”的名字,就把我
顺口编进去了。
七一年下半年北京总後勤部文工团到山西招生。因文革运动延续不断,一切文
化领域都出现断层现象,而青黄不接的一代正是当时处於二十岁左右的老三届这一
代人。经一位已考入总後文工团的朋友推荐,我和夏县几位知青被通知到专区参加
了考试。当时举国上下只有八个样板戏可演,所以招考人员宣布招考目标是按样板
戏对号录取的。如果没被录取者,而他们又认为优秀者,可推荐给地方文工团。结
果他们只收了一名会弹“黄河钢琴协奏曲”的钢琴演凑员以及一名会唱李铁梅的京
剧演员。我不会唱京剧,被他们推荐给了运城地区文工团。
七一年冬天我正在村里参加冬季修大寨田的劳动,运城文工团一位同志来到
我们村,当他找到我後说明来意,并说已见过大队领导了,遗憾的是大队表示不同
意放我走,理由仍是那铁定的三条:1、表现不好。2、欺骗大队。3、反革命五
一六分子。我听後非常气愤,声明这纯粹是大队领导无中生有的报复。来人由於对
大队领导接待他时的傲慢无理的态度非常反感而产生出对我的极大同情。他问我: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就敢带你走。”我在当时处於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想
尽快地离开此地,以及渴望找到一份就业机会的状态中,当即决定收拾行装和来人
一起去了运城地区文工团。
运城专区文工团的前身是个话剧团。为了适应文工团的发展,又从山西省艺
校和地方上招收了不少舞蹈、戏曲以及声乐、器乐等方面的人才。知识青年中人才
辈出,成了他们重点选拔的对象。
第一批先我进入的是三名男知青,他们是小号袁国华,黑管朱向东,小提琴
钟离满。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因为大家都是相同命运的一代人,又
同是从北京来的。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过许多真诚的帮助,使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由
於生长背景的差异,在团里我们四个人结为一体。
当时团里有两种风格,以本地人为主的演出风格以地方民间色彩为主,他们
演唱当地人喜爱的地方戏曲或民歌。另一种风格自然是以来自大中城市的人以及知
青表现的所谓“洋”风格。那个时候大部分文艺作品被禁演,除了样板戏之外我只
能演唱毛主席诗词。当时团里有一位从山西省歌舞团调来的手风琴演奏员,由於英
雄无用武之地,他从来都拒绝拉琴。我来了之後,他居然成了我的忠实伴奏者,同
时也成了我们北京知青帮的好友。
在後来的一段演出生活中,我又在运城市里结识了从北京外贸学院下放分配
到此地城关小学教书的二位老大学生,一位是学法语的智颖怡,一位是学德语的徐
景田。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这些外乡人紧紧地联结起来了。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过去
,感叹生不逢时的岁月。当然他们也是音乐的知音者。他们是我每场演出时最热情
的观众。在我短暂的演员生涯中,他们曾给予过我极大的鼓舞和勇气。
三个月之後的一次演出,我在後台发现了夏县武装部的刘参谋。当时感到有
点奇怪,但很快我就醒悟到他是为我而来的。果不其然,第二天文工团支部书记通
知我到办公室去一趟。他很婉转地讲了刘参谋昨天的到来是受堡尔大队领导长期恶
状的干扰,县安办不得不采取行动,居然动用了县武装部的刘参谋对文工团领导进
行威胁,如果不放我回大队,他们将上告专区领导,并给文工团贴大字报说他们起
用反革命分子……。书记表示深深的歉意,他们在这种高压之下,不得不屈从了。
团里很多同事对此事表示愤怒。我的三位北京同乡更是为我两肋插刀,带着
我到处奔走,找到地革委会领导,要求“公正”。可是文革中的地区革委会的领导
班子,正是处於“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乱状态,所以事情最後只能维持原判了。
在我即将要离开文工团的时候,我的那位手风琴伴奏,交给了我两封写好的
信。他要介绍我到山西省歌舞团去投考。他说一封是给团长的,另一封是给声乐主
考人员的。他鼓励我不要为此灰心,并说凭我的条件一定会考上的。我就是这样怀
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带着大家的真诚和友情,热情和无私,告别了仅仅三个月朝夕
相处的同事们。在回北京的途中经过太原趁着转车的空闲时间,我带着那两封介绍
信去了山西省歌舞团。因为途中太疲劳,我答应他们回山西时再参加他们的考试。
但我并没有再去。从地区文工团回村後,我意识到继续在堡尔大队呆下去的前景,
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阻止我今後的一切就业机会。当时去省歌舞团,也算是为了回
报朋友们的一番好意吧。
到北京後,我碰到了同在夏县大庙公社插队的黄元。他和我曾同是北京中学
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团的老朋友,也曾是我在北京演出时的钢琴伴奏。
黄元原是北京二十五中六八届高中生。父亲曾任建国初期第一任驻苏联大使
馆文化参赞,母亲留学苏联。他们都是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干部。黄元小时候曾被
寄养在中共早期著名人士李立三家多年。文革一开始,父母就被打成苏修特务、叛
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六八年他随北航附中的朋友到夏县大庙公社、沟东大队、
杨家川小队插队落户。黄元从小受过系统的钢琴教育。由於他插队同村的几位同学
都是音乐爱好者,其中一位将北京家中的钢琴运到他们安家落户的所在地杨家川—
—中条山腰中的一个窑洞中。在那个没有希望的年代里,他们过着自得其乐的田原
浪漫生活。
七一年中学生诗人郭路生和後来成为电影编剧的卢伟、李平分三人结伴,拜
访杨家川时写下了这样的信天游赞美诗句:“姑娘大了十八变,杨家川越变越好看
,杨家川这好姑娘,春风一路百里传……。”
七一年北京总後文工团到夏县招生,黄元是二位被录取者之一的钢琴演奏员
。他居然也经历了一场和我相似的故事。他被录取後,大队公社坚决不放他走。於
是总後文工团就动用了地区军分区司令员亲自到公社大队去动员说服放人。当地土
皇上说:“他出身有严重问题,父母是叛徒、苏修特务。军队怎么可能收这种人呢
?”总後表示这方面他们已请示了军方上级,由於党的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现,不会
成为录取的障碍。没想到土皇上大怒说:“你们若是要敢收他,我们就是不放人,
我豁出去乌纱帽不要了,上中央告你们去……。”军分区也惹不起土皇上,黄元只
能留在山里继续接受贫下中家的再教育。
黄元告诉我他已被宁夏自区治歌舞团录取,为了防止当地不放人,他同时办
了一张宁县附近农村接收他转插户口的准迁证,他转过去後歌舞团可立刻安排他进
团里工作,一切手续只是为了确保事情成功进行。
七二年的农忙时节,我回到村里,一边劳动,一边做何去何从的打算。这时
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说北京传来消息,对六六年遣返原籍的人员有新的政策。据说有
一些人已得到落实回北京恢复了工作。这消息促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决定——转回
我的山东老家。
在我离开夏县的前夕,我去了一趟运城专区。在办完所有的事情之後,顺便
去拜访了那两位外贸学院的老大学生。当我见到智颖怡问起仍留在运城文工团工作
的那三位北京知青近况的时候,智颖怡突然对我说:“朱向东去见阎王了。”我当
时是丈二和尚根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等到他娓娓道出事情的前因後果,我
才明白在我离开之後所发生的一切。当我回到大队之後,文工团相继从几个不同县
里知青中招收了一些人才。其中一位是我们夏县司马公社史庄大队插队的男知青钟
国常。他曾在北京中学生四·三派的大型歌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担
任主要角色的男舞蹈演员。他也是在投考总後文工团之後被推荐给地区文工团的。
当时全国各文艺团体学习和上演芭蕾舞剧“白毛女”。钟国常担任剧中的大春角色
。有一天山西省军区文工团到运城地区招生。运城文工团的一些人偷偷参加了考试
。结果是舞蹈钟国常,黑管朱向东,小号袁国华三人考取。他们三个人是穿着军装
向运城文工团告别的。文工团领导很生气,但是地方服从军队、下级服从上级,而
对这种弱势和强势的竟争,只能是哑巴吃黄莲,随他们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
处流,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改变的真理。何况那一身国防绿曾经是多少年青人梦寐
以求的愿望啊。
他们来到省军区文工团之後,刚开始和大家一样参加排练,政治学习和演出
。过了没多久,领导开始找钟国常和朱向东谈话,由於政审时发现他们的家庭出身
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不能将他们转成正式的军队编制人员。後来他们又被领导
告知:由於他们的反动家庭出身,今後不允许参加部队文工团的任何政治活动,如
政治学习,传达各种上级文件,听忆苦思甜报告……。到後来居然成了批判对象,
让他们批判揭发自已的父母,坦白自己受的反动影响。种种精神和人格上的摧残,
使他们在军队抬不起头来。终於有一天,他们两人被宣判了:脱下军装,解甲归田
——从哪来回哪去。回运城文工团是不可能的了,反而会招来幸灾乐祸的嘲笑。只
有回到原来插队的村里去。
一个清冷的黄昏,在山西省首府太原市的晋祠公园里,人们发现有一个男青
年吊死在一棵大树上,地上放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
文革初期,朱向东全家被遣返原籍农村。这场磨难造成了他母亲跳河自杀,
父亲失踪,生死不明,只有一个年幼的妹妹靠朱向东抚养。
朱向东的死讯传到他插队的村里,全体知青为他的不幸痛哭一场。大家凑了
一笔钱为他送了葬,剩余部分给他妹妹寄去了。
人生的路对当时的朱向东来讲就是这么窄,为了从家庭及个人的不幸中得到
彻底的解脱,他选择了“死”。
我带着“重温旧梦”的情感,写下了这段历史的回忆。时间是无情的,岁月
的轨迹记录着我们未来的憧憬,然而历史的荒谬却无情地摧毁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人
生之梦。□(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