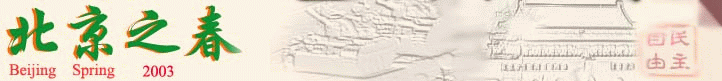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当鲁迅为被杀害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
》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名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受存
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
孩儿塔》序})。岁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当年的血迹,但当我在编纂这本《文化大革
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时,却刻刻反刍着当年那种由激情与痛楚酿成的躁动不安的心
境。这种共鸣自然发端於相似的史实;在这本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集子里,也有着我
相识或不相识的亡友的遗文,他们与当年的殷夫同样年轻、狂热、虔诚、富於献身
精神。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在鲁迅作这一序时,青年殷夫们所信仰,所引
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三
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
形态。而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字,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
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倪端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决不是
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如果广泛而言之地论及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所代表
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
的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
更令人觉得“寝食不安”地要把这些文字“流布”出来。
这本集子的雏形,成於年湮代远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时值红卫兵运动
被它的发动者赶下历史舞台,流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队落户)之际。当时
,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红卫兵决定编
辑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为赠送给所有上山下乡战友们的礼物。这本
数百页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思
潮”的文章:遇罗克的《出身论》,联动的“003通告”,“省无联”的《中国向何
处去》以及伊林·狄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编辑这样一本异端思潮文
集,出自於这批年青人这样一种共识:因“四大民主”而“解放”於文化大革命中
林林总纵的“反动思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种思想,并没有被斩尽杀绝
。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中,必然又会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
来,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变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於这场大革命
中的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学习与研究这些异端思潮。三十年後重新审视当年对
“思潮斗争”的预测,仍微微惊叹於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对中国社会竟已有了
并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矛盾比
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而兴盛於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更是直接以李一哲们倡导“民主与法制”为其进军大纛县的。当年参加《思潮集》
编印工作的伙伴们除我外还先後有曾小逸、陈兼、郭秀君、张昭卿、戚显炯、闻震
威、高哲民、许子明等,其中许子明因“四人帮”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
打三反”运动中祭上了他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如同我在这本书“总论”中第三部分《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里所阐释的,一九六八年後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
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後中共中央所发动
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
·一六”(一九七一)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
”和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的。上述编印《思潮集》的伙伴们,都曾经受到过程
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编印还曾经被上海中学工宣队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疑案
来进行清查。我个人的命运可能更不幸一点: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
因组织“地下读书会”而被审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作为“
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後的一九七八年才作为“纯属反‘
四人帮’平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异端
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时时“捏着一团火”,要把这本异端思潮文集编纂出来。
幸运的是,尽管文革後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文革非官方材料
强令收缴,这本《思潮集》被我的一个朋友尽心保存下来。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学
时毅然把它藏匿於箱荚之中,带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当时就怀着一个在将来的
某一天以此为基点编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文集的“美国梦”。经历了六
年的异域学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职於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中
心,重新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怀着一种迹近於神圣的使命感,我开始了编辑这本《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文稿。
尽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数十篇异端思潮的文章已为本书提供了一个
极好的蓝本,但要顾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异端思潮,其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是不太
够的。例如,武汉“北、决、扬”这样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仅收有
一篇《北斗星学会宣言》。为此,我只能向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广泛求援,并得到
了他们热诚的帮助。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教授首先捐赠给我他全部关於“北决扬”
的个人收藏。明尼苏达州立学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莱加大张国良先生,澳洲莫纳大
学杨小凯(曦光)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社科院哲
学所徐友鱼教授等都无私地捐献出他们的个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这本较为完整的
异端思潮集的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扬曦光、王绍光两兄——一个作为当年
“新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另一个作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为本书作了
热情洋溢的序,更为这项源起於一个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丝情与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书公开出版为止,一个渊源於少年时代的“异端梦”应当告一段
落了。我却仍然无法写下一个嘎然而止,余韵幽远的尾声。我蓦然间看到了自己已
秋的霜鬓;当年亲历文革的十六七岁少年,今天已过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岁月
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一瞬间,我又联想到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
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
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中央机密”。我在突然中
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民遗忘,在歌舞升平中遗忘他
们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一丝透底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我们这一
代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抗拒这种难以抗拒的遗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