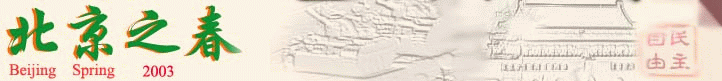从两个“替天行道”的人物说开去
农妇杜润琼的“以毒攻毒”:以投毒杀人“拯救社会”
九六年一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农妇杜润琼以投毒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当传媒透露了杜润琼连续投毒杀人的动机,是认为“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
人口太多”,所以要以毒杀老人小孩村民的方式来“拯救社会”。此一奇特的“特
大刑事犯罪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持续性的讨论。广东《文化时报
》刊出了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详细记录了这位普通农妇条理清晰、“正
气凛然”的临终自白。现摘录如下:
记者:你为什么对社会现状不满?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太多造成。社
会治安不好,偷抢杀,民工没活干。毛泽东时代到哪个城市铺头都是食店,现在到
处都是“鸡店”(即妓院)。毛泽东时代城市很少偷抢杀,现在经常看到。把毛泽
东时代与社会现状对比,觉得现在时代不正确。……社会不正当的我们需要搞一搞
,对吧。
记者: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途径去关心社会,不需要杀人啊。
杜:嗨,将别人用毒杀害是不对的,这样做不对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杀,人口
就平衡了,自己认为怎么公道就怎么为自己做。
记者:你是否认为现在社会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别人差?
杜:为国家着想。样样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么行?……我自己属于穷的生活,我
为大家着想。……我看大局顾大局。
记者:你认为文革时期农民比现在富裕吗?
杜:富是不富裕,但能长久平衡。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孩子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
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
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後要变成恶,才能搞得成事
,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杜: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
记者:你自己怎么评判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的方法做,为国家,不是为自己。
这真是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的一份绝佳的材料。
别以为这只是一位走火入魔的农妇的疯人疯语而已。这里面实在隐藏着一个
病态的社会里太多被视为“常态”、甚至“天经地义”的现象。试看:
一、在以崇高的目的和理由,理直气壮地做灭绝人性的事情方面,共产党、
毛泽东多年来的教育,已经成为底层社会一般民众的基本文化心理积淀,于是就构
成了现实行为中许多匪夷所思的表现。你看,“做善後要变成恶,才能搞得成事,
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这种“无毒不丈夫”式的人生哲学,甚至连语言方式
都是“毛体”的,如果把“杜润琼”的名字换成“毛泽东”,我们那些大御笔“张
春桥”、“姚文元”们,不是一定要解读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智慧”的么?“
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文革中以最最最革命的理由虐杀无
辜、草菅人命,令得万千生灵涂炭,正是出自这样的“革命逻辑”。杜润琼在法庭
上说:“杀得尸骨成堆,继续前进”,这类狂言放在共产党话语的语境之中,比如
土改的“血洗清算”、文革的“刺刀见红”,六四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安宁
”等等,实在没有比它更“正常”的了。
二、文革影响与“毛时代情结”,是至今制约着大陆社会基层群众日常心态
的基本要素。邓小平式的改革是缺乏意识形态支持的(“邓小平思想”云云完全是
胡扯淡),毛泽东却有着一套既适合平头百姓、又深入浅出、且自足性很强的意识
形态框架,构成了大陆底层一般民众日常判断是非、评价事物的基本价值结构。近
十年的经济改革给民众带来的利益越多,它在意识形态价值结构上与现实的脱节就
越严重。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任何的难题,比如杜润琼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能就业
,广东“民工潮”给地方治安带来的困扰等等,都会使得一般民众拿起现成的判断
标尺:毛思想、毛时代、毛武器等等,对现实加以抨击。毛时代特有的道德优越感
又使得任何“替天行道”的反现实冲动都具备了超然的合法性——请注意杜润琼是
多么沾沾自喜于村人称呼她为“律师”——一旦有合适的世态诱发,杜润琼、张润
琼、李琼润之类的“以毒攻毒”手段,自以为“为国家做事”的“草莽英雄”,就
会以各种面目涌现。可以说,不批毛,没有全社会的非毛化过程;在日渐深入的商
业化、市场化过程中,不彻底扔掉“四个坚持”之类的意识形态陈旧框架,杜(李
、张、王)润琼式的民间“律师”与“民工潮”、“盲流潮”的社会盲动力量一汇
合,其破坏性前景是相当可怕的。
三、人口压力带来社会心态的畸形化发展,杜润琼的范例是让所有人口学家
闻之色变的。杜润琼明确道出:她投毒杀人是为了“减少人口”、“为国办事”。
人口压力成了这位农妇采取疯狂的社会报复措施的直接借口,这是人口问题上潜伏
的社会危机的最明显的表征,也是那些坐在书房里、办公室里的“计划生育”高官
、学院派专家以往任何“沙盘操演”、“数理模型”都预测不到的逼人问题。人口
问题所带来的城乡劳力过剩,经济发展又拉大了城乡、贫富的悬殊,却又同时刺激
起人们一浪高一浪的消费欲望,这几大因素的夹缠扭曲,再加上前述的社会价值、
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脱节,人口背后隐藏的社会危机已经不是仅仅靠操作性、技术性
的政策、方法就可以解决的,“杜润琼现象”表现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病态,而且明
确地宣示出制度性的病态了。
王海的“知假买假”:“打假英雄”与造假时代
从杜润琼“以毒攻毒”的范例,就很容易辨析,九五年大陆新闻人物“打假
英雄”王海的出现所透现的社会病症了。
王海是九五年出现在北京、东北、河南等南北大城市街头的另一位“替天行
道”的民间英雄。近几年来,大陆市场上假货充斥,从中外名牌的日用品到性命攸
关的医药品,伪劣产品已到了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地步,毒酒杀人、毒“药”致
命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商店为了推销商品、标榜“真货”,就贴出“绝对真货,
买到假货保证X倍赔偿”之类的布告,殊不知,连这“绝对真货”的广告也是假货
。本来一文不名的个体户王海看准这一点,以他对市场商品的熟稔,便开始了他的
“知假买假”,到处索赔的专业生涯。开始是针对“标榜真货”的商店、厂家索赔
,然后是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可能抓住的任何公司、厂家高额索赔。王海
为此发了大财,“知假买假”本身成了王海个人的一种谋取暴利的商业行为,王海
甚至挂起了“买假专家”、“打假英雄”的专业招牌,开始了他的南北征战。
王海的打假行为经媒体披露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和广泛争议。赞成者
捧之上天,批评者贬之入地。《光明日报》在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发表法律学者陈苏
《知假买假索赔有理吗?》一文,认为知假买假是一种“黑吃黑”、“以暴易暴”
、“以恶去恶”的行为,与造假卖假一样,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言论较为开放的
《中国青年报》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则登出经济学者张曙光的《从王海事件看市
场制度的形成》一文,主张“知假买假索赔有理”,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把买假索赔的权利界定给消费者,为私人进入查假打假这一公共活动领域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和巨大的利益激励。在王海一再受到舆论质疑以后,又在《东方》杂
志九六年第二期发表《合天理,顺人心》一文,再一次从法律、道德的角度对王海
的打假行为予以支持。
笔者细读了论战双方的驳难文字,一时感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贬者认为王海“知假买假”以谋取暴利是“不道德”,褒者认为市场机制的供求关
系中本身就包含了“利益性投机”,这不能以道德去规限。——孰是孰非耶?笔者
以为,把“王海现象”放在前述的“杜润琼现象”之中,或许有助于我们廓清一些
看问题的视界。在法律意义上说来,王海的“知假买假”与杜润琼的“以毒攻毒”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且造成的社
会后果至少并不是人身伤害性的,后者则相反。但是,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学
的角度去分析,其二者又有着共通之处了——无论王海现象或杜润琼现象,它们都
共同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病态的病态性报复行为”。无须说,杜润琼以“投毒杀
人”的方式“为国家办事”(减少人口),其设置的前提是虚假的(假得疯狂);
王海的“知假买假”是为了打击造假之风,一旦成为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其
前提也就同样变得虚假了(假得功利)。“打假”是为了消灭假,如若“打假”是
为了以“打假”谋利,恰正是从市场的供求意义上,“打假”者其实不是在扼制假
,反而是在欢迎“假”,甚至以“假”为生了。辨驳者说:从商业行为的角度,王
海“打假”的动机如何可以不论,其後果却是使假货受罚、遏止了造假的。问题在
于,“打假”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商业行为”,同时更关涉到社会道德、社会公
理、社会风气等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制度结构的问题。“道德万能论”自然是乌托
邦,“市场万能论”何尝又不是另一种乌托邦?任何商业社会都有造假货劣货的现
象,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免俗。其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与其说依靠市场机制的自然
调节,不如说,市场机制首先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之下的。
中国大陆今天的伪劣横行,其症结恰恰是体制性、制度性的——执政者即是执法者
的官官相护“双轨制”的谋利缝隙,所有制、所有权的含混不明,都使得以造假谋
取暴利的短期行为,有了最直接的刺激动力和最好的体制屏障(比如受罚也可以转
嫁到企业和国家身上)。象王海一样“替天行道”式的“打假英雄”,恰恰正是不
折不扣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它或许有着权宜性的合理因素,但作为“
天理人心”去鼓之倡之,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社会改革的中国大陆,已走到了不变革根本制度则无以解
危解困的重要关口。制度问题所郁积的社会危机,已到了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并且恶
性发作的临界点。正如“以黑吃黑”、“以恶去恶”造成的必定是恶性的社会循环
一样,病态性的社会报复不可能克服制度性的病态——这,就是杜润琼、王海两案
给予我们的一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