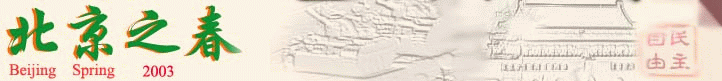关於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
——纪念反右四十周年
许良英
一、我怎样自投“阳谋”罗网的?
我在大学是学物理的,入学前对当代物理学产生狂热兴趣,立志要做一个象
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可是,抗日战争初期的社会现实使我无法安心钻研科学
,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後的白色恐怖,激起了我极大的革命义愤,从此,义
无反顾地投身於中国的人民革命斗争。我是以科学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牺牲精神,
以及对革命理想和革命领袖的虔诚的信仰投身於革命的。当时以为自己领悟了纯真
的科学精神、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诚的宗教精神的真谛,认为三者是融合一体的,
遗憾的是,它却铸成了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盲从和迷信。我於一九五七年
六月八日瞬息间变成“右派”,就是由於这种迷信;而直至一九七四年才觉醒过来
。
反右运动的前奏是“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双百”方针是对一九五
六年苏共二十大的回应,主张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强
烈地吸引了我,我在当年写的《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
从科学史上和哲学上来论证这一方针。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
学。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听到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後改名为《关於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详细传达、十多天後又听到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在後一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
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七个月後,他却把这个“推而广之”的帐算
到“右派”头上。)并且提出整风问题。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改正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求“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
帝拉下马”的无畏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了宣传“鸣放”政策,毛泽东从
三月六日到二十日这十五天内在北京和外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九次话,这些讲话
的要点,我大多及时地听到了传达(通过中宣部科学处),每次都感到振奋。四月
,正式开始了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即所谓“整风鸣放”,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毛泽东要
党的干部对党外人士“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四月三十日他
还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
,恐怕有道理。(可是一个多月後,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
在种种极端感人的坦诚的言词反复动员下,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
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报答这个千年不遇的盛世圣主,都毫
无顾忌地开怀畅言,使一九五七年五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
从五月初到六月七日,报上什么意见都有,甚至连要杀共产党的话也登上了《人民
日报》(以後了解到,这纯属断章取义的歪曲捏造)。这个时期,我每天花四小时
读报,并曾去北大看大字报,企图分析研究鸣放出来的各种意见,从中找出人民内
部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和当前的主要矛盾。当我获悉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编译
局(当时已改组为科学出版社)有人在鸣会上骂我,说以前编译局是受“许良英王
朝的统治”,我并无反感,觉得别人把心里的怨气都吐出来,总是好事。由於我长
期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盲从迷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偏离共产党的思想,因此在
鸣放期间我不仅没有放过任何所谓反党“右派言论”,相反,在听到这类言论时,
我都要予以反驳。例如在哲学所一次党员骨干座谈会上,有一个老党员提出,科学
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即表示反对,认为实质上这是否定党的领导
,而当前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观任务大,主观力量小。在场的多数党员都不同
意我的意见。
就在沉迷於鸣放的热潮时,做梦也想不到,六月八日突然变了天。一个多月
来天天以大量版面报道各地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各种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民日报》
,这一天完全变了脸,从社论到第八版,摆开了对那些批评意见进行全面反击的凶
狠架势。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危言:“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
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这个睛天霹雳对於一年多来由“双百”方针所带给我的
喜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怒不可遏,认为这会使党失信於人民,很可能是那些反
对鸣放的干部(毛泽东说过,有百分之九十的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背着
毛泽东干的,於是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
。在随後召开的两次党员骨干会议上,我都第一个发言,把不满情绪全盘倒了出来
,认为《人民日报》的突然变脸,既失信於人民,也是不道德的,连起码的民主也
没有。鸣放是我们动员他们放的,而且反复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可
以言而无信,把提意见的人当作敌人?会後,我进城找了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长
,兼哲学自然辩证法组组长),郁文(科学院党委书记)、范文澜(中共中央候补
委员,邻居)、潘梓年(哲学所所长),知道反右斗争确是毛泽东自己策划的,理
由是右派利用整风向党进攻。既然如此,我的思想也就通了。随後读到一个月前(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来毛泽东在鸣放尚未达
到高潮以前就已布置了反右运动,他说右派“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
主”,他们是“具有利牙,喜欢吃人”的鲨鱼。他估计,在各个单位的知识分子中
间,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
由於我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我成了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八月一日科学院借北
大礼堂召开第一次全院性批判大会,主要是批判我。《人民日报》於七月二十九日
和八月三日一再刊出批判我的报道。经过连续一个月的大会小会的批判,结果我被
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浙江临海农村)当了二十年农民,靠劳动工分养活自
己和老母。一九七八年回科学院工作。一九七九年初,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但留下一个尾巴,认为我当时反对党中央,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好心的朋友说,
这是一条光明的尾巴。象我这样,仅仅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划为右派的,未
曾听说有第二人。
二、是“阳谋”还是阴谋?
反右运动开始後,毛泽东得意地称自己策动鸣放和反右的计谋是“引蛇出洞
”的“阳谋”,右派是“自投罗网”。我大概是自投罗网者最愚蠢的一个,是我对
毛泽东愚忠的报答。可悲的是,在我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与地主、富农、
反革命、坏分子同为“五类分子”)以後,依然迷信毛泽东和共产党,处处以共产
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直至一九七四年在北京(为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耳闻
目睹江青、毛泽东关於“批林批孔”的种种表演,发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原来
是一个大骗局,这种迷信才彻底破灭。由此我又醒悟到所谓“大跃进”和“反右”
显然也是政治大骗局。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历史倒
退到中世纪,他的三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返祖现象”,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的背叛。可惜我醒悟得太迟
了,要在当了十七年右派後才认清了历史的真相。
要了解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反右究竟是“阳谋”,还
是阴谋?所谓“阳谋”是指:毛泽东提出整风鸣放是真心诚意的,右派却趁机向共
产党猖狂进攻,毛泽东不得不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予以反击。这是毛泽东
自己的一贯说法,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可是,在文革初期,我读到红卫兵印发的毛
泽东讲话文集中他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现那
时毛泽东就已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一个月後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
和三个月後的整风鸣放,都不过是一种歼敌的计谋(即阴谋)。请听听他的原话: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
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
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
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中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同时,他还泄露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永
远只能充当顺从的被统治者,如此“百家争鸣”,无异於双簧滑稽剧。可惜我不知
就里,把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当真,以为中国将再现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古代希腊和
欧洲文艺复兴以後的学术繁荣局面。可是,在毛泽东的愚弄下,它所带来的却是对
学术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和知识分子的无尽劫难。
真实反映“毛泽东思想”的这篇重要讲话,收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泽东
选集》第五卷中,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重视。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
由邓小平定调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在论述鸣放、反右历
史时,都重复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後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
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八十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一九九四年出
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
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
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但瑕不掩瑜,
这本回忆录仍不失为了解毛泽东人品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反右运动仅仅错在“扩大化”吗?
反右运动历史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反右运动?它是象文化大革命和
大跃进一样是反历史、反人性的倒行逆施,还是象李维汉和邓小平所说,反右斗争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两个月後又出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长。一九七八年,他在中央党校,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创了影响深
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奋力推动平反历史上由共产党所造成
的一切冤假错案工作。这两项工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由於胡耀邦的努力,一
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终於作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我是有幸最早读到
这个文件的右派。当时中央组织部还通过我邀请科学院系统几位遭遇很惨的右派到
中组部座谈,诉苦。改正工作阻力很大,各单位在一九七九年才开始。据我所知,
科学院系统(包括以後分出去的社会科学院)的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值得注意的是
,毛泽东似乎很“关心”我们,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科学
院哲学所被敌人统治着”这样骇人听闻的话),反右重灾区浙江省以及江苏省也全
部改正了。一九七九年民盟中央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指出毛泽东当年所说的
“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所谓他们的右派言论“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
“平反委员会”,要不是无中生有,就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曾经轰动一时的所
谓章伯钧於六月六日紧急召集六教授会议,也是莫须有的诬陷。以李维汉为首的中
共中央统战部於一九八零年五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虽然承认“章罗联盟”在组
织上并不存在,但却认为在政治上是存在的,因此,章伯均、罗隆基,以及彭文应
、储安平、陈仁炳不能改正,由於留下了几个靶子,就大言不惭地认定,反右“是
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李维汉所以采取这一态度,显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邓小
平的威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执行反右斗争的主要负
责人。
经过两年的复查,全国有五十五万右派得到改正,未改正的仅三千人。这三
千人中,少数是原单位党组织坚持不予改正,多数是由於下落不明或其他原因。尽
管如此,正式改正的右派已占“正式右派”的总数的99.44%,不被改正的仅占
0.56%,何况不予改正的理由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承认99.44%是搞
错了,却还要在一九八一年的《关於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硬着头皮
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是“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这里所以在“右派”前面加“正式”二字,是因为反右运动时在小学教师和
农村区乡干部中也产生了大批右派,估计人数可能达五十万,我回老家後曾与他们
同受监督劳动。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於是
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以後给右派摘帽和改正,他们都没有份。
四、一九八七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怎样流产的?
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
,夸耀自己坑的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并说对资产阶级是少一些良心好。於是,背
信弃义成了美德,说假话受奖,说真话受罪。反右运动一结束,他就发动了以全民
打麻雀运动开始的“大跃进”、信誓旦旦地要在几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全国
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对这次失败报复,他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制造了
历时十年的文化浩劫和造神运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拔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和
大跃进虽然被否定了,但对反右运动却含情脉脉,一九八一年九月邓小平就曾作过
目前形势比一九五七年还严重的危言,以此作为反自由化的根据。於是反右运动历
史真相问题成了禁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为了解下我们头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一九八六年我和方励之、刘宾雁共
同发起召开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们两人我是一九七七年先後认识
的,由於有类似坎坷的经历,都一见如故。尤其是方励之,虽然比我小十六岁,但
由於都是学物理的,并且都十分崇敬爱因斯坦,自然成为莫逆之交(一九八九年官
方报刊上称我们为“密友”,倒一点不假)。开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的主意是方励
之首先想到的,他觉得中国改革进程太慢,通过这样的会可以促进一下。十一月十
四日,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发起这个会的问题。会期定於一九八
七年二月三至五日。方励之想得很天真,说要扩大影响,先在《人民日报》上发个
消息。刘宾雁和我都认为不大可能。我们三人一致希望会议限於学术性讨论,人数
不宜过多,当场我们提出了大约三十人的名单。会上我还出二十五个可供大家讨论
的参考题目。方励之自告奋勇,说邀请信由他带回合肥起草,联系地点就设在我家
里。当天下午方励之就去了上海,在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处作了关於民主、改革
的讲话。对究竟是谁养活谁,民主是否恩赐,知识分子的使命等问题作了透彻的阐
述。一个星期後他寄来反右历史讨论会邀请信稿,信稿写得很得体,我即找人打印
寄发了。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由个人发起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反应十分热
烈。
我们发出大约四十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
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山、电影评论家钟
惦裴、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
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
有不少我们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
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
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
了一个。
十二月二十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参与这个会的
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十二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
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於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
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历史讨论会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
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
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
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
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大会(把我误认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
为纪念大会),於是邓说,要把这三个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
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方励
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三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
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
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於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
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二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後,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央不准我们开这个会的指示精神,说
如果一定要开,“矛盾的性质会转化的”(即将转化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
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
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之後,还准备再开除十人,我是首当其冲。大概由於赵紫
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後,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後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
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後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
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
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三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
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处分又最重,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
。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
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一
九九零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
五、对几本反右运动史的评论
反右运动涉及中国三代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空前的灾难,在世界历史
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段历史曲折、复杂、内涵十分丰富,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将近十年内,先後见到六本反右运动史。其中一本是很多年前一个外国人写的(
有中译本),内容很单薄,材料完全出自当时的报刊,缺乏深入的分析。另一本是
近年国内出的《中国百名大右派》,仅仅汇集当年报上所谓揭露批判的材料,不加
分析、核实,真伪、是非莫辩,没有历史全貌,严格说来,算不上反右运动史。其
余四本,较有影响,值得一评。
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後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费正清
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八十年代已出了二个中译本。
由於作者被认为是英美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他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又曾作为哈
佛大学的基础课,我不得不认真去读这本书。可是,读後,不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
愚弄的感觉。请听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
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性使得党的
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
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
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以实现党员品行上面
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泽东与刘少奇於一九五七年的
“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
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
话并非我说的,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只是向哲学所党支部
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
社”也当作新闻报道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
的主要根据。这本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
,是值得怀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
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
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决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
,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
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
第二本是一九九一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阳谋——“反右”前後》
,一九九三年又出了修订本,篇幅增加一倍。作者丁杼,文革初毕业於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八十年代初留学美国,现在美国中部一所大学教物理。他心系祖国,关
心故土亲人的命运,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三本书:《阳谋》,《人祸》,《浩劫》,
记录了四十年来我们民族三大灾难:“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
两本已经出版。作者是一个有心人,文革时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日後把这段历史
记述下来。《阳谋》是一本成功之作,对反右运动的实质和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
,抓住了反右运动主要由於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这一核心问题,把历史线索上溯到
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用感人的笔触诉述了无数优秀知识分子所遭
受的劫难。这是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
第三本是一九九五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右派始末》。作者叶永烈,
六十年代毕业於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写过很多科幻小说,後改行写纪实文学,出过
不少畅销书,关於反右题材就出过好几本。这本书的扉页赫然印着:“中国第一部
最具权威的反‘右’史”。作者采访过一些右派明星,对他们的经历作了比较详细
的介绍,这些内容有一定史料价值。但从总体看,它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根
本谈不上什么“权威”性。首先,它只是在官方关於反右历史结论的框框内打转,
对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例如,虽然书中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毛泽东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但看不到它与随後公开发表并被说得天花乱坠
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整风鸣放之间的因果关系。书的结尾毫无批判地引
述了官方的结论,认为反右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
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写历史,竟然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却要自诩为“最具权威
”,未免可笑。在《後记》中,作者表示对右派的同情,称一九五七年千千万万受
污辱的右派为“被扭曲的心灵”。认为受污辱者的心灵必然都扭曲了,这是一种什
么心态?至於史实的可靠性,作者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作者自称是一九五七年反右
时考进北大的,说北大有五百多右派。可是,据我所知,北大教职员中的右派就有
七百多,学生右派六百多。书中开列的“著名右派名录”中,把北大教授冯友兰,
以及许德珩(误为衍)、张奚若、陶孟和也都给戴上右派帽子,可见本书“记实”
的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
第四本是一九九六年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逆转 ——“反右”运
动史》,作者华民(笔名)。从刘宾雁所写的序看来,作者是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政
治运动冲击的中共老干部,出於良知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根据自己所能接触到的
文献资料,写出这本很有特色的反右运动史。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很严谨的,所叙述
的史实都有根据,尤其是附录中的十九个文件,是十分难得而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原
始资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反右”前後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
为反右运动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美中不足的是,视野是扩大了,但
重心却被忽略了。凡是亲身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都知道,反右运动实质上是整知识
分子运动,毛泽东所有反右的言论,矛头主要都是对着知识分子的。所有“右派言
论”中,最刺痛毛泽东的莫过於罗隆基所说的,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小资产阶级
的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李维汉也承认,罗隆基这句话对毛
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是起关键作用的。可惜在华民这本书中知识分子问题这条主线被
湮没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在分析上显然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此外,本书所引为
根据的内部资料,仅限於一般中层干部(即所谓县团级)所能读到的文件,而毛泽
东反右前後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内部讲话在书中很少反映,因此,难以使读者对反右
运动史形成一个完整、深刻而生动的形象。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一部难能可贵的
历史著作,它所提供的史料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如果把它和丁杼的《阳谋》对照起
来读,一定会更受益。总之,华民和丁杼两人对反右运动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应该感谢他们。□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