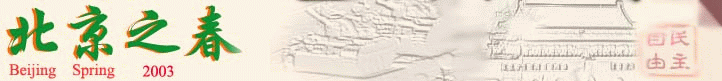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续)
吴仁华
继工自联总部之後,坚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学生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
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
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於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
食团广播站,撤至位於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
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後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
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
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
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
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
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
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二时三十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後
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後!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
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么,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要
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
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刘晓波等四名绝食知识分子也先後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後
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
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间,一名纠察队员匆匆跑来告诉我,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
枪支,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我闻讯急忙带着几名纠察队员赶过去。侯德健、刘
晓波也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枪上覆盖着棉
被,枪口朝西。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
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在我们犹豫之时,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约二
十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也许是由於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那帮工人弟兄并未动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
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
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
落泪。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刘晓波等人留在原地继续说服他
的工人弟兄。
经过再三劝说,我们终於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谅解,拿到了这挺从装甲车上卸
下来的机枪。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
步枪没有子弹。
我们回到纪念碑底座北侧,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
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
毁枪行动,再次重申了我们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仍然坚持和
平请愿的宗旨,我们愿意以流血为代价,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
凌晨三时许,在绝食棚内,四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
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
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应当想尽一
切办法避免更多的流血,争取和平撤离广场。但是,他们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
撤退方案。这时候,北京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们的陪
同下乘救护车出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以争取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许诺与时间。
随後,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进学生指挥部,准备与学生领袖们商议撤
离广场事宜。因为请愿静坐的主体是学生,广场的控制权在学生手里,没有学生领
袖的参与,谈判就没有代表性。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
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於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
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
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後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
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後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
。
时间已是凌晨三时许,再也没有什么商议回旋的余地。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
,武力攻占广场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刘晓波等人只好放弃争取学生领袖共同参与谈
判撤离广场的努力,决定先由他们自己出面去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在取得一定的
承诺後,再回头继续争取学生领袖的认可,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广场。
凌晨三时三十分许,侯德健和周舵作为绝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两位红十字
会医生的陪同下,从纪念碑底座西侧出口下去,寻找戒严部队谈判和平撤离事宜。
选择侯德健当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张脸在大陆就是最有效的
通行证,也许可以在军人面前增加安全系数。选择周舵当代表,则是因为他那副文
质彬彬的书生相,加上他说话慢条斯理有逻辑性,不象刘晓波容易情绪冲动,说话
又结巴。
侯德健一行与戒严部队接触的经过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借助
侯德健本人事後的一段自述:“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
已摆好了冲锋阵形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
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
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立即
停住了脚步,医生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
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无恶意。
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後,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来,他看
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
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
、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
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然停止了,之後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
,他表示需要请求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
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清晨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
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的
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
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後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
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
,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
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
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
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它含
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见《时代周刊》第二三六期
)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
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人们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後的时刻终於到了。
於是,悲壮的《国际歌》再次响起。放声高歌的人们安然端坐着,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没有一丝骚动,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後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而自
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
值了。”
黑暗中,最後几名中外记者撤离了纪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学生随着市民零零
散散地离开纪念碑一带,从前门方向撤离广场。最後坚持留在纪念碑一带的除了为
数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人数约有五、六千人,绝大部分
集中在纪念碑北侧。
此时,在纪念碑西侧大约二、三十来米,有人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点起了几
堆篝火,火苗在风的吹动下闪烁。在广场的东北角,也有一团火焰在闪动,似乎是
先前被民众放火燃烧的装甲车的余火。
在熄灯後不久,早已列阵於金水桥前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向广场推进。借助
隐约的火光,只见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首当其冲,在强烈的撞击下轰
然倾倒,然後是一座座的帐篷被辗倒,连同帐篷内为数不详的学生,这些疲惫已极
的学生尚在梦乡之中。
我的心也被辗碎了。
许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还有学生在帐篷里睡觉,完全是因为
没有亲身经历广场那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的缘故。我的两位学生虽然被我从帐篷中
强行拉到纪念碑一带,但直到撤离广场为止,仍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对後来撤出
广场的经过毫无记忆。这两位学生自五月十三日绝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广场,疲惫
得不能再疲惫。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摄制的题为“北京风波真相”的纪录影片中,
就曾提到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之後,有一名叫吴斌的学生在帐篷里被军人唤醒。
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经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纪念碑底座前最西侧的一
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坦克这个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
嫩芽,轻易地就被折断了。
由於是黑暗,帐篷的遮挡和心理的紧张,几乎是在看见铁旗杆倒下的同时,
我才发现这个赫然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庞然大物。这辆坦克在黑暗中出现得太突然了
,坐在铁旗杆附近的学生根本来不及移动。
约在熄灯後十分钟左右,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来到学生指挥部的帐篷内
,匆匆向学生领袖们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并继续劝导学生领袖们带队撤离
广场。
四时三十分,广场上的灯重新点亮。从人民大会堂处的官方广播中传出戒严
部队的通告。通告称:“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这个通告的播放,纯属当局欺世盗名,以掩盖血腥清场的真相。如前所述,
血腥清场其实在凌晨一时三十分军队抵达广场之初即已开始,射杀驱逐广场边沿地
区的学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工人自治会所在的广场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
的广场北部中端),难道就不是清场?坦克快速推进到纪念碑前,辗倒“民主女神
”塑像、铁旗杆、帐篷以及帐篷内睡觉的学生,难道也不算是清场?
在播放这个通告的同时,还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於迅速恢
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灯亮之际,数以万计的军人,已经从广场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地涌向
纪念碑底座。由於身後阻隔着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但事後据纪念碑南侧
的学生反映,在纪念碑南侧同时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向纪念碑底座逼近,并伴有大
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侯德健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向在场学生介绍与戒严部队
接触谈判的情景,并发出和平撤退的呼吁。直到此时,广大学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
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这件事。侯德健讲话的大意是:在没有经过同学们同意之前,
我擅自作主,去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希望大家谅解。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不能
再流血了,呼吁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
侯德健的讲话激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周发出一阵阵怒骂声,几乎是
侯德健每讲一句话就被骂一句。许多学生怒不可遏,斥责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
软骨头。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侯德健,你快滚蛋吧!别影响我们了!”一些学
生甚至冲进广播站,或是抢夺话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
周舵和刘晓波随後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内容大致与侯德健相同,主要是呼吁
学生和平撤离广场。
此时,在纪念碑东侧也开始有大批装甲车逼近,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
声。历史博物馆一带的军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齐声呼喊:“快点撤!快点撤!”
军队和学生双方都处於极度的愤怒与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双方一旦
稍有冲突,就会导致大量人的死亡。我和几位高校青年教师纷纷不约而同地出面安
抚学生的情绪,呼吁大家保持镇定和秩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在军队到达之後,
谁也不许有过激言行,尽量避免流血冲突。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坡在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
要与学生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民主运动的成果,决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他鼓励说
:同学们,我们的身後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在这里流血牺牲,这是我们
的光荣和骄傲。四周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密集的枪声,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豪气。此
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分。过去同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对他有所误解,认定他属於只动
口不动手的虚弱书生,以至於不屑与他来往。陈坡在六四事件後身陷牢狱。
我逐一叮嘱守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的特别纠察队员们,在最後时刻
,一定要尽忠职守,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望着眼前这些熟悉而
可爱的学生,想到自己再也无法尽到保护的职责,心情极为痛苦。唯一可以自慰的
是,在生死考验之际,我与自己的学生们在一起,我没有恐惧和退缩。
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
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
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实
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後是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少量的防暴警察,也都是全副武装
。最後才是督阵的坦克和装甲车。
学生们面对逼近的军队,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不约而同地对着军队做出V
字形手势,使劲地挥动着。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
,约二十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後是一排排
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後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後面是人数
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
察。
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响下,面对严峻的局势,学生领袖们坚守不撤的决心似乎
有所动摇,他们难以承担数以千计学生安危的重责,最终决定在场学生立刻用口头
表决方式决定是坚守还是撤离。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在广播中解释说,在目前危急
情景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口头表决方式
,具体做法是,我在广播中喊叫一、二、三後,主张撤离的同学就喊“撤离”两字
,主张坚守的同学就喊“坚守”两字,少数服从多数,以声音的强弱来决定。口头
表决的结果是坚守的声音远远越过撤离的呼声,在纪念碑北侧几乎就听不到撤离的
声音,学生们还对眼前的军人做着V字形手势,情绪高涨。然而,学生领袖们还是
倾向於撤离。
正当学生领袖们准备具体布置实施撤退行动之时,军人鸣枪冲上纪念碑底座
,因而使侯德健等人力图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
凌晨四时四十分许,在纪念碑北侧,一支人数约四十人左右的军队突击队冲
入学生队伍。他们身穿迷彩服,端着冲锋枪,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
的边沿,冲上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这批士兵异常凶狠,目透凶光,一边不断地对
空鸣枪警告,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开出一条通往纪念碑底座
最高层的通道。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
机等。当场就有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包括女学生,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
速跨过数千名学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纪念碑东侧,也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
层。
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
叭一阵猛射,喇叭当即被打烂了。呼吁撤退的声音消失了。随後,军人又迅速扯下
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拆除绝食棚。从我身後的纪念碑东南角广场指挥部所在地传
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心为之一紧,默默地想:指挥部完了!更担心的是学生领袖
和坚守在那里的纠察队员们的安全。
一些学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对着士兵们呼喊:不要对纪念碑开枪
,那是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纪念碑呀!而招来的则是更为密集的枪声。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
上来後,已经从最後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
後,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後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始终
回响着一个声音:死吧,死吧,给我一梭子子弹,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刹
那间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亲,想到苦苦爱恋多年的姑娘。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
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
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後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
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於回头望一眼军人。
指挥这支突击队的是一位上尉军官,年纪约三十岁,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
着对讲机。较之士兵,这位军官的态度还算温和,始终没见他动用武力。他站在我
们的身後,不停焦急地催促:“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语气中似乎带有恳求,或许他
怀有恻隐之心,不希望见到更多的学生流血。
相比之下,我们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位於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所
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十人的突击队,而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那些军人和防
暴警察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
早已对学生充满了仇恨,认为学生们是祸根。此时,这些军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
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进行猛烈的袭击。场面的暴烈
,令人终生难忘。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宣
布戒严後坚持不走,表明他们是八九民运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
於北京学生。在军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
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
。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只是时间有先有後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
。
军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
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於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於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
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
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此时,我已与几位纠察队员一起被军人打下了最高一级台阶,但依然坐在稍
低几级的台阶。坐在我身旁的是与我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
,同时,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
人有过任何过分的言行。
凌晨五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北侧
的学生队伍中。他们边走边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快走,想尽量
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东北侧
的学生随同他们从纪念碑东北角往外撤。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
从东南侧撤离广场。当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时,柴玲等人即撤离位於学
运之声广播站内的指挥部,隐身於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中。
天已经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
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於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成一
片,全是“哒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混乱中也看不清是
否对准人群扫射。
於是,纪念碑底座第二层和第三层台阶上的部分学生终於站立起来,开始慌
乱地从纪念碑东南角撤离。时间大约在凌晨五时十分至二十分之间。
我和纠察队员也站立起来,随着队伍向东南角移动。在我们的身旁,突击队
的军人仍然不时地开枪,但我未看见他们朝人群开枪。
直到我们转过纪念碑东南角,挤在狭窄的所谓撤离通道口时,纪念碑底座第
一层各级台阶以及台阶下的学生们仍未能够向外移动,因为前方的学生队伍尚未离
去,正拥挤在东南角,队伍移动得极其缓慢。
纪念碑上下,枪声还在密集地响着。
在纪念碑东南角的所谓撤离通道口,学生队伍仍然受到猛烈袭击,不时有学
生倒下。在我身边不远处,一位学生头部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
捂不住。
纪念碑东南角方向是戒严部队曾经对侯德健等人允诺过的撤离通道,当局事
後也反复如此强调。其实,东南角并不存在安全的通道。在这个位置,不仅有大量
的装甲车、坦克以及军人的严密封锁和挤迫,而且还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栏杆和被装
甲车坦克辗倒後的帐篷杂物等障碍。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
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
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
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撤得稍早,人数也较少,情况可能会好些,但也谈不
上是有组织的主动撤离。
与我同时从东南角撤离的学生,只是遭受到棍棒和枪托的袭击。而一些慌不
择路,匆忙中脱队跑向历史博物馆方向的学生,则有人受到枪击。
学生队伍直到撤出纪念碑底座的范围,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东南侧一带,
才显得不那么拥挤。大家缓过一口气後,自然而然地走成了整齐的队伍。
我看到,在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站立着约四、五百名学
生,一声不吭,打着几面旗帜,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旗帜。这群学生
默默地看着我们撤离,对我们的做出的V字手势也毫无回应。後来我听说,他们是
一群誓死不撤离广场的学生,对我们撤离广场很不满。
当走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忍不住留恋地回顾天安门广场,学生队
伍在密集的枪声中源源不断地撤出,并不时有学生退出队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旗帜下的人群之中。尽管心中悲愤异常,但我强忍住泪水,不想在军人面前示
弱。学生们大多与我一样,紧咬牙关,两眼喷射着怒火。
在“毛主席纪念堂”与前门箭楼之间的开阔地,数以千计的军人在待命,配
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
约有数千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泪水挂满双颊。见到学生悲愤的神态,他们
强忍悲伤,安慰学生说“你们没有失败,你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广场上来的!历
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面对这样的北京民众,我再也止不了泪水。
一位六十岁的老大爷一边悲伤地哭诉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
……”一边对学生队伍哭喊着:“孩子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不能忘记呀,孩子
们!……”
一些学生对着路边的群众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
没有尽到责任……”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後的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
密集的枪声,期间夹杂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
从队伍後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
在撤退的路上,不断见到血腥镇压所遗留的痕迹,鲜血斑斑,枪孔密麻。沿
途不时遇上大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军队,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空降兵部队。
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当局出动了除海军之外的各兵种部队。
清晨七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进到西长安街。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约二
十余名师生处在邮电大楼附近。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约宽七、八十米,属双
行道,南北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
着一道高约一米二的绿色尖头栏栅。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南边的自
行车道上。就在这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一边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一
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辗过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像是催泪
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使人咳嗽不止。政法大学的
一位青年女教师当场被薰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尽管在广场上经历了血腥镇压,但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军队会残忍到用坦克
继续追辗已经撤离广场,并正处在返校途中的和平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
纷翻越绿色尖头栏栅而躲避,不少人被关头栏栅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
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栏栅,只好紧贴在栏栅旁,惊恐
万状。
待坦克过去,比我们所处位置稍後的学生已惨遭不幸,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
,另有两名学生被辗断双腿。(事後得知,其中一名被辗断双腿的是北京体育学院
的学生方政。)发生惨案的现场位置在六部口。
一位市民见义勇为,将其中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运到中国政法大学,摆放在
教学大楼前。这五名死难学生,一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一位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
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带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
两位死难学生的校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学生。
坦克追辗学生的惨案激怒了大家,许多人拣起路旁的石块,奋力抛向已经远
去的坦克。
学生队伍经过重整後,继续沿长安街前行,在西单路口北拐转向西单大街,
然後转向新街口。在新街口,学生队伍分为两路大军,一路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
政法大学为主,往北去,一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为主,往东去。
自进入西单大街始,两旁的民众越来越多,情绪很激烈,纷纷痛斥军队的暴
行,并热情地赞颂和鼓励学生。
在新街口,发生了一段令我难忘的小插曲,一位纠察队员遇上了通宵达旦寻
找等待他的女朋友,泪流满面的姑娘小鸟似地飞扑上来,俩人当众紧紧相拥亲吻,
以中国人罕见的方式庆贺劫後重逢。在为他俩庆幸的同时,我不禁想起那些长眠的
学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前景无限美好,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科学家、工
程师、作家,可以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以至好爷爷、好奶奶,然
而,为了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想到此,《血染的风
采》一歌的旋律在脑海中回旋,我带头唱起这首悲壮的歌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
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
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
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
泪眼朦胧中,那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尚在滴血。一名死难学生的头颅被坦克
压扁,绑在额头上的红布条深深地嵌入右侧面颊。
师生们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
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北京城枪声密集,血腥屠杀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