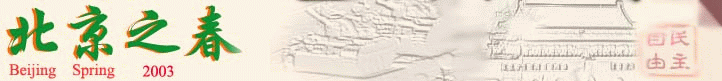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六·四”血案之後,中共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机空前加重
;邓小平南巡之後,压抑的中国大地又被新一轮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所冲破,人们在
对政治改革的前景绝望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商海,然而,迅速漫延的腐败吞食了人
们心中仅存的良知、正义感,贫富差距之悬殊又从切身利益被剥夺的体验中,加深
了平民对现政权的不满,价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赤裸裸的
短视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庸人;加之申办奥运的失败对公众的民族自尊的伤害和对执
政党虚荣心的打击,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
。在此种背景下,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
义的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後官
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倪端。
中共官方一方面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需要,希望以爱国主义化解合法性危机
。执政者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动员一切媒体高倡民族自尊,回顾近
百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所经受的耻辱,不遗余力地举办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宗旨的各类晚会、报告会、读书会、音乐会、艺术节、画展、祭孔仪式,电视中
每天播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版社大搞爱国主义丛书工程,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
各地的中、小学,每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
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已经把热爱祖国提升到“
五热爱”之首,而正统的爱社会主义则沦落到“五热爱”之末。另一方面,执政者
以民族主义周旋於国际舞台,官方利用复关受挫、申办奥运失败,美国的最惠国待
遇讨论,知识产权谈判,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人权状
况和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李登辉访美所导致的两岸危机……在民众中煽动反西
方和仇美情绪。面对西方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中共执政者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底牌,以国情、传统的差异和主权不
受外来干涉为理论依据,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替践踏人权的行为辩
解。一九九六年三月以来,中共更抓住两岸关系的危机和香港回归一周年倒计时的
机会,对内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然而,奉行功利主
义原则的中共高层,绝不会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国际正义的追求。它也会用金钱收买
第三世界国家,也会利用在联合国的地位拉拢第三世界诸国,甚至投弃权票默许萨
达姆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中国的宿敌日本,其态度分外暧昧,从教科书事件到日
本政坛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至最近的钓鱼台岛事件,中共对日本光说不练的软弱,对
国内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的压制,都证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扬民族主义的赤裸裸的
功利准则。对西方国家亦如此。中共控制的传媒抓住一切机会丑化美国社会,而在
暗中,中共高层人士都希望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
在民间,申办奥运的失败,复关申请的屡屡受挫,知识产权谈判的曲折艰难,两
岸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指责和美国的武力威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自作主张
,特别是中共传媒对这一切的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把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挫折全部
归罪於西方霸权的干涉内政),都加深了中国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
,於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各类嫔妃,太监纷纷在影视屏幕上尽
显风流;易学、卦书、气功奥秘、兵 法经营学、历史人物传记、国学丛书、诸子精
华众书,中华文化精粹丛书遍布大小书摊;锦绣中华园,中华民俗村、炎皇纪念馆
、古代蜡像馆、西游记宫、三国演义、水浒村寨、大观园等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游
乐场所遍地开花;由北京示范,迅速遍及全国的飞檐式建筑,把中国的城市装点得
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传统飞檐盖顶而变成了丑陋的建筑大
杂烩。漂泊海外的游子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民族主义大合唱,以“洋插队”为题材的
小说、记实文学、随感录、影视作品更是独领一时风骚,遍布北美、欧洲、澳洲、
东洋、苏东的炎黄子孙纷纷把自己的洋插队经历变成畅销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
约》的火爆创近几年电视剧收视率之最。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现了飘泊异乡的艰辛
、积怨、乡愁和自立自强的民族自尊,用浅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对比来讽剌西方
文明,宏扬中华传统。在通俗音乐中,红极一时的是《中华民谣》,《大中华》以
及来自民族传统的爱情歌曲,甚至连电视台所插放的公益广告也以突出五星红旗、
国徽、天安门为主题。然而,一个缺乏价值支撑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民族主义的
统一根基,功利主义的动机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表面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几乎无
人肯放弃去西方、特别是去美国的机会,非法移居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仍然有增无减
,青年人在消费上仍然以追逐名牌为时尚,商品广告,店铺招牌仍然想方设法沾上
点洋味,就连曾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
方汉学家的名字来推销自己;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促销手段
,最近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即是成功的一例。换言之,中国人追逐功利
的堕落已经到了除了比谁无耻之外,再无什么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说,“六·四”
刚过的几年间,大众文化的大腕们在比谁平庸,“咱也是个俗人”成为一时的招牌
,那么到了一九九五年以後,无耻代替了平庸,专制主义加金钱诱惑已经彻底瓦解
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仅存的善良。这种无灵魂的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用利禄来收购,扔
给这类民族主义者一叠美元,他们就会象面对高官时一样,媚态可掬,频频应诺,
出卖灵魂到肉体的一切,直到再无可出卖的为止。
在这种民族主义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精英们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其
强烈程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之最。他们既不象官方提倡爱国主义那样,出於赤裸裸
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象大众文化的民俗热那样出於浅薄的金钱功利目的,而是经
过了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和道义修饰,後现代主义和後殖民主义的学术视野,拒绝
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的本土化姿态,批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的正义立场,
似乎都在显示着中国当代学人的渊博、新潮、良知和尊严。北京大学的一批中年教
授高倡振兴国学,回到乾隆时代,以抗拒追随西方新潮的轻浮学风;张颐武、王一
川、王岳川等青年学人,从後现代、後殖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卫本土文
化的学术立场,认为中国学人应该重新标举“中华性”,以振兴衰落的民族精神,
重建中国人的灵魂支撑;邓正来、甘阳、李陀等人强调人文学的本土化乃中国当代
学术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坚信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非中国
的经济学家莫属,就象当年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
样;被舆论界称为经济学“四少”之一的盛洪,坚信只有中华文化能把人类从核威
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象当年的李泽厚用“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为世界指
明路径一样;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展开的学
术讨论,几乎涉及到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坚人物,《读书》、《
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重头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关於民
族主义的文章,并且不定期地发表成组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前一二年关於《人
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一九九六年初,影响日隆且
被中宣部内部点名批评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组织了围绕着盛洪提出的“什
么是文明”为主题的讨论会,文明的抉择这一近百年来绐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重
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还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的名角,出国归来後大骂西方,似
乎西方人出钱请他们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骂。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现代派起
步而走红文坛的先锋作家、新潮艺术家,大都回归黄土地和悠远的传统来寻找灵感
和包装。最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狮”、“夏纳”等国际电影节
大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专以黄土地为素材拍电影的张艺谋、陈凯歌,
在坚信民族主义的学人中,成了专向洋人献媚的“後殖民化电影”的典型,批判他
们专以展示中华民族的愚昧和丑陋来博得洋人的欢心的洋奴心态。而这一切民族主
义的学术化讨论,其锋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以及西方的文化殖民
的霸权,直指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化热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确定文明
基本构架的抉择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然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人文学本土化的学术定位,还是立足於中国传
统的现代化的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把西方文明作为崇尚物质和武力的恶的文明加以
痛斥,还是以崇尚精神和和平的善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幻想,无论是抗拒西方
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还是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努力,无论是後现代主义
的解构方法,还是绝对相对主义的价值立论,无论是经济学的新颖角度,还是生造
术语,从西方移植问题和概念的哗众取宠,这一切表现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都不重
要,而重要的则是骨子里的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和对现存的专制秩
序的认同。如果说,《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一种浅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歇斯底
里式的发泄,那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则是经过学术修饰和道义伪装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失败和落伍完全归罪於西方列
强的入侵和压迫,而拒绝检讨自身文化的弊端和反抗现存的专制主义秩序;把西方
人对自身传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中国人维护自身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方
便口实,本来西方人的现代相对主义是针对西方中心论所作的自我检讨,是针对西
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针对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所
作的学术突破;本来,西方的後现代主义是对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传统的统摄下的种
种现代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消解,是在解构自身的传统。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更
开阔的视野和更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文明与全球的未来,是为整个人类寻找相互
融合的共同点的带有悲怆情调的努力。而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们却把这种严肃
的自省和人类情怀理解为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复兴,完全无视自身传统的弱点和当
前专制主义的严酷,放弃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对既定秩序的抗争,一味沉缅於“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幼稚幻想之中,使发源於西方的现代相对主义和後
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变成了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只对外批判而不对内反省
,只虚构光明未来而回避当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种阿Q式的家奴的自尊。我不
相信,一个在家里每天对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一跨出家门便会有人的尊严。我更
不相信,一个每天都能目睹到一党专制残酷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学者,对身边的
非人状态熟视无睹或因恐惧而不敢公开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能够真心地关怀整个
人类的未来,能够具有诚实而正直的良知。特别是在经历过“六·四”泣血悲剧的
短短几年後,中国知识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体大逃亡,大退却,大沉默的氛围中,
能够有几个人凭良知为死难者伸冤,为维持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命权而抗争?千万别
再对大洋彼岸和遥远的文明摆出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的身後,
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就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也崩
溃了。诚实、良知对於中国知识界来说,是太高贵太奢侈的品质,我们根本不配!
如果我们还想关怀人以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的话,我们只有重新回到作为一
个人的道德底线上站稳後再说。 其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以从西方般来的术
语、方法、理化论体系来包装苍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几年
的人文类刊物,内中充斥着故作高深、云里雾里、不忍卒读的洋术语、洋理论、洋
大师,有人把此概括为“洋浜泾文风”,西方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弄透彻,就为了赶
时尚而频频引用连在西方学界都被视为阅读畏途的福柯、德里达等後现代主义大师
。近几年颇为风光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更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门徒自居,从西
方制度经济学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进而定义什么是西
方文明和什么是中华文明,再进而便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最
後虚构出以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结论。当年,我曾向新儒家们请教过这样的问题
:中国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们作为它的捍卫者和宏扬者,怎么就不
能从中提炼出一套方法和概念来捍卫和宏扬,而非要从洋人那里移植呢?一种连整
理自身的文化资源的方法、概念都找不出来的文化,其优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们
捍卫和宏扬吗?今天,我还要以此问题来请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者,用西方舶来
的主义来发现和肯定中华文化岂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吗?盛洪曾经谈自已
的读书体会,说他当学生时从亚当·斯密那里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後来他翻阅
先秦诸子,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就
已经昭然於天下。就象近百年来中国的学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
样,难怪崔之元在美国知道了“後福特主义”後回国寻根,如梦初醒般地在毛泽东
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义”的源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那么自信西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源头,那又何必留学
西方呢?何必用亚当·斯密来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义”来肯定毛泽东主义呢?
其三,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以无包万有的大而化之的定
义与比较,来混淆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因素,进而否定文明的进步、制度的优劣和
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安排。他
们可以从中餐与西餐无价值优劣之分推论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公有制
之间无优劣之分,从长袍与西服之间无好坏之分推论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间无
好坏之分,从京剧和芭蕾、水墨画与油画之间无高下之分,推论出个人本位主义与
国家本位主义之间无高下之分;他们可以从古老的审美象征和道德象征至今魅力依
旧推论出工业文明并不比刀耕火种更进步;他们从不区分德国传统和英美法传统及
政体的根本差异,笼统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罪於整体的西方文明,他们不愿
意正视历史事实: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的
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为优先目标加民主政体的英、美、法诸国;他们根
本无视二战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和专制主义
国家之间的当代历史,无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
凭臆想天开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战争的根源归罪於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
明,他们更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停止过的征伐夷族和内战,无视古代中国的帝制
在战争和和平时期对人的残酷杀戮。他们从不提及二战结束後,大多数国家都是开
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时,中国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一场绝不次於抗日战争的惨烈内战
,被日本人砍杀过的中国人,还未及掩埋尸体、揩干血迹、医治创伤,就开始了更
残酷的相互厮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怎么可以用佛家传统中的一个“仁”
字掩盖住呢?即便是这个“仁”字本身的历史,也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
同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席卷全球的以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
潮意味着什么却不置一词。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正义的公认
准则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居然以这种泯灭任何普遍价值和正义标准的绝对
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宏扬中国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灾难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国人
民来承担。他们不仅模糊了中国现代化和文明抉择上的未来方向,而且使中国人陷
於狭隘盲目的民族陷井,失去了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制止恶势力的人类所应
共同遵守的正义准则,不知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的共同价值何在。换言之,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诡辩所取消的恰恰是我们
最需要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又已恰恰是我们最应该
抛弃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民主政治的
拒斥和对现行专制主义价值及其一党专政的默认,才是此种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其四,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特征,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官方的爱国主义拒绝
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词句才能如此地一致:霸权主义,一为文化霸权,一为政治霸权
。而且两者都把这种霸权地位的取得简单化地归结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对外扩张的
尚武品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强大和军事优势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换
言之,在他们眼中,西方人仅仅依靠金钱加大棒便征服了世界并行使其霸权。他们
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以“船坚炮利”来理解西方的强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启超
、胡适等人曾经论述过的由西方人所创造的私有化、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
治。历史的轮回竞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
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拒绝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者,就连因“六·四”而
流亡海外的甘阳、苏晓康、李陀等人也加入反省西化谬误,宏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
行列。如果说,中共官方出於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义策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
明还说得过去的话,如果说,大众文化出於发财的经济功利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来推
销其商品还情有可缘的话,那么,一向以超然的学术立场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标
榜的知识精英们也拒绝西方文明、特别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太有辱於知识分子的
良知了。其中的善意者、无私者也许是出於困惑,但是我认为这类动机纯正的知识
分子极少,大多数人则是出於攀权附贵、向大众献媚的功利动机。因为,历经专制
主义蹂躏的中国知识界,大都清楚其人格、独立和尊严被全部剥夺,皆源於一党专
制的残暴和对知识、知识分子的仇恨。
“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
受人非议。“六·四”後,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
今天,仍有当年被我挑战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进主义。而对这一切,
特别是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
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
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
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於此的现代
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
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
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
。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稿 九月改定於北京翠微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