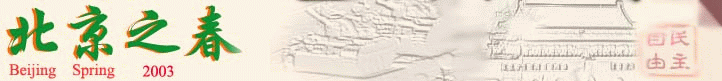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路标”改变以後……
——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苏文
【编者按】一位读者投书本刊,建议转载苏文的《“路标”改变以後……》。现将
苏文的文章和读者来信一并登出。
《北京之春》编辑部:
我热烈地向你们推荐苏文写的《“路标”改变以後……》。此文原载於国内的《
东方》杂志(现已被迫停刊)1996年第5期。作者感觉锐敏,见解犀利,视野开阔,学
问扎实。不要把它简单地看作“影射史学”,搞什么“对号入座”。重要的是鉴古
察今,从历史中吸取教益。海外有这么多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又有资讯自由、言
论自由,但能达到这篇文章水平的实在寥寥无几。贵刊是海外异议人士最重要的言
论阵地,若能刊出此文,想必对广大读者、作者都大有启发和大有刺激。
大陆访问学者 余之荫 97.5.23.
一九九一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
的话,那就是“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一九九一年剧变之後俄罗斯始终忘不了“
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一九一七年二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
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拚命呼唤“革命
”而革命就是不来,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
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十九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没有发生革命,反而
在斯托雷平改革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
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後反而发生了“彻底”的经济
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
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十九世纪末对民粹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
一九一七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粹情绪所裹胁,以至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
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於知识分子过於
“激进”?由於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於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些,
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
冲破公社世界
呼唤市场与宪政
十九世纪以前的俄国是个“公社世界”,当局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
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为国策。史实表明,俄国的传统公社(米尔)组
织并非某些理论所讲的“原始时代的遗存”,而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破坏古
代农户所有制,强化对农民的管束後形成的。俄国的农奴化进程也并非“原始公社
解体”的结果,相反倒是与“公社化”互为表里的。到十六世纪後,俄国农奴化,
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位一体的进程趋於完成。农民属於公社,公社
属於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公社社
员——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位
一体构成了俄国近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
进入十九世纪後,西学东渐,个性解放之潮冲击着传统的公社世界,以市场
经济和民主宪政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变革在俄国开始了,经过十二月党人起义,“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进步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
俄国自由主义逐渐形成。一八六一年,开始了“大改革”。这场改革以“解放农奴
”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
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为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
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
,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
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
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
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
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
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盗走了家产的一半席卷而逃,却把子弟们
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於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
改革後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後一呼声中产生了
民粹主义反对派。
“大改革”後二十年,民粹主义一度成为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主流,但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後它便明显衰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联盟”在世纪末的
大论战中压倒性地击败了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从而成为反对派运动的主流思想。之
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民粹派的政治冒险召致镇压;当局中最守旧的“公社拥
护者”与之合流形成“警察民粹派”,失去了反对派形象;俄国社会因市场经济发
展而来的自由要求,农民要求摆脱公社束缚而对民粹派不感兴趣等)外,很重要的
一点就在於,当时的自由派在呼吁冲破“大家庭”的同时,还坚持从“大家长”那
里索回被盗走的“家产”,从而主张“公正的自由”,而不是“肮脏的自由”。自
由派虽然不象社会民主派那样强调无偿“收回割地”,而是主张赎买,但不是由农
民,而是由国家按强制性的低价买下後分给农民,实际上也与“收回割地”相差无
几,因此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农民中都不乏拥护者。於是在一九零五年後的一二
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自由派大获全胜,首届杜马因而史称“立宪民主党(俄国最重要
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党)人杜马”。而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也大都偏向自由派。民
粹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面对这“令人痛心的事实”也无可奈何。
一九零五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
的双输之局
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间,俄国社会的改革要求与当局的守旧立场发生了
冲突。苏联时期称之为“第一次俄国革命”,并极力宣扬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中
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城市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然而实际上用英国学者T
·沙宁的话说,城市罢工和起义在这两年只是“一瞬间起初的革命”,实际影响很
小。真正充斥这动荡的两年的,一是杜马中以自由派为主体的反对派运动,一是乡
村中的“农民骚乱”。就连列宁当时也讲过:俄国形势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
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峙,而当时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
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都做不到的。自由派通过立宪民主党
人执牛耳的杜马实际上主导着全国的反对派运动,在这两年间为冲破公社世界,发
展市场经济,为改革专制之弊,实行自由宪政,采取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合法抵制
行动。
所谓“最革命的议会”之说,实际上是对後来苏联官方关於自由派“软弱、
反动”评价的嘲讽,然而“最反动的专制政府”之说却不符合事实。一九零五年的
俄国政府由著名的开明政治家维特任总理。他不仅对公社之弊已有认识,决心推进
经济改革,而且还是宪政的热心者。当时政府中有人认为维持专制有利於吸引外资
,发展经济。因为国外投资者并不关心俄国是什么政体,只希望稳定,而害怕动荡
。维特对此批评道:“这当然是十分幼稚之论。不错,他们希望停止无政府状态,
但是,无论外国还是俄国的贷款者,都希望俄国确立这样一种政体;它应当不至於
或很难於让某些冒险分子一旦心血来潮就能挑起像可怕的日俄战争那样的冒险活动
,也不可能出现让一个伟大民族永远受一批自私的宫廷弄臣任意摆布的状况。
显然,在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为主流,而政府方面又由开明的改革派官员
执政的条件下,只要双方能达成妥协,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之後的俄国将会完
全是另一种前途,而一九一七年的“雪崩”也就不会发生。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
杜马反对派与以维特为首的政府当时也确实多次谈判,试图和平解决危机。然而由
於种种因素的掣肘,谈判未能成功。维特由於过分“温和”,终於被沙皇一脚踢开
,由主张警察统治的戈列梅金与斯托雷平相继登台。他们对反对派使出了致命的铁
腕。一年之内,第一、二届杜马相继被强令解散,立宪民主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
该党的土地问题专家赫尔岑斯坦与活动家约洛斯惨遭杀害,米留可夫避难海外,参
与了反对派杜马议员《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被交付审判,立宪民主党机关报
一度被查封,许多城市的立宪民主党组织、俱乐部和他们控制下的一些地方自治局
被捣毁。由於大批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被剥夺选举权,也由於修改选举法并动用“
黑帮”极右分子进行威胁与控制,後来产生的第三、四届杜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
。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席位从第一届的一百七十九席猛降到第三届的五十四席
,基本丧失了对杜马的关键影响,整个党组织也处在瘫痪状态,自由主义反对派尚
且无立足之地,比他们更激进的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自更不待言。於是从一九零七
年六月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被解散起,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代”。
立宪民主党人洛吉夫所发明的悲惨的幽默:“斯托雷平领带”(指绞索)成了那个
时代的特征。斯托雷平在全国建立军事审判网点,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
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遍布全俄的绞架,终於把要求
收回“家产”的“子弟们”暂时镇压下去。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
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然而“家长”在镇压了“子弟们”之後,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巩固“大家庭”
,反而实行了彻底的“分家”。一九零七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
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上的“反动时代”与经济
上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不知所措。反对派起先还有气无力地抱
怨斯托雷平“改革不彻底”,但不久就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就连最“激进”者列
宁也宣称斯托雷平“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不仅“很彻底”,而且“
勇敢”、“纯粹”、“丝毫不妥协”,甚至於列宁们原先的土地纲领也“已经通过
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来也简单。从理论上说“公社世界”与私有产权的
差别很了不得,然而人们的现实选择往往不从理论信条而是从利益取向出发的。在
一个宗法大家庭濒临解体时,要不要分家之争往往远不如争夺“家产”份额的斗争
激烈。一九零五年以前俄国的“公社世界”大家庭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暗蚀下变得“
父不慈子不孝”,只是还保留着一层大家庭的温情面纱。而一九零五年——一九零
七年“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就在於:刺刀挑破了这层面纱,透过破口一看,原来家
长与子弟们都对家产心痒久矣!於是对当局来说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赶快把家长
权变为家产所有权吧!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愿先要“抑强扶弱”充当“公社精神
”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
不言而喻,“强者”用铁腕把弱者绑起来後实行的“分家”是谈不上公正的
,由此产生的後果下文还要提到。但一时看来,这样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产
权明晰,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毕竟比种“大锅”地,纳“大锅”税的村社经济有效
率,而铁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这种效率的发挥,於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
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四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俄国粮食产
量一举超过当时西方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一九一三年的
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纪录甚至一直保持到赫鲁晓夫时代才被打破,俄国成了“欧洲谷
仓”、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当时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由於农
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出现繁荣,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一九零七——一九
一四)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二十六亿卢布增至五十一亿卢布,其中外资由九亿增
至十九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一九一三年与一九零零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二十二
点三五,而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棉花加工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二,出口总
额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国民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制造业国民收入增
长百分之八十三,农业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点六,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上前
所未有的。
在市场之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一九零五年的政治热情似乎
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关心的只是钞票,维特在一九一三年感叹道:“这件事过去
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称‘安宁’也有那么久了,但他所实行的制度迄今没有改变,
舆论对之也没有反应,现在舆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口袋里有多少钱……”
於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
无聊,内讧成习,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愈来愈多,而社会民主党内的
两派更於一九一零年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党,彼此从政见直到经费
之类的琐事都斗得不亦乐乎。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九
零九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一潮流的标志。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它体现了俄
国知识分子的“路标”转向。
《路标》文集的七位作者司徒卢威、伊兹戈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
、基斯嘉科夫斯基、弗兰克和格尔申宗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
”论者,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间大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
但现在他们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十九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布尔加科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
“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过於认同;而格尔申宗更尖刻地说:“别林斯基以来
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其结果是使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这
已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
文集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司徒卢威说:“反动”的胜
利不应使我们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而“革命的错误”不仅包括罢工
、武装起义等“挑衅”行为,甚至也包括“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和解散杜马後
引起的抗议活动这类合法行动。文集的作者继续了以往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的批
判,但过去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民粹派以整体(“人民”)名义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
倾向,而如今这种批判则变成了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的另一种极端。
格尔申宗宣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
们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
害。”这就完全背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整体主义的初衷,而沦为一种不分青红皂白
的“秩序主义”了。
《路标》的作者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作出结论: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
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
国家的非宗教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因此“
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只
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再生”。
而“叛逆性”的消除,世界观的重建与“精神的再生”都要求回归传统,回
归东正教、回归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弃对“西方化”的追求。於是,《路标
》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以译介西学而成名的这七个作者,
此时又成了宏扬“国粹”的一代宗师。
“路标”改变之後: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於是在斯托雷平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出了三种趋势:
一是“寻神派”或东正教文化运动。它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
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
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复兴。
为了纠正“非宗教的叛逆性”,实现“精神上的再生”,别尔嘉耶夫、希尔
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
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
“寻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动从斯托雷平时代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後的白俄侨民生
活中。他们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
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这样,《路标
》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
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
,从反思马克思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从而成为
後来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其影响至今不衰。
如今我们很难恰当地评价这批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激进自由主义而东正
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家。事实上,当他们的批判矛头从“激进主义”转向理性主义、
世俗主义、乃至转向整个现代市民社会,并提出要建设“新的中世纪”时,对他们
的评价就超出俄国史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本文不可能涉及的领域了。在这个意义上或
许他们是“後现代”的先智。耐人寻味的是,像米留可夫这样的正统自由派思想家
在後来的白俄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寻神派却超越白俄群体,影响遍及西方
,这其中就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然而对当时来说,在自由主义运动衰落的这股
俄罗斯“国学热”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对俄国社会生活却丝毫没有作用了。用别
尔嘉耶夫的话说:“二十世纪初俄国出现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
,出现了对伟大的俄国文学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回归。”“俄国的文化上层
开始了精神文明的真正复兴,有了独创性的宗教色彩的俄国哲学流派,出现了俄国
诗歌的繁荣,在美学鉴赏力下降数十年後,强烈的美学意识复苏了。十九世纪初我
们曾有过的对精神领域的兴趣苏醒了。”
然而作者在眉飞色舞地讲了这些之後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这种“复兴”
在当时的俄国却已失去了土壤,“开始失去与社会革命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失去广
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他们
“与世隔绝”,“如同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人民(至少在当时)已经把他们忘记
了。以至到一九一七年“激进主义”之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俄国根本没有人还记得
他们仅仅在八年前对“激进主义”作的那些阳春白雪式的批判。
二是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曰政治保守主义。《路标》发表,舆论为之哗然,官
方欢迎,左派愤慨,而立宪民主党内也对它深为不满,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
许多人不愿钻入象牙塔去整理国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的姿态比起
一九零五年来也大为改变了。其中,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B.A.马克拉科夫为代
表的一派实际上已成为秩序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十分强调“法制”的必要,认为法
制在宪政上,为维护法制,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杜绝革命,“使进化过程成为统治
方式在‘生活自身的压力下’渐变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立宪民主党应当给自己
下达“心理上的复员令”,以摆脱心理上的“战时状态”。
与《路标》的作者一样,马克拉科夫也严厉批评了自由知识分子在一九零五
——一九零七年间的“激进”行为,不同的是《路标》的批评主要在哲学和形而上
层面,而马克拉科夫则集中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进行了被後来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之
为“事後诸葛亮”式的批评。他认为,立宪民主党犯了“最高纲领主义”即不妥协
主义的错误,先对维特,後对斯托雷平都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而“他们本来与其
说应该成为敌人,匆宁说应该成为盟友。”立宪民主党只知利用杜马作为反对派的
讲坛,而不知用它来进行“建设性合法行动。”而《维堡宣言》更是铸成大错:“
它基本上是个革命的行动。”
马克拉科夫承认立宪民主党其他领袖与他本人一样既不希望革命也不相信革
命,但他觉得,他们与自己不同之处在於不“害怕”革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
们并不相信革命胜利,或者说是相信革命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就被制止,因此他们便
以革命来吓唬政府:“由於革命的威胁迫使政府作了让步,他便继续打(革命)牌
,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玩火。”由此他实际上得出了与《路标》中的某些作者一
致的结论:“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
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
三是米留可夫派,即立宪民主党原方针的支持者。历史学教授米留可夫在与
马克拉科夫的论战中为立宪民主党在一九零五年风波中的做法辩护。他认为,党并
不是“生活在抽象安乐椅中去进行老谋深算”的,它必须“和俄国的社会生活一起
”忽左忽右地变化,在一九零五年的巨大的社会情绪波动下,党如果无动於衷,社
会就会将它抛弃,而那样的话,“革命”还是照样会发生的。为了使党能在动荡中
“保持中心地位”,它就必须“被迫向它的许多追随者的更为急躁的情绪作临时性
让步”。他指责马氏“把捍卫法制与捍卫某一给定的法律混为一谈”,认为马氏的
主张实际上是为了战术的需要而牺牲党的纲领,“把手段看得比目标更重要。”而
米留可夫看来,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尤其是土地纲领,“虽然是激进的,但并不是乌
托邦的。”
米留可夫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派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
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
一道法律。如今我们不能不说米留可夫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制”一词在自由主义
语汇中实际上是“公民权利规范”的同义语,它当然不能等同於某些无视公民权利
的具体法律,比如说难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必须符合希特勒的屠犹法律,否则便违
背了“法制”吗?
显然,米留可夫主张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派立场,然而面对如此“彻底”
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立场的基点在哪里呢?当自由派仍在进行种种论证以说明应
该从公社的束缚中解放农民的时候,“大家长”们已经很不耐烦地一脚把农民从公
社“大家庭”里踢出来了!你自由派的书生们还有什么可说?
这里的问题也许在於能否坚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场。如前所说,立宪民主
党在一九零五年时之所以众望所归,原因在於它不仅主张“分家”而且主张“分家
”的方式必须公正。大家长不能独霸家产而一脚把子弟们踢出大家庭了事。它的“
强制赎买”主张实质上与社会民主派的“收回割地”类似,都是要求索回被“大家
长”盗走的“家产”而後再公平“分家”的。然而在一九零九年米留可夫可以仍然
坚持“自由”,却很难坚持“公正”立场了。因为这时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
会下层已经涌起了重建“公社世界”的反改革运动,而这与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
入的。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一边是不公
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叫米留可夫们表个什么态好呢?
因此,米留可夫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於苏联官
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勿宁说更多地出於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
尴尬境地。而另一个情况又使得米留可夫们的反对派立场更加模糊。这就是当时高
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传统时代,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沙皇,以“抑强扶弱”的“俄罗斯
独特的公社精神”,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
地主”是俄国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这一
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
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
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
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
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而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颇有些人很吃这一套
。於是随着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米留可夫他们也
在向右转,而“马克拉科夫类型的温和派则在转向更右。”终於使立宪民主党逐步
沦为杜马(斯托雷平的乖戾“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四届傀儡杜马)中诸保皇大党
的小伙计,而整个杜马又变成了沙皇与斯托雷平政府的小伙计。立宪民主党正如米
留可夫自己在党内论开展战中一再提醒要避免的那样,已经落入了一个圈套:“当
他们不可能对政府施加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
於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
代逐渐从历史舞台上“缺席”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於
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对传统体制起着强烈的腐蚀作用,到一九一七年前夕这部貌
似庞大的统治机器已经“自由”得松松垮垮,所谓文官要钱不要命,武官怕死更爱
钱,个个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报国传统信念者已如凤毛鳞角。但是
,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
,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与一九零五
年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说,俄国那时就已差不多注定与自由宪政无缘了。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於“社会情绪”,而
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
张,即只要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
是:当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
”,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强扶弱”。而当一九一三年前後知识
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於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
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
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
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
实际上,俄国知识界与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十九世
纪的俄国盛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
纪之交便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
“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
从一八八四——一九零三年,这十年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反国家罪”,由
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为的演变。在这期间,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军政公职人员
与自由职业者等知识阶层在“反国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体力劳
动者的比例相反地上升了一倍半,两者的地位恰好来个颠倒:一八九零年时,“反
国家”的人中体力劳动者已占五分之三,比知识阶层高出一倍多。这样的趋势到了
一九零五年以後更加明显,据一份统计,在政治性“罪案”中贵族、教士与富商所
占比例已由百分之四十九点一,下降为百分之十六点四,而下层市民(包括工人在
内)则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农民也从百分之十九点一增到
百分之三十七。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本文无法详述
,但通俗地概括说是:在一八六一年“家长”偷走了一半“家产”的情况下,斯托
雷平又允许“子弟”们中的“兄长”放手抢夺剩下的另一半“家产”,并把“弟弟
们”一脚踢开,以此来完成“分家”并换取“兄长”对“家长”偷窃行为的支持,
最终达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变革,一方面又维护了“家长”统治的目的。
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
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
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
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显变化:
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
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
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
第二,一八六一年,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一九零七年後,农民
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护。由於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
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
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
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
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於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
粹主义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於“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
社世界”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一九零五年以
前俄国的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着较多的贫富差别,难於一致行动,而沙皇却可以以凌
驾於贫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斯托雷平改革後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
立独立农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处於一盘散沙状态,不可能成为斯托雷平所
设想的政府社会支柱,“兄长”支持“家长”维持统治的希望落空。而公社本身却
因富人的退出而变成了贫弱户的均一化团体,成为绝望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佳组织
方式。到一九一七年,这种内部认同大为提高并且一致对外仇视富人的公社组织终
於成了“农村大雪崩”的巨大动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对其形成制约。
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
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
。後者举起了自由主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
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因而从一九零五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
成了一九一七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二月雪崩”之後,它不仅在农村苏
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与苏联官方史学的描述相反
,当时沙俄流放地与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它的
成员主要是政治侨民)并不多。
然而改革的另一影响,是造成了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双向异化”。迄今
人们谈到俄国革命,无论贬者褒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实如果就史实而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反对派中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小於自
由派与民粹派。而且俄国的正统民主党人的直接导师与其说是马克思,不如说是那
时已日益的从革命党向议会党演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些俄国人虽然从马克思主
义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诸理论,但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
阶段论那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後的事,而在当时的俄国,他们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
议会民主,反对民粹派的“公社社会主义”与“人民专制”论。因此在一九零五年
以前他们在俄国现实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於自由派。
斯托雷平改革在使自由派陷於尴尬的同时,也给社会民主派与民粹派造成了
难题。对民粹派来说是“时间恐惧症”问题;原来传统民粹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希望
寄托於农村公社,公社解体,希望便渺茫了,所以民粹派历来有“时间是革命的敌
人”之论,主张“马上就干,否则就没机会了”。而斯托雷平改革後公社眼看不保
,民粹派的事业还能有希望吗?面对这一窘境,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人
对传统理论作了重大修正,以“劳动主义”取代了“公社主义”。即认为只要是“
劳动者”,哪怕他不是公社社员而是私有农民,也是革命的希望所在,因此斯托雷
平改革对公社的破坏并不会使民粹派事业失去希望。这样民粹派便逐渐承认了私有
产权,进而接受了政治自由原则,并把“公社主义革命”推到“劳动主义”胜利之
後的下一阶段,实际上接受了正统社会民主派的二次革命。这样,民粹派政党便日
益社会民主主义化了。
而对正统社会民主派来说,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问题是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
带有抵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恢复传统公社的“反动”性质,由此产生了“人民恐惧
症”。在这些书生看来,为富不仁的统治者可厌,“反动”的人民可怕,於是只好
独善其身,做纸面上的“革命”者。面对这一窘境,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
中的非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则从“夺到政权再说”的考虑出发,实际上把传统民
粹派“公社主义”与“人民专制”之说变成了自己的理论,并转而斥责民粹派留恋
“小私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时他们也与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决裂了。这样
,在民粹派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同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却日益民粹主义
化了。这种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双向异化”使得民粹主义在取代自由主义成为
反对派主流的同时又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民粹派被民粹主义化的社会民主派挤
下去的可能。
总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
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
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
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於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了不
“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了。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
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
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
,也冲毁了公社精神、都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
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
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
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
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
“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
立。
“雪崩”、“人民专制”
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虽然处於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但从精英层面上看并没
有什么“革命”先兆。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极力描述布尔什维克如何精心组织
了“二月革命”,但实际上该党当时不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动於海外“政治侨民
”中。就在这年的一月,身居瑞士的列宁还不无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
许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看来此时年才四十多岁的列宁已在作终老他乡的打算了
。然而只过了四十天,意外的惊喜便从天而降: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眼便胜利了!
胜利之快使他甚至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的确,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显得那么“突然”,从沙皇到列宁,从极左派到
极右派,无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於一件“小事”:二月二十三日(俄历)彼得
格勒“由於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
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加骚乱的组织,於二十六日下令解散杜马,
不料杜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戌部队有几个团率先
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於被
迫在三月二日服输,临时政府同日成立。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
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B·卡万史夫
後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可以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
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姆斯季斯拉夫基回忆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无知少女
一样。”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则说:“革命犹如睛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
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
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苏联早年著名革命史作者H·苏汉诺夫所言
:“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
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
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於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後,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
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制
。从二月到十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
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
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
“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为了抢占潮头,这个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帮杜马”
不但抗旨逞强,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时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职能,从国
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後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八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
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
命民粹派,最後在十月的冬宫之夜,後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
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
的末届临时政府。当时人们对这一後来被称为“十月革命”的事件并未感到过於吃
惊,以为不过是八个月来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罢了。直到次年一月立宪会议被解散,
六月左派社会革命党被赶出政府,人们才恍然大悟:“人民专制”中更严厉的铁腕
诞生了。
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
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国人(包括下层在内)绝对生活水平实际都有提高,但社会上的
不公正感在战时困难的触发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
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
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波企尼科夫在五月十九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
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斥责斯托雷平“为私人而对公有土地发动掠夺”并表示临
时政府立即纠正这种“专横的”不公正。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
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後,“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
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
对改革的清算引出了“社会”对“个人”的专政,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也厄运难逃了。
主要代表知识界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一九零五年判若宵壤。在既不
能“说服庄稼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
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一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再
版,然而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而苏维埃
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其中最主要要求是“在哪
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
和村庄”则应在“肃清”他们方面展开竞赛。接着在取缔了立宪民主党後,又宣布
把“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并为此致信高尔基,劝他不要
“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
局,於是学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
腾了知识分子?
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
起社会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
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这恐怕才是自由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
为,只要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
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
。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於: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
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
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怕也就不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