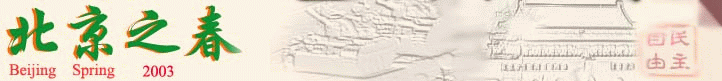俄国流亡作家科培列夫的生命事业
(德国)廖天琪
在谈到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主义大国时,一般认为中国先跨出
了经改的步子,俄国则由戈巴乔夫先启动了政治改革,不少中国人看到俄国的社会
主义在帝国解体,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而市场经济至今始终上不去,一付落魄穷
措大的味道,就有些瞧它不起了。再看中国近年来经济发烧,人人争相下海,少数
人富起来了。炒股票、炒地皮、卡拉OK,好不热闹,连俄国的年轻女郎都上中国
来镀金了,可不,中国人真抖起来了,沾沾自喜之色溢於言表。务实精神使得中国
人缺乏悲剧情怀,并怠於思考,不说对反右文革这些历史大事不进行真正的反思,
连对近在眼前的“六四”的记忆也都被一股席卷全民的淘金热冲得苍白退色,不错
,中国人也许更富於喜剧精神,阿Q杀头前,那会儿挂牌游街时,心理不觉悲哀,
反倒认为一大群人仰头围观,暗地有点喜滋滋的得意。
俄国的政改和中国的经改都不是偶然的,中国人勤劳实干,搞了几十年的一
穷二白,有朝一日尝到点物质主义的甜头就会往油锅里跳,这是中共领导最清楚不
过的,邓小平不过顺水推舟罢了。戈巴乔夫也并非圣贤之人,却是个识时务者,数
十年来苏联的异议分子不但捉不完,反而“里通外国”,得到国外的支持,内外施
压,苏共日子不好过,戈老没有邓小平那种“死二十万人,换它二十年的稳定”的
大气魄,他的前任敢派坦克到外国去“维持秩序”,他却没胆量派坦克压自己的人
,这点他也输给了小平同志。
五十年代毛泽东开始整肃文艺界,许多人遭殃。像胡风、俞平伯、冯友兰、
梁漱溟这些人以及反右时期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加上揭开文革序幕的吴晗、廖沫
沙等人全葬送了。即便活过来,许多人的人格和风骨已经荡然无存了。像魏京生、
王丹、陈子明这样的勇者和智者在中国十二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是中共
的高压和连坐法的严酷夺去了人们的正义感和勇气呢,还是中华文化里知识分子和
统治者之间的嗳昧关系在作崇?这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当年
的红卫兵和曾经参与了各种批斗运动的人不下百万和千万,然而如今回顾检讨当年
运动的人,几乎都清一色地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这样巨大的“触及人灵魂”的大
革命总不可能是一小撮坏人干的吧?缺乏“忏悔精神”是共产党的教育所致,还是
可以溯源到儒家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六四”以後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学生及
民运人士流亡,其中不乏在国外站住脚跟,继续为民主运动努力的人,但有一部分
人士的表现令人不敢恭维。那些落难的“保皇党”,以为等到某人复出时,自己就
能回国平步青云,竟在国外就开始封官许愿,这类人中毒已深,民主、人权、自由
、独立人格对他们说来是解读不通的化外之语,不值得在此一提,但即便在“广场
派”中,也有人自命精英好汉,既不检讨过去的失误,也不利用在国外的机会好好
地学习进修和创业,似乎不知道“广场”这块招牌也有吃光用尽的一日,至於因去
国失意,返身拥抱伟大华夏文化,讥讽西方社会肤浅功利,甚至不甘寂寞,重新投
入中共怀抱,将自己共事的同志出卖者也在有人在。到底一名流亡者应该怎样处理
自己和母国的关系,身居海外还能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吗?这是第三个问题,笔者
想藉俄国的流亡知识分子科培列夫的一生来作解答以上问题的参照。
青少年时代1912——1933
一个在犹太基督教文化和共产主义信仰之间徘徊的青年
科培列夫Lew Kopelew(1912——1997)出生於十月革
命前五年的一个乌克兰的犹太家庭中。父亲为农业专家,家境小康。在孩提时代他
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十月革命成功,末代沙皇全家被谋杀,他家所在的基辅市成
了白色恐怖势力和红色政权争夺的地盘,周遭的邻居,亲友甚至他父母都被逮捕。
由於他们的犹太身份,其危险性又比别人增高许多。科培列夫从小在家中被不同的
女仆带大,她们有的是信仰东正教,对沙皇忠心耿耿的老实俄国人;有的是信基督
教的德国人,他被灌输了是邪恶的犹太人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的知识。列宁的死亡
,红军建军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夺权步上流亡生涯,到一九四零年在外国被斯大林
特务暗杀,所有这些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像走马灯一样伴随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
代,他早熟地注意到母亲为了保护一家老小,怎样在不同的人面前以谎言掩盖自己
的出身和宗教政治观点。由於基辅是个种族混杂,宗教文化迥异的城市,科培列夫
从小就养成一切人都平等的观念。加上当时俄共提倡国际主义,中学里就教授世界
语,这就更为他日後的宽阔心胸和对异类的关心认同打下了基础。
中学毕业後他当了几年工人,二十一岁上大学,开始学日尔曼学,这後来成
为他一生努力的事业。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笼罩在共产主义思潮的狂想气氛
中,马恩列的作品当成圣经,後来还加上新上台的独裁者斯大林的著作。俄共发动
了宣传机器,鼓吹集体化的优越性和大农场Kolchos的诸般好处,说农业机
械化很成功,粮食生产量提高,各地都有大丰收。报纸上日日宣传说全国工厂如雨
後春笋般建立,设备优良,工人生产积极性高,实际上一九三二年秋季苏联全国闹
大饥荒。城市居民缺粮,政府就逼地方上缴粮食,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竟饿死了
几百万人。当时全球性经济危机,各国自顾不暇,也没有能力提供帮助。斯大林政
府当时非但未警觉到大灾难的发生直接和腐败无能的官僚干部有关,反而说是因阶
级敌人的捣乱才引起生产不足和运输工作的混乱,政府借机开始清党,排除异已。
科培列夫当时已是党员,作为铁路工人小报的编辑,他和几名同事下乡参加
征收粮食的工作,并进行实地报道。他亲眼见到乡下到处路有饿稃,心中很是矛盾
痛苦,然而对一个才二十出头的青年,共产主义峋丽的光环暂时还没有消失。很多
年後,他进入壮年,逐渐看透了俄共利用这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大行其
专政的虚伪性时,他写道:“我当时参加乡下的征粮工作,这是个无法推卸的罪责
,不能原谅的错误,此罪只靠祈祷是无法洗脱,也永不能补偿的。唯一能作的赎罪
工作是诚实的面对这个罪责。”这段残酷痛心的经验记载在他的自传“给我创造一
个偶像”(Und schufmir cinen Gotzen , Munc
hen 1981)里。
中年时代(一)1941—1955
——法西斯主义的短痛和共产主义的长痛
一九四一年科培列夫以关於席勒的戏剧理论为题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法西斯肆虐欧洲,德军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一九四一—
—四五年他在苏联红军里当宣传士官,以评议文字来对纳粹官兵进行心战,写了很
多诉诸德军的道德和理性正义感的小册子和传单,这些文字後来收在“文字武器”
(Waffe Wort,Steddl Verlag Gottingen
1991)一书里,步入中年以後,他曾经回想这段经历,扪心自问觉得心战宣传
要求兵士背叛自己的国家,放弃军人的义务而投诚到敌对一方,这种做法违背了他
自己的一贯信念,因而深感不安。
战争接近尾声,他看到红军在东普鲁士占领区对平民的残忍暴行和肆无忌惮
的破坏掠夺,就反过来对自己的士兵进行游说和教育,要求他们对德国平民给予人
道的待遇。为此他被开除党藉并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刑狱,罪名是:“具有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思想,同情敌人,削弱我方士气。”从一九四七——五四科培列夫被关
在Scharaschka监狱。这里是苏联政府囚禁科学家、高级技术人员和知
识分子的地方。犯人被分派特殊的任务,他们得继续为国家从事科研项目。科培列
夫因是语言学家所以就被分配到跟物理学家索忍尼辛一道进行一个如何精确辨认人
声音的研究计划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其实是被克格勃KGB拿来干窃听勾当的。索
忍尼辛在他的小说“第一循环”(Der erste kreis,这第一环指
的是地狱)中写过一个名叫Rubin的日尔曼学者犯人,指的就是他,这一段漫
长的狱中生活科培列夫自己则记录在他的传记“安慰我的忧伤”和“永远存档”两
本书里。“永远存档”是苏联的拥有“危害国家”罪名的犯人档案上所盖的印章,
两本书里都有翔实的记录,狱中犯人被挑拨怂恿和指使而互相揭发检举,在监狱中
人性被拷上了双重的枷锁,接受空前的挑战,然而也是经过这种炼狱的考验,人性
得到显彰,有些犯人间从此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像他和索忍尼辛的例子,多年以後
两人都生活在自由天地,而人各有志,後者的许多言行,特别是索氏几年回到俄国
後的狭隘爱国主义的卫道表现,是他不以为然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对这位狱中难友
批评责怪过,只是一迳地保持沉默。
中年时代(二)1956——1980
——从共产主义信徒到人道主义者的艰难路途
科培列夫是在十年劳改的艰难生活中历练成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一九
五六年他出狱後,就开始在大学任职。但他并没有忘却狱中的难友,他经常为认识
或不认识的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挺身辩护,从六十年代起他不断写信给中共中央,提
出呼吁和抗议。一九六二年在全俄戏剧协会上召开的会议上,他发言指出:“斯大
林遗产至今还危害社会,特别是在对个人偶像崇拜作斗争时,还依然被作为手段来
使用。以斯大林手段来克服斯大林遗产,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九六七年他写信给
苏联第四次作协大会主席团:“近来政府对文艺的检查和管制,对艺术作品主题,
内容和体裁的干预,是违反宪法的。”一九六八年的文字狱,杂志“凤凰66”被
查封,主编Galanskow判刑七年劳改,後死於狱中,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
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辩护,像诗人Ginsburg因此被判了五年,科培列夫
也出面为这位下狱的编辑如Sinjawski和Daniel说话,并作持续性
的呼吁。为此他被重新开除出党,KGB的公安人员也对他进行长期的监督。科培
列夫一点不为所动,继续为落难者奔走,他写信给中央,要求改善监狱及精神病院
里的医疗和卫生条件,并要求给他的囚犯友人送阅读品。同一年他在莫斯科作协选
举散文写作办公室主任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当时在政工系统工作的戈巴乔夫来就任,
他指出戈巴乔夫是个走斯大林路线的人。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此人後来竟是结束
苏联极权统治的功臣。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被捕,又是科培列夫首先通知外国记者
并公开发表申明,要求政府放人,他的种种行为使自己和家人经常生活在被捕和坐
牢的恐惧中。一九七七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这在当时对一个作家来说形同被判处
死刑。别说发表和出版作品被禁止,连继续写作都不被容忍。他因而转入地下工作
,将手稿经过传抄的方法向外推出,有时也请外国友人将稿子密携出境,在西方出
版,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科氏仍然毫不气馁,常在家中狭小的厨房(在严寒
的莫斯科大部分人家平日都爱坐在屋子最暖和的厨房里)中和友朋们高谈阔论,计
划怎样曲线式的发表作品和援救被囚禁在狱中或精神病院的异议分子。
老年时期1980——1997
——流亡者成了两个文化,两种社会之间的搭桥铺路者
一九八零年科培列夫和他夫人奥罗娃有机会到德国进行访问。然而苏联政府
已经开始一种把所有异议分子赶出国门的政策,科氏夫妇结束了德国的访问後,就
成了有家归不得的异乡客,因为苏共将他夫妇俩已除籍,并不允许他们回国,这一
趟奥德赛之旅竟长达九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尚在执政的戈巴乔夫不计前嫌允许他们
夫妇俩回国,当时奥罗娃已病入膏肓,她要在死前看故国最後一眼。苏联解体後科
培列夫并未像难友索忍尼辛那样回国定居,这并不是他乐不思蜀把德国当成了第二
故乡,而是他知道在千疮百孔的俄国,他能作的事很少,而在德国他正在进行有意
义的文化桥梁工作,不可半途而废,因此他继续留在德国直到去世。今年六月份他
逝世前交代得很清楚,他的骨灰得运回莫斯科墓地,安葬在他妻子旁边。
科培列夫於一九八零点年被迫流亡德国时,已经六十八岁了,西方知名的大
文学家如波尔和费许都是他的朋友,对这位遭难的朋友,他们都伸出友谊的手,给
予他精神上和实质上的巨大的支持。德国总理亦私下为他向克里姆林宫求情,让他
能返回家园,未获允许,由於是日尔曼学家,科培列夫在德国的社会发挥了他累积
了几十年的文学语言知识和经验,充分地放出能量。除了写作,编辑和出版他自己
的文学和学术著作,他也积极帮助国内同行,使他们那些在本国无法出版的书籍在
国外问世,他在科隆的家中经常高朋满座,艺术家、学者、朋友、学生、记者爱围
绕这位豪爽热情又健谈的老人,到他家里,人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书籍和半新的旧
衣服或半旧的家用电器去送他,因为大家知道他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国内友人向
往并需要的书籍、药品、甚至营养品和衣物送到他们的手中,到俄国去旅行的友人
也都愿意当他的差使,替他携带这些东西。
科培列夫从一九八二年以来就在雾泊塔儿(Wuppertal)大学里主
持一项庞大的文化交流计划。内容是将德国文学里的有关俄国和俄国人以及俄国文
学里有关德国和德国的部分整理翻译出来,汇编成集。一九九零年当东欧共产国家
变色,他又已经回过国之後,他说了下面的话:“我的工作在这里(德国),只要
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把雾泊塔儿的项目作完,死了以後再回家(俄国)不迟。”他
真的作到了,他主持的项目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七八本厚厚的文学集子早就已经
问世,这对德国和俄国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提供了极大的贡献,双方都能在
对方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对方的眼光和心目中的形象。科培列夫在德国
得到很多高荣誉的奖,像一九八一年的德国书商的和平奖,一九九一年北莱茵省的
国家奖和奥斯那布克市的雷马克奖,德国社会尊敬并爱戴这位替两国文化和人民搭
桥牵线的仁者和勇者。
总结
1、科培列夫曾是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个人道主义者。
他经历了法西斯战争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
三十年代的大饥荒让他明白了一个政权的谎言是要人民付出千万生命为代价的。他
忏悔自己当年曾经是“帮凶”,战争结束时他认清了以暴易暴只能继续制造仇恨和
悲剧,他不惜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制止这种恶性循环。十年的刑狱也没有动摇他
的勇气和信念。出狱以後他反而开始向专制极权的政权挑战。一九六八年苏联进军
布拉格,此时,他对共产主义最後一点的希望也幻灭了。从此他更加以人道主义精
神来对抗不人道的制度,以诚实的态度来对付谎言。
2、从流亡者到世界公民
被迫流亡的科培列夫虽然始终保持了他的俄罗斯灵魂,却并不以“游子思乡
”之情而返身拥抱俄罗斯母国的“伟大传统”。鉴於德俄之间本世纪的宿怨他投身
从事疏通化解两国的误会和怨恨的文化工作,年高体衰和丧妻之痛也没使他放松步
伐,当成果累累时,他才撒手而去,科培列夫自己享受到自由之後,没有一天停止
关心他尚在极权高压下生活的友人和同事,他竭尽所以地去接济他们,并不断地为
尚在狱中的人道呼吁求援。
科培列夫没有把客居的德国看成暂时栖身的他乡异地,他积极地参予各种活
动,对社会出现的怪象如敌视外国人的排他主义,他极力抨击,并成立了一个“外
国人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化解人们的心结,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3、不是精英,也不是大师,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像科培列夫这样言行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多,除了和索忍尼辛,萨哈诺夫,叶
甫图申科等知名的以外,还有数十个有名有姓的异议份子,他们有的还没等到政权
变色就死在狱中,有的存活下来,如今过着依然贫穷谦卑的生活,他们不自认为精
英或英雄,人民也并不这样看待他们,唯一不同是他们活得心安,觉得自己作了分
内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