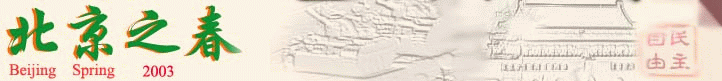“邓後”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能性选择
——兼谈海外民运的角色困惑
(法国)安琪
对所有的人来说,九十三岁的邓小平之死,实在是意料中的事。但是,这位
中国现代社会最後一个帝王生命的终结,同时也预示着强人政治的结束和共产党专
制极权的解体。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政治结构的转型,面对中国社会累积难解的各
种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和官僚腐败引起的民怨,价值观的普遍丧失等等,就变得分
外沉重。不可避免的高层权力纷争,增加了某种变数,对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坚
持实现政治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派来说,是机遇,也是风险。
但是,把握时机,不等於投机。参与政治,不等於介入权力。中国知识分子
如果不要被社会变革的大潮所淘汰,首先应该独立其精神,昂扬其人格,从传统的
“士大夫”角色中挣脱出来,以一种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的群体意识,
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承担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应有的社会历史使命。
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选择,之後
又在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选择,再之後胡死赵离任了,就在所谓代表改革
路线的邓小平和代表极左路线的陈云之间选择,陈云死了,又在邓小平和陈云的代
表者邓立群之间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跳出共产党极权制度下
所仅有的有限选择的怪圈——如果我把它称作选择的话。到了“六四”後,这种选
择更显得尴尬,无奈。因为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差异。从这
个角度讲,邓小平嘲弄了一代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选择怪圈中,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失去了两次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的机会。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当时中国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否定
“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出任国家重
要领导岗位,共产党内改革派力量占主导,开始了经济改革等重大变化,同时对毛
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重提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
使得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局面。
这时的邓小平,由於自身三起三落以及累及儿女,爱子邓朴方受害致残的个
人体验,他对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不是没有考虑,这在他当年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
。但在实际运作中,他却比较被动,现出两难之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头十年
,中国进入了一个逢单改革开放,逢双反自由化的循环。分析这一过程,我们会看
到,这一循环不是恶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虽然很慢,但是在向前走的。因为
每一次循环之後,自由化空间都会有所扩大。到了八九年,反自由化一词已成为中
共极左派的专用名词而不再被提及。当然,这种自由化空间都是人们争取的结果,
但是了解中国政情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权力高层某种程度的默认,任何努力都只
能带来更为严厉的控制。“六四”屠杀後的情形就是这样。
致命的忽略
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良心自称的中国知识分子,原本是有机会表达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争取新闻自由、保障基本人权的诉求的。但由於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
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所以不可能有知识分子群体的声音,零散的表达,形不
成压力。至今为西方知识分子甚为不解的,是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对邓小平重判“民
主墙”活跃分子魏京生的麻木不仁。如果说这样一种忽略可以解释为被“胜利”冲
昏了头脑,没反应过来的话,那么在之後的几年里,隔年出现的反自由化,清除精
神污染等政治运动,早该引起知识分子的警觉,团结起来,采用一种不介入党内权
力斗争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方式,并诉诸解决问题的诚意。将问题提出来,解
决一个,再提下一个。有了这样的独立性和诚意,我想邓小平也不是没有可能被迫
做出某种让步。事实上,邓小平是第一个实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且带头退休的
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同时,他也提出过“权力不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警告。悲
剧在於,他自己并没能走出共产党政权封建家长制的旧巢。这种封建传统政治的逻
辑特征就是,即使你不想当“家长”,也会有人要你当“家长”。除了邓小平个人
说了算的不自觉外,党内极左保守派势力与改革派的矛盾与斗争,改革派内部的矛
盾等等,都要邓小平来拍板。於是乎,邓小平便轻而易举地继承了“毛家长”的权
威。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就象八一年代表社会党的密特朗出任法国总统而消
融了认同社会党理念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精神一样,邓小平初期的中国知识
分子,同样丧失了本来就很弱的那么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传统的依附性再
度膨胀。“民主墙”时期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派第一次联盟的历史经验,最终演
变为知识分子“精英”纷纷在党内高层寻求政治靠山,党内改革派则在知识分子中
寻找代言人和助手,当时的流行称呼即“智囊团”。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一旦做了
谁的“智囊团”的一员,不管是真是假,好象都是在“替天行道”。不同的“智囊
团”和“智囊”又有自己不同的外围圈子。风气的蔓延使得一些一“沾边”就跟沾
光一样乐此不疲(至今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搞清“智囊团”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并直接介入了高层权力争夺战。那些与权力中
心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民主理念与思想,他们的思考和贡献,以及因此而
遭受的迫害,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正义的声援,反而显得势单力薄,成为孤独
的少数。“民主墙”时期的重要文献《论言论自由》和它的作者胡平的长期被冷落
即是一例。直到“八九”後精英大逃亡,都成了流落它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情
形才有所改变。这种现象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虚荣、恋权与不独立,使他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权力的
中心,对全社会、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几乎等於零,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
”的基础。发展到八九民运,知识分子的表现就更是可圈可点了。有的“文革”中
的造反派,这时也成了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代表,不封自许地成了学运的当然“导
师”。岂不知他们身上那种难以掩饰的“造反有理”的精神留存,恰恰构成了对民
运的伤害。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运动後期,我看到扶赵倒邓的口号压过了争民主
、反腐败的呼声,将重心完全偏到了权力争夺的一边。而这一次机会的滥用或丧失
,同时也削弱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
分析这一过程,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於知识分子选择的错误,而
是知识分子对这种错误选择的自觉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民运人士”的角色困惑
以流亡民运人士自居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
所谓兼具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双重身分者,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成分:一、
“八九”前即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的,主要指中国民联及其同盟与支持者;二、“
八九”流亡者或原在国外进行访问,因“六四”屠杀而与中共决裂滞留不归者,这
部分人大多以当年的民阵为中心,後来的民联阵和其他民运组织中也有一部分;三
、投入海外民运,但不介入民运组织的独立活动者。在这三种不同成分中,又有体
制内、外之分,学者、作家之分,记者、自由撰稿人和留学生之分等等。细究起来
,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民运分子之分。但因都是在海外民运的大范畴内活动,故沿
用惯“例”,统称为民运人士。
从个体分析,他们中间的确不乏独立思考者和具备独立人格者;但整体看,
情况并不比在国内时好。角色的转化,充其量不过是名词的变换而已。在自由、民
主的口号下,掩盖着与共产党毫无二致的政治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几年
来,海外民运从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即是证明。其中,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批评也很多,恕不赘述。
我想指出的是至今存在而不为人知、或“为人知”而“不为人说”的潜在的
危险,即那种对八九民运构成过伤害的、毛式斗争的、永远有理的造反派精神。我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种潜在的深刻危险,直到今天仍在海外民运中继续,
甚至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警觉。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对八九民运进行反思的时候
,由於这种潜在的危险和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所谓“民主意识”的影响,使得所
有的争论都转化为毫无意义的“口号之争”或“人事之争”。
我认为,就目前来说,跳出角色困惑,是海外民运面临的首要问题。也就是
说,要准确无误地了解民主到底是什么?长时间以来,在角色混乱的民运精英中,
有的人很自然地把民主等同於革命,把民运的目标定为夺取政权。这种概念混淆,
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是有害的。道理很简单,革命成功了,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了民
主;以民运的名义获得的政权,不一定证明就不搞独裁。而且,把民运和获得权力
连在一起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清醒地面对“邓後”。从这个
意义上说,“邓後”的来临,对海外民运也是一次表达机会。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过
程中,仍一味地喊打倒,推翻之类的口号,显然毫无意义。你讲民主的大道理,共
产党内的改革派也讲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实际情况是,经过红色恐怖和经济冲击的
中国人,谁也不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漂亮的语言修辞了。共产党在政治转型的权力斗
争中不得不考虑民意。海外民运要想真正在大陆发生作用,也不能离开民意基础。
民意要求海外民运增强民主意识,重建公信力。民运精英的责任还在於,团结海外
留学生和华侨,拿出适合中国民主发展和民意的政治主张,表达争取民主的诚意,
争取成为一支真正的以自由、人权、民主为终极目标的民运队伍,最终成为能够制
衡政权的民主力量。反之,那种“闹灵堂”式的抗议,不应该再是海外民运、特别
是知识精英的表达方式。
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应该通过反思和总结,明确自已的目标选择,对终极
价值,对社会正义应该有一种基本的认同和标准,并在同一理念下达成共识。对社
会不公和遭受迫害者,应该有一种声援;同时,知识分子应当有甘当永远的持不同
政见者的勇气和品质,参与政治而不是介入权力争夺,关心民生疾苦多於接近权力
中心,从事民运而不是为了满足权欲,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形成一个不介入权力
斗争的、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此,中国崩溃中的价值底线当得
以补救和重建,真正的民主意识当得以普及和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