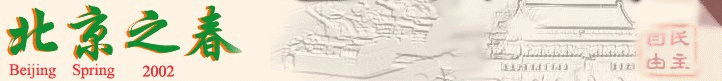我们显然有些共同的看法,例如,中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的愿望被压制,这
些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中国只有民主化了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些共同看法并不
能掩盖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对於不同观点的发展和完善本身也是
必要的。我想就这两天的讨论争论中表现出的两组分歧引出反对运动的战略思考。
第一,在讨论中,受过严格实证训练的学者主张,客观地理解和看待稳定性问
题,不要搀杂主观愿望,毒化学术解释。这些学者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结构功能方
法、历史模拟方法等框架力图客观描述。
我怀疑这样的实证方法在解释和预测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迁的有效性。我研
究历史,历史学界的看法是恢宏的,牵扯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以复杂的方式相互
作用,很难以可行的实证方法所能容许的少数变量来描述;如果遗漏了某些对局势
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变量,就会失算。而历史发展中这些决定性因素经常发展变化。
所以,第一个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你为了应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你必须简化和
抽象现实,以便把握主要变量。忽略什么和选择什么就有主观偏见;而选择什么几
乎就决定了你会看到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即使在自由国家的学术界纯粹为理解现
实,这种选择也极有争议;如果在公共舆论讨论空间,就更会受意识形态支配。在
一个独裁国家,客观、开放、自由和公正研究本身就是挑战极权,是不被允许的;
此时,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问题,逃避政治迫害和禁区。这些学者的处
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由於这种局限产生的成果的先天不足。
例如,不少学者谈论经济没有看看库存量。这个指针在中国已经到危险的度了
。目前大陆库存商品已经达四万亿元人民币,占去年GDP的41%强.按国际公认的标准
,库存商品与GDP的比率,发展中国家以不超过5%为好,现在大陆已经超标八倍.宏观经
济管理,就是私人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也要关注这个变量,但中国的学者谈论形势并
不理会它。在库存量严重超标时还能维持的繁荣既是有问题的,也是靠不住的。
再例如,学者喜欢在开放社会中用民意测验或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现实稳定性
。可是,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必须小心。我们知道,动摇人心乃至稳定的最大问题
一定是人民最不满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关于稳定性的民意测验中回避老百姓最愤怒
的问题,那怎么能评估影响稳定的人民情绪呢?可谁又能去公开调查那些爆炸性问
题呢?因为提到这些问题就是被禁止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客观理解的最大失误的根源还不是选择变量的局限,而
是历史是活的,不断被发展和改变的;其中,人的愿望和创造性选择才是历史的直
接动力。没有某种同情投入的理解,很难把握历史的方向。人的介入和不介入以及
怎样介入,会有不同结果。而且,各种力量一定主动或被动地积极为维持或牟取利
益而行动;这些选择会影响局势走向和结局。
在所谓实证研究的争论中,我的观点是,应当有积极的政治参与的角度评估稳
定性。我高兴地看到,王绍光和孙哲教授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对稳定性的乐观估
计并不建立在客观的调查上,而是计算考虑了人的选择因素。尤其是孙哲教授,主
张我们应当积极介入解决问题,这才是稳定的真正可靠保障。
但如何介入,我与他们有分歧;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组分歧。绍光和孙哲相信
,中国政府可以在现行体制内通过正确的体制、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性选择解决问题
,维持稳定。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显然,晓光先生的结构/群体分析也不会认为他们的对策可
以解决问题,因为神圣铁三角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这些问题之上的,腐败收买精英
是这个基础。徐斯俭教授问晓光的问题,点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延误时机。他说,以
台湾政治发展的经验作为参照背景看,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基础上的精英联盟会以
行政消化政治,解决问题,而不是拖延解决问题从而使问题日益严重?孟玄先生引
用裴敏欣研究员的最近的文章说,大陆以这样的心态错过了最好的政体变革时机,
现在由於没有体制积累,问题更危险了,而且;越来越危险。如果这是比绍光和孙
哲更现实的估计,那么,中国今天的稳定是为今后不稳定做铺垫。
我的最大质疑还不是从这个角度展开。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的选择是稳定因
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当然应当首先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这是胡平的
问题,稳定的意义是什么?何频已经说了,中国早就不稳定了;对许多老百姓而言
,经济机会、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既不安全,也不稳定;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所谓
稳定只是权势者在维持权力结构意义上的稳定。胡平指出,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压
制大家(包括镇压者自己在内)公认的好人基础上的稳定,是压制大家公认的可以理
解、值得同情的要求的稳定。难道这样的稳定应当继续维持吗?我们当然需要稳定
,但是,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良心标准的稳定,要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稳定
。这样的稳定不是现在的政府能提供的;到不是说他们很坏,而是因为体制决定了
他们的容量和局限。
我的观点是,能够提供这样的稳定的只能是自由民主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
,人民? i以选择领导和政策,这种公正程序产生的决策以及人民享受权益可以保持
稳定的人心,而稳定的人心是稳定的最大保障。这样的稳定必须要由一个反对健康
的运动来创造。
晓光和何频都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都对在现行体制中解决问题不乐观,但同
时他们又都看不出别的希望,从而认为这样的体制会继续维持下去。我的看法没有
晓光和何频那样悲观。诚如胡平所言,如果镇压象秦始皇所设想的那样灵验,可以
镇压反抗,维持不义的话,我们今天应当生活在秦千世或秦万世的统治下,而不是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其实,晓光和何频的悲观都来自中国目前解决问
题的动力不足,而反对运动就是提供这样的动力。一个强大的反对运动会推动中国
改变。
这也顺便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中国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力量;反对运动正是
一种对共产党的替代性选择。只不过,反对运动不是坚持以自己替代共产党,而是
创造一个体制,在其中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
我知道,马上会有人说,没有这样的反对运动;中国的反对运动证明,不能指
望反对运动。这里,才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发展一
个强大的反对运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建立正义基础上稳定繁荣的中国。
没有人比反对运动的参与者更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反对运动的挫折所带来的痛苦
了。然而,这些挫折并不表明反对运动的不必要和不可能成功;所有这些,不过说
明反对运动确实勉励困难,需要调整自己。
反对运动是必要的。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已经有言论自由和压力团体,仍
然需要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在中国这样的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
权势者有无限权力却不承担失败罪责的极权国家,反对运动更是不可缺少的监督力
量。经济改革和发展并不自动产生公平和正义,必须有政治改革才能让全体中国人
分享发展的成果。
以往反对运动的衰落有大的历史背景原因,谁也无法左右,更重要的还是反对
运动的战略。过去,反对运动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标,又缺乏适宜的发展战略,还
缺乏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这是主观原因。我相信,如果采取适宜的战略,反对运
动就可以回到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心,影响中国的命运。
反对运动必须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必须扩展自己的基础和成分,力图卷入所
有中国人,不分职业、宗教、阶层和地位,特别应当避免外国化、精英化的倾向。
为得到中国人的拥护,反对运动应当关心现实问题,研究响应政策,以理念批
判现实,使民众意识到,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公正,从而动员民众的支持。
我们目前正在推动宪政协进会,就是希望民运有个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