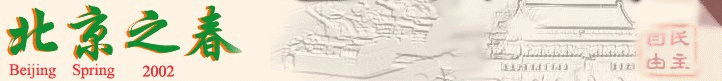拙作《为了明天》刚刊出一半, 就读到《北京之春》上关于独立笔会暨《倾向
》杂志给王力雄和廖亦武颁奖的报导,和在新泽西举行的六四13周年纪念座谈会的
发言。两会发言使我深受感动,启发我又有很多话要讲。现在特就两次会议提出的
某些问题,同各位探讨求教:为什幺至今没有文字留下整个民族的记忆?
首先,我在这里摘录几段陈军的发言:“写作是为了延续一个种族的记忆,保
存它的文明成果,促进人们在精神上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信念,使得人们在各种死
亡、灾难和恐惧面前不致因为孤独或其他与生俱来的脆弱的特质而崩溃。”当人们
纪念六四13周年,担心人们只留下对屠杀的恐惧而遗忘了六四的目标和勇敢、富有
正义等善良品德时,胡平、王军涛等在会上立即表示同意陈军的上述发言,希望我
们能尽快读到这样的人格化的记录民族的记忆的作品。那幺,事过13年,或者说,
民运已经20年,为什幺,还没有这种记录我们民族心声的作品问世呢?
现据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做一点分析。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前后拖拉十年以上
,动笔几次写不下去的困难在於如廖亦武说的,我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我在所有
右派面前“是个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来”
了,尽管我也如他所说,“但我有脊梁、有血、有眼泪,”却仍然感到像狗崽子那
样矮得仰头看不见人脸,怎幺也不易交待清楚。我是在中共在六四后,在我于1997
年回去后还一再把我当狗打,在我继革命战争时期,继“六四”1997年后,又为中
国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好事后,它仍以‘不可接触的贱民’对待我,甚至有可能对
我施加新的迫害的同时,我自己又在最近几年努力吸收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
系列成果,自己精神上有新的升华,即从一个独立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批判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錾新地感到自己自1957年开始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立思
考已经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时,才感觉自己可以对当年同苦命的右派,如今的民运同
仁可以有所交待了,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才感到自己写的也许真可谓是一部民族
的记忆,值得写完它时,我似乎才感到争得了写作的自由。总之,要自己感到1有王
力雄他俩那样有基於政治争议的自由,不是单单有愿望揪可以做到的,必须有深刻
的反省和理念上的升华,才做得到的。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写’,而在如何认识自己。所以写作层面的问题必须从
社会层面去剖析,陈军说:“比较其他民族的流亡者,我们未能将各自的境遇变成
某种文化创造的源泉...反抗使我们生活和心灵有了可以认定的意义,但也使我们可
悲地成为这种制度的衍生物...如果我们仅仅成为这个制度的反抗者...那我们会注
定会成为有缺陷的人。我是说,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个时代和这种
制度加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在反叛的同时有另外的比单纯反抗更宽广,更丰富意义
的人生价值和心灵品质的选择?说白了,就是你要反抗共产主义,你必须超越共产
主义,而不仅仅是对民主的单纯的追求的愿望和推荐。
何频先生的话最直截了当,他说:“十三年了,为什幺越来越没有听众?为什
幺越来越无力?究竟是这社会太堕落还是民运人士堕落了?流亡这幺多年,你有什
幺收获?除了大家彼此消耗,彼此受到伤害,使民运这个词蒙羞,还干了些什幺..
.我看是离现实越来越远,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没有调整自己...流亡,已不是政治
资本,而是负债,你不是被流放到更荒凉的土地上,而是到了自由、富足的国度,
可以读书,可以成就事业,你在这样的地方都不能自立,不能培养良好的心智,难
道只等到有一天空手回国,说‘我流亡回来了’?留在国内的人会接受你吗?流亡
已使你比国内的同道少了道德优势,如果你只剩下民主这句口号,中国还需要你吗
?”
是中国12亿人口都麻木不仁吗?有一种倾向似乎中国发生了中共专制和金钱资
本的结合,而人民则麻木不仁,对民间疾苦缺乏同情心,不仅民心不古,而且堕落
到了只知道追求金钱与物质享受,我很赞赏现在的《北京之春》,但是它发表的文
章中在表杨9-11后美国人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时,屡屡鞭策中国人,似乎如果9-11
发生在中国好像人们只会去趁火打劫。我非常不同意这类论断。
首先,专制统治与金钱资本的结合是全民所有制的斯大林模式,1980年前完全
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共专制统治与党政军掌握全部经济相
结合。千万别弄错,现在是国有经济大为削弱,民营经济已经超过半壁江山,为什
幺江泽民要拉私人资本家入党?就是两者结合得还不好!
第二,腐败不是全民腐败,是一小撮官僚腐败。不能说商品经济已经把人人的
良心喂了狗。只能说,过去人民对共产党尚有幻想,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为人民服务
的,现在不再存在幻想了。至於为什幺不奋勇斗争?亿万人民的社会行动那是要乘
风而起才行的,平白无故不可能上街栏军车阻挡解放军,老百姓也不可能掀起要求
六四平反的运动。
有人说,国内上上下下都没有人提出六四平反要求。这绝对不是事实。我就认
识一个老前辈,他个人就同几十位副省级一上的干部(含政治局委员),副军级以
上的军人(含大军区司令员)探讨过六四平反问题,争取到了其中多数人的同情。
我确知,1999年他还借机会同到某大城市联系工作的几位政治局委员探讨六四平反
问题,而且当某些政治局委员担心海外捣乱时,他说,海外的工作他包了,说平反
只能使海外的反对力量变成合作的力量云云,后来这几位政治局委员心有所动,建
议安排他直接同江泽民谈。此时,他徵求我意见,是不是先同曾庆红谈,我表示反
对。因为江手下诸如王沪宁是对六四平反问题作过社会调查的,包括到香港去调查
过,(这是徐泽荣告诉我的,当时徐显然像安全部的人。)很可惜,这一年长江发
大水,江没有到预定的城市去,我这位朋友又癌症复发,改变了行程。错过了上面
讨论六四问题前夕的时机。也就是这一年年底我同时听到两位政治局委员,其中一
位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说:“明年不改革政治体制不行了。”接着信息显示,2000年
两代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讨论了六四问题的,因为当时曾宣布‘六四问题维持原
结论不变’这就是对某种平反六四的呼吁的回答。
自1997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呆在中国,我自己给规定一个任务就是帮助沟通
,以上这些情况,我在2000年都对严家其、苏绍智等很多朋友说起过。
我也同民营企业家有广泛深入的接触,绝不能把他们归类为同中共专制腐败势
力一丘之貉,他们有很多弱点,但他们是战战兢兢的,随时准备被淘汰出局,被没
收财产的。他们的弱点是信用狭隘,所以成不了类似西方特大企业的大气候,他们
不得不尽量仰仗主要是地方当局,却远没有达到与中共当权派勾结的地步。相反,
据我所知,有些海外活动的媒体还得到过某些私营企业偷偷的支援。
我决不同意那种认为现在大陆全体人民已经道德沦丧的贬斥,相反,现在没有
人像文革时那样会把你私下的发牢骚,去打小报告给安全部门或单位领导了,就是
王军涛说的,“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干预他人的倾向‘比以前’(我加这三字)要少
,在政治生活中,与他们相处比与他们前辈相处更安全,更少麻烦。我想,问题恐
怕像何频所说,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又说,
“关键是我们要有新的视野和图式:其中,对世界极其可能发展前景,大的势
力和政治取向、我们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们和中国的主要势力的政治关系的潜在
合作基础等问题要有数;否则就会碰壁,就会有无奈感,就会在与主要势力的发展
脱节的同时我们自己在主导大陆局势中放逐自己出局。”我在《为了明天》一文中
提出要关心民间疾苦,搞合法斗争,看来王军涛是有同感的。他还理解了现代化发
展中崛起的专业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
吸收现代文明之外,并应该努力思考如何使之适应中国的情况。而是不是只会‘反
对’,特别是仰仗外国政府去反对,尤其要慎用‘制裁’手段,因为经济制裁的受
害者主要是老百姓。
我在国内同自由化知识界有一定的接触,比如,王若水的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两
次接到通知,直到预定日期前的深夜又接到取消会议的通知。我发现,确实有思想
非常自由化的朋友说:“我现在恨那帮搞六四的人!”他们多数不满意的理由主要
在两点:一是当时过激;二是自己遛走后到海外的言行不负责,让在国内的支持者
为难。我发现他们多半对海外民运寄以希望,恨铁不成钢而已,他们甚至劝我不要
同严家其搞僵,要好好沟通,他们真的对一大批老朋友热情依旧。
总之我猜想,那幺多流亡者有很好的写作和发表的环境,为什幺没有拿出东西
来?就是因为每个人还没有回答好诸如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过激和明天怎幺办?
我写《为了明天》就是企图从总结天安门前的过激出发,探索明天,希望各位响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