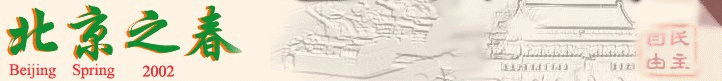六四已过去13周年,中共在这13年内召开了14、15两次党代表大会,现在正忙
於迎接第16次代表大会。过了13年之后,海外民运的接权梦还没有破,还在期盼着
马上有机会回去成立合法的反对党,推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制,从而在国内政坛取
得一席之地。而《北京之春》发表的周舵先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神圣和革命万能
论应该休亦,江泽民已经接近赫鲁雪夫,似乎中国的戈巴契夫很快就会出现……如
果中国真的又一次出现政局转化的兆头,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争取民主的勇士们已
经作好必要的准备了吗?我们梦寐以求的转化将使历史朝前挪动一大步,还是又将
夭折,又一次血溅天安门呢?
没有人能预见明天,更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要分析未来可能出现的
各种各样的动向,科学的方法只有借鉴昨天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经过的历史。那么,
关心中国明天的人是不是已经充分地从历史的明镜中照过人和物,因而吸取了足够
的教益了呢?显然没有。
海外民运这13年在自由天地里忙於什么呢?众所周知,分裂的各民运派系、各
民主人士一直在忙於吵架,争权,却没有忙於争论,至少可以说,没有致力于把不
同政见摆清楚,更没有理出一个是非曲直来。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讥
笑民运朋友:“你们搞革命,却没有学到共产党搞革命时的那种艰苦奋斗精神,而
你们反对共产党,却患了共产党几乎所有毛病,除了没有武器可以开枪杀人。”我
看情况依旧。
目前是非常时期,就是革命尚不可能发动,民主遥遥无期。既然没有条件,就
不要讲谁有权代表谁的利益,特别不要讲利益分配的合理性,而来一点无私无畏的
奉献,那么就请你从打破万马齐喑局面,在没有资金奖赏,没有地位分配诱惑的单
纯的追求真理的,冷静理性的争论来开始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奉献吧!我希望拙文发
表后有人高兴有人骂,却没有冷场。
一、怎样的明天?怎样的形势出现算得是另外一次机会来临?
我们都希望“变”,时刻准备应变,这种心态是不是健康?1988年秋我离开中
国前,中国就有强烈的切盼“变”,的社会心态。大约是是年的八月份,胡耀邦的
身边人来访,告诉我,耀邦的身边人有的力劝他“说话”,有的反对,呼吁他说话
的人们说,“凭你的政治经验,你一定能看出现在问题很多,你应该说话!”我告
诉来访的朋友,“千万别向耀邦施加压力,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请他千万别说
话,因为,他说什么都只能落不是,从而给他惹更多麻烦。”过了几天,大约是八
月下旬,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夕,赵紫阳的身边人也来了,他正式来传达赵本人的口
喻:“千万小心,别帮倒忙,别惹事酿成耀邦下台前那种形势。”我听后,心里一
机灵,这不仅使我想起几天前得知的耀邦身边人的那种不耐烦的急躁情绪,也使我
回忆起1987年底或1988年初出席王军涛,闵琦,陈兆刚和一位民主人士冯先生举办
的《时局与选择》座谈会。他们兴师动众,邀请了从胡启立到曹破产等广泛的各层
次的各界人士参加,并安排了中央电视台现场摄制节目。这是一个自由论坛,但组
织者的倾向非常鲜明,他们也是极端不满当时的死气沉沉,但求来一次政治地震。
比如,他们请人演讲苏联改革,我当时在这个领域非常出名,以“敢说,有见地”
闻名,他们却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很保守的教授来讲戈巴契夫的“500日加速计划”
──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改革计划经济,我听出了会议主持人的愿望──反对赵紫阳
磨磨蹭蹭的“摸石头过河”。更明显的是傍晚会议结束前,会议组织者个别地找与
会者留言,找我的是陈兆康,他这样解释:“等明天到来时,回头看看,你在1987
年底说过什么?”
那种厌烦死气沉沉,巴不得发生一场政治地震的心态也表现在1987年底1988年
初一批名人联名上书邓小平,和一连串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
的筹备活动上。这种种迹象显示的“思变心切”同六四的心理酝酿似乎是一致的,
倒不是说六四可能有人策划。也许可以说,八九民运与这种求变心切有关,是从这
种心态出发的应变!可是将有怎样的变局和应该如何应变,思想准备却显然不足。
根据常识,革命只可能在当权者不再可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时才会爆发,
革命首先以统治危机为前提,而不是革命家准备出来的。那么,1989年春夏中国是
不是存在统治危机或革命危机呢?不存在!
中共十三大以后,整个共产党对大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实行消极怠工,但是
李鹏却抓住“党政分开”这一条向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闹独立性,不让赵继续插手
经济和经济改革。但是邓小平要开放价格,闯价格关,他仍然找的是赵紫阳。邓很
清楚,只有赵有勇气闯价格关。但是,一开始放松价格控制,就引起通货膨胀和抢
购风潮,於是,九月在北戴河开会,在对赵极不利气氛中决定治理整顿经济环境,
李鹏进一步把经济的领导权拿过去了。於是赵紫阳另外提出了“两头在外”策略,
即原料和市场均在海外,他以为,这样可以帮助沿海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以此推
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主张不但招致内地的恐慌,沿海地区
也惶恐不安,当时尚主持上海工作的汪道涵打电话同我谈了这件事,他有意请我去
一趟上海共同讨论。我鉴于在这样的经济问题上没有能力给赵紫阳提供谘询服务,
又忙於出国准备就没有去上海。据吴国光后来告诉我,鲍彤那时已经钻进旧纸堆,
在读《易经》,无事可做了,显然赵的地位岌岌可危。以上这一切说明,当时以邓
、赵为核心的中共在尝试进一步改革,邓小平是同赵站在一边的。政治体制改革虽
然搁浅,但是新闻法,起草了一稿又一稿,结社法也在酝酿之中。当时上海有人申
请成立新政党,上海公安局马上决定以反革命论处,报告打上来,赵的班子批复,
指出上海公安局失当,不过,也还没有允许成立新政党,尤其还没有允许成立明确
的反对党。但是当时被海外讥讽为花瓶的民主党派正按胡耀邦的主张改革,原来那
种不仅发展党员的范围地区均受严格限制,而且组织上不独立,法律上不平等的状
况开始变化,即已经采取措施让共产党员退出民主党派,中共各级统战部不再作为
民主党派的指挥部,对民主党派直接领导甚至颐指气使……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专
家,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把这种民主党派的地位日益改善夸张
为“民主党派也是执政党”,招来港台报刊的冷讽热嘲,我曾协助高放教授为大百
科全书政治学篇定稿,我告诉他,所谓“执政党”,仅仅指参加内阁的党派,於是
,他修改了提法,至今中共仍然在引用他的提法:民主党派也是参政党。当然,这
一切,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以后都倒退了,比如重派共产党员入民主党派并控制领导
权等,这是后话。我要强调,综合政治经济状况,当时绝对不是中共走到极黑暗地
步,而是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开放、最开明的时期。不然89民运绝不可能形成
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势,天安门前的和平发展不会持续得那么久。
那么,胡耀邦去世唤起了什么?为什么要为了悼念他人们就立即上街游行呢?
人们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关于胡耀邦去世有很多传说,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解,怀
着不同的心情上街纪念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是打倒中共,而是对把他赶
下台提出抗议,要求的是继续改革开放。可能有人听信某个谣传,比如说他在书记
处会议上发言,激动受气致死,却也没有人因此要求打倒赵紫阳或邓小平。但是社
会运动震撼了共产党,以北京市委陈希同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并
且趁赵紫阳访问朝鲜之际炮制了4月26日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引起了广大
群众的不满。社论发表后,以费孝通为首,九位著名知识份子(有张宗厚、李慎之、
季羡林等)举行了集会,并且上书邓小平,要求中央‘理性温和地处理学生运动’,
五月一日邓小平即在这封信上批示,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贯彻执行“理性温和地处
理的方针” 。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著名的五月三日讲话,就是遵照邓小平这个批
示精神表的态,接着鲍彤在安排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会议上,又提出中国
要过民主关;胡启立和饱彤在全国文宣系统的安排都是党内改革派贯彻邓小平批示
精神,企图利用学生运动来推动改革开放。但是,当费孝通组织第二次扩大的高级
知识份子集会时,统战部长阎明复带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三位大秘书来
参加会议时,严家琪把他后来签署的《五·一六》声明上的话说了出来:“邓小平
是不是君主制的共和国的君主”,一听到他这样的发言和追随者的类似的激烈言论
,阎明复哭了,他泣不成声说:“完了,这下完了,邓小平不是这样的人!”一切
无法挽回了。这不啻是给刚有可能向学生倾斜一点的邓小平一个大巴掌把他扇到右
边去了。正在这时,学生又阻拦在天安门安排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报上发表了赵
紫阳对戈巴契夫的谈话,可能是右派误导,把他经邓小平批准的这个谈话解释成把
镇压学生的责任推诿给邓小平(中共十三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曾经由赵紫阳口头
提议一致通过决议:今后还要请邓小平把握重大决策。)广场上追随严家琪的五月
十六日声明,一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使运动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恰在这时,做为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赵紫阳访问了北京军区,这个行动引起杨
尚昆和邓小平的神经质,既不好问,又不便调查一位军委副主席的行动,只有疑虑
重重,於是邓小平通过杨尚昆迫使中央军委勉勉强强同意派军队到北京戒严,但是
,如何做这件事?既然连中央军委都勉强,北京军区又信不过,所以杨尚昆根据邓
小平的旨意,特意安 国各地24个集团军中的12个集团军各抽调一个或几个军、
师前往北京,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互相不摸底,从而互相牵制和监督,又可以
起到监督北京军区动向的作用,可见,邓小平已经不相信自己的任何一支部队对他
的绝对忠诚。另外一件事就是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明明白白的开枪的命令 。
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有关的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这件事后来在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江泽民发现自己失势时,当作一个救命符告到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的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另外,六四后中共
发动群众慰问军队,据军内高层人员告诉,几乎每支部队接见群众的第一句话都是
:我们没有开枪!可见,对一贯宣传军民鱼水情的解放军,开枪是非常不光彩的,
连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也不易指挥他们开枪镇压老百姓。
在在说明,没有什么发生镇压的必然性、开枪的必然性,或必然会流血的道理
。正如西方政治学从战后南美和南欧总结“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
LES TO DEMOCRACY" 的经验所显示的,凡是从威权制向民主制转化成功,总是仰
仗当权的改革派同社会上的温和派的联合,而所有转化的失败都显示,社会上的过
激派总是起着极坏的作用,即实际上向当权的保守派提供口实,让他们有借口动员
和说服军警,乃至使他们得以动用军警来血腥镇压。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邹谠教授
在开枪之前就亲口对我多次分析中国政治的极端化趋势,却一直保留说,“至今双
方都有打牌的余地,否则就不存在政治家和政党起作用的可能了。”他同时指出,
在中国,Winners take all and losers lose all,於是,实际容易引起一种升级机
制,而不是像民主制国家那样每当社会激烈动荡,总是出现妥协和进一步完善法制
的对立双方的互动过程,比如英国的所谓不成文宪法就是这样在几百年内通过对立
双方妥协积累起来的,而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因为发生广泛的社会运动而死人的
事了,包括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几乎没有死人。中国越是没有法制,越无
法按照法制约束官方和民间的行动,於是总是越来越激化,天安门上的学生领袖也
更换得一代比一代激进,口号也越喊越过头,领袖越来越脱离群众,越以激化矛盾
为能事,而像此柴玲这样的领导居然说,她就是蓄意要流血,只是不流她自己的血
,这样的人在领导运动,但是怎么可能领导“民主”运动呢?她只能为独裁者准备
祭牲,让群众做被宰杀的羔羊。
如果现在讨论89年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那么不会有任何当事人乐意说
“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承担“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不会有此悲惨下场”的责任。
现在只能借题发挥,在承认过激的举动应该避免的基础上转而讨论,如果再出现政
治危机或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必须怎样把牌打得漂亮一点?为此要具备怎样的条
件呢?那就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怎样提高呢?从自我总结经验做起,而这
又不可能要求以平反,以对方“你先改变态度……”为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只能是
也必须是涉足89民运的勇士们不要怕丢面子,请拿出当年不怕天地鬼神的气魄和公
心,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上升到懂得如何推动民主制实现,为此必须学习斗争艺术
的觉悟,并再次做出令人感佩的贡献;而我们广大的事后诸葛亮不要动摇我们对天
安门英雄的感激与钦佩,在讨论中免不了提到人名和事件,免不了褒贬,但绝不是
抱怨和讥讽,不许可抱怨和讥讽,只是恳求有关人士摆清事实,总结经验,目的不
是煮酒论英雄,而是教会中华儿女从只知道激进再激进变得学会更聪明,更有计策
,这不是倒退投降,而是一步步走向掌握实现民主制的艺术。我们无法恳求当权者
温和,只能以社会行动的合法与温和来迫使当局日益承认我们的合法性并用法制加
以固定。这就是在积累民主,就是在剥夺保守的反动派镇压的借口。
政治学相信人的作用,相信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作用的能动性,而不相信社会
发展的“必然性”和统治者的“本性论”。我们总结经验提高政治文化就是要使我
们全民族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或机会出现时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学会不祈求一步登天
,而要善於攀登,攀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使中国达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一
个个制高点。
二、海外民运提出“体制外”自外于中国政治
那么,合法斗争是不是幻想呢?吴稼祥尚未出国前,我曾在家里邀他用餐,饭
后我对他讲过合法斗争,他说,“没有合法地位谈何合法斗争?”我回答说,“正
是1905年俄罗斯革命失败后列宁提倡合法斗争,这就意味着利用黄色工会,意味着
来一点灰色,而决不是动辄建立红色团体和公开布尔什维克或者申请成立另外的目
的在於推翻沙皇的红色政党或团体。”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海外民运挤不进大陆的合法团体和进行合法斗争?与其说
中共的残酷镇压构成了非法处境,还不如说首先是因为六四后几乎所有民运组织和
民主斗士本人个个都自外于合法地位和合法斗争。我个人认为,六四后海外民运的
最大的错误还不是分裂和争权夺利,而是提出了一个“体制外”的概念,而这又是
由於一个流行的错误的共识:“中共这样的镇压学生的政权不可能长远控制中国,
而且六四不平反,中国一切都停摆了。只要把六四真相揭穿,中共将土崩瓦解。”
各方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回国掌权, 所以只想做一件事──争权,於是分裂,重组,
分裂,再重组,最后,以为有了“民运联席会议”就万事大吉,无奈这个联席会议
发布的公报和消息赢弱智极,不会得到一点国内或侨胞的民心支持,更妄谈为中国
争取到民主了。总之,在上述错误估计形势的前提下私欲熏心有时跃然纸上嘴上,
比如当时有位民运负责人对我讲:“X老,像你这样温和,我们回国掌权时会没有你
的份的!”而中共在报刊上一点他的姓名就喜出望外,以为这样就增加了他的知名
度!为了留一点面子还可以参加讨论,恕我不说出他的姓名。
三、中国形势
相对讲,中共在六四后的政策选择就比较聪明。1990年汪道涵在美国访问时对
我说,上海的经验说明只要认真清查(六四问题)的单位,就麻烦多,相反疏于清
查的单位工作就好做。整个中共也以抓群众路线,而不是穷追猛打到底作为六四后
的工作重点。很快,苏联垮台,邓小平立即指出,苏联是因为没有抓好经济改革和
经济发展垮台的,所以,中国没有按极左派批判戈巴契夫的分析,借此抽紧阶级斗
争的弦,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当然,倒退是有的
,政治体制改革偃旗息鼓,反而把党政军大权更加集中于一个人了,江泽民还谴责
过支援乡镇企业的党员,说他们丧失了党性,(不久他改变了态度,肯定了苏南和温
州模式。)同时,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允许把土地的使用期权当作商品,从而
使土地得以流通,也开始了证卷市场,尽管这种证卷市场严重地先天不足。又是邓
小平在1992年以南巡讲话形式制止了江泽民、李鹏政权在改革开放上倒退的倾向,
从而为中共十四大打破鸟笼,正式把市场经济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十四大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对所有制改革初步放松严格控制。於是,
中国经济在南巡讲话后又一次腾飞,而且在高速发展九个月后,开始宏观调控。这
时邓小平犹健在,朱镕基没有顾虑被扣上“保守”、“倒退”的帽子,中流砥柱,
挽救了中国经济,以致在1998年没有被卷入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金融危机为便於分析
经济形势,现在我们来讨论闻道先生在《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北京之春
》总108期)所阐述的系统观点。我感到,他指出了中共在体制改革上的止步不前是
切中要害的,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朱镕基这样一位务实的总理也搞了一点虚图空
名的把戏,那就是他保证三年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超过了任何人的能力
。他通过成立几个接收国有企业债权的债转股公司,仍然靠国家收购呆帐坏帐等债
务使那些企业摆脱呆账,这怎么能算得扭亏呢?当然,后来允许那些接收债务的公
司拍卖,可能使生产起死回生,也许是一个办法,但不是“扭亏为盈”。对闻道先
生所做的整个的对中国追求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的抨击我不敢苟同。我不去分析闻先
生的每个批评是不是站的住脚,因为任何选择都可以找到它的负面效应,我想强调
的是,我们更应该考虑,舍此而外,有没有其他更为稳妥的选择?并且想一想如果
不控制通货膨胀,不控制汇率,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农民就能得利吗?权力资本的
霸气就会被削弱吗?
说中共在搞凯因斯是对的,尽管它自己没有那么说。实际情况是,早在1995年
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就向中共中央打报告说明,宏观调控已经起了好作用
,目前必须注意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滞胀状态,而且有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而后
者比通货膨胀更有害,建议中央改采积极财政,放松银根,调动内需,刺激经济增
长。当时我还陪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拜访过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首
席经济学家,办事处的第二把手Keidel博士,对他说,“恐怕中国现在更需要的已
经不是货币主义而是召回凯因斯。”问题是中国不能等“凯因斯契约”完善了,自
由市场体制完备了再修改政策。一贯很理解中国国情的Keidel博士没有同意我们的
看法,朱镕基接到报告也不以为然,他很生气地说,“别再重复这种意见,打这种
报告了。”但是,形势比人强,经济开始有滑落的可能,因此,朱镕基从1998年起
,开始了积极财政,刺激内需,促进高速增长。应该说他把财政拨款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同几年前地方上搞“开发区”和楼堂馆所是很不同的,更加不能说,他这样做
是为了肥育中国的权力资本。如果不及时改弦更辙,中国失业下岗不知道要严重到
什么程度,那时候,极左派就可以大肆攻击朱镕基的宏观调控了。
闻先生所关心的体制改革看来主要是产权改革。这确实是个问题。一、至今中
国没有正式开放产权交易,只是没有禁止产权交易(主要是在上海发生)的实践;
二,中共害怕产权流失因嗌废食,同时它把老百姓的钱袋当作国家财产可以任意敛
财的源泉而不加保护。十五大决定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从前年开始
试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转持,就是出售给股民,但是拿出来的几只均是垃圾股,所
以,一宣布就股价大跌,甚至在一级市场上都没有人认购,我当时写文章批评财政
部的做法,立即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大报《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可是
不久前正式出台国有股转持,仍然是这个态度,就是显然目的仍在於转嫁亏损给股
民,让股民用钱去买债务,而不是股权,当然会遭到严重抗议和反弹,不得不中止
。可见这不是财政部的态度问题,而是从创始证卷交易以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不严
肃态度的继续。
原来,中国的企业要上市,不是按严格的标准审批,而是权利分配,即中央部
、委、团体(包括工、青年、妇女)或省(大区)、市都分得了上市额度,要求上
市的公司必须先领一个上市额度。於是,有了额度,一切都可以按需要包装造假,
“我有额度了,领导都决策了,为什么你不让我上市?”於是,毫不夸张地说,不
是有多少虚假资讯,而是倒过来,在中国你很难找到那一家或几千家中哪几家上市
公司公布的资讯是真实的。甚至有不少企业,多长时间已经发不出工资,仍然敢捏
造说,连续三年盈利;因为凭额度上市,所以,圈了钱进来后供给额度的机关不仅
通过职工原始股等形式坐享其成大发横财,这个给额度的机关还可以命令该企业用
圈来的钱去解救本系统或本地区它所指定的某几个其他国有企业,所以中共实际上
把上市视作税收以外的一种“取之于民”的渠道,而根本不尊重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更不把它当作个人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於是,老百姓只好把多余的钱存进
银行,使银行存款余额盒带张一起无止境地升高。显然,中共并不把公民个人财产
权当作“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一部分来代表之;国有化又回来了。我个人接触的有
限范围内就听说了一些私人财产被实际上国有化,多半是因为这些人利用国有企业
招牌发展民营经济,等资产增值后,不方便脱离,本人又把个人财产诸如汽车房产
登记或隐藏在国有企业资产名下,有人甚至个人没有大额银行存款,本来认为可以
一手遮天,反正一切都是他的,但突然地方政情有变使他措手不及,难以更改,政
府就以年龄为由,请他退休,规定一个远高于正常定额的退休金,就剥夺了他全部
资产。我还至少知道有两个省,省政府看中了某个很肥的私人企业,说它偷税欠税
几十亿,让老板除了交出产权只有坐牢可以选择。但是,中共不可能肆无忌惮,因
为如果大规模实行国有化,那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极端严重地遭到破坏性打击。
200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软着陆成功的总结报告,它指出,
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民营经济的领先发展,报告以雄辩的事实和资料
证明了正是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困难条件下岿然不动这一点才使中国经济持续上升,
度过了宏观调控后经济可能的萎缩,也避免了陷入类似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这些
岂不是说明了尽管有些倒行逆施,中国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阻挡地取得了极大成就,
目前除了垄断性行业,非国有经济早已驾驭过半江山,已经谈不上国有经济控制什
么国民经济命脉了。
关于所有制改革或私有化,俄罗斯是一步完成的,所谓shock therapy(震荡疗
法), 一步跳跃山沟,代价是经济连续近十年下滑,至今尚未恢
复元气,如果这种下滑发生在中国,由於中国的承受力更差,可能会赤地千里
饿殍遍野。俄罗斯从十月革命起就有传统,即不惜代价承受巨大破坏去达到政治目
的。而中国相反,从1949年后,土改、抗美援朝都要求保持经济增长,连文化大革
命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只要生产
受影响,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让步先保证经济增长,比如1986年反自由化,赵紫阳
一指出生产因为干扰受影响,连左王都不得不刹车。所以,这二十年改革,中国不
把国有经济毁掉,而是让它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国民生产,而且还要维持高增长,(
因为减去必然存在的虚构资料,中国的生产增长必须维持在6-7%以上才行,低于次
数了就会险象环生)至少是巧妙地废物利用吧!你说,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是有根据的,但是,说中国的高增长使用了“近乎掠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似乎
偏颇了。
闻先生在这么长的文章里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规模经济问题。在朱镕基任
总理前一年多,从西方留学回去的前经济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陈一咨
)王小强给江泽民写报告,他焦虑万分地呼吁,如果不抓紧,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
的大型企业将被西方兼并收购一空。他建议必须采取坚定的措施实现规模经济。江
泽民立即批示给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李鹏闻风而动,他召开多次国务院办公会议讨
论,结果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南京附近的四个大型化工企业巨人同山东的一家大
型化工企业合并组成托拉斯,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只见到国务院办公会议起劲嚷,
没见五大企业的积极反应,好像没有什么结果。等朱镕基担任总理后,他任命的恩
人─(小国务院)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在新官上任后第一次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就兴致
勃勃地宣布,他已经把全国石油化工企业划江而治分成南北两家,其规模不言而喻
都已经可以进入世界500强 。消息发布,中国经济界哗然,北京大学的著名经济学
家张维迎的一段话披露在《中国经济时报》上,他说,如果形成规模经济是如此简
单,那么把全中国的国有企业合并成一家,保证是世界第一。谁都清楚,盛华仁不
懂得,他的进入了500强的企业有多强的竞争能力和市场份额?所以,他没有到朱总
理换届就下台了。不过,他典型地反映出中共高层那种忧国忧民之心,并且动辄使
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来干违反经济规律的“好事”,而不能说他们做任何什么事
都是唯利是图,一切按权力资本的私欲实行分配和再分配,而不顾国计民生。(未完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