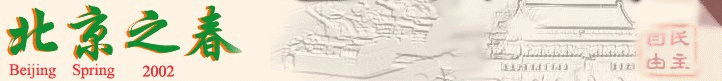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一个中国学者的观点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令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尤其自“六四”天安门事
件后,中国民主化的内在性质、历史经验和未来前景引发了海内外有识之士更深入
的思考。在这篇讲演中,我想和大家讨论这样几个问题:如何界定中国的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Westernization)?理解中国民主化进程如
此艰难的历史因素都有哪些?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回答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者
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以专制社会为对象的批判理论?
在这篇讲演的结尾,我还拟就与这个论题相关的、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所谓
“新左派”(New Left)和自由主义(Liberalist)之间的论争做一简要的评析。
一.如何界定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
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曾有一部份知识分子真诚地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
方化,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只有学习、采纳西方的立宪、议会及其他民主建
构,才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另一个极端表现为今天仍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在庆祝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再一次表示“
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
如果我们可以把前者视为囿于时代条件而对中国民主化得出的过于简单的
理解,那么后者则是出于统治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战略。
我个人倾向于不用“西方化”这个词来指称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其理由是
:
1. 在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水平上,民主化本来是
人类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具有社会进化意义上的普适性(Un
iversal Law)。西方国家(如英、法、美)不过是以各自经验的特殊性证明了人类
社会进化的普遍性。说得形像一点儿,西方国家并不能因为在历史上率先进行了民
主改制而享有“民主化”一词的专利。
2. 每个西方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西方化”并不是一
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以美国为例,这个由英裔美国人创造的、植根于新英格兰乡镇
自治传统的民主精神,以及在这个精神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世界”,其成长经历
显然与已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欧陆国家不同。难怪一百七十年前法国的年轻学者托
克维尔来美国考察时,对美国的民主制赞不绝口。当时,密歇根这块土地还没有纳
入美国的行政版图,如今这里已经是一派欣欣向荣。我想,“美国精神”中这种独
特的东西恐怕也非“西方化”一词所能概括。
3. 更重要的是,用“西方化”指称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有可能使人们忽略
中国民主化所遭遇的特殊语境和中国民主化必须面对的特殊挑战。无疑,中国民主
化是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份,也有“Universal”的一面,但它的特殊性(Par
ticularity o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一面,更值得重视,更值得研究。事
实上,正是这个“特殊性”或“独特性”的方面,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民主问题
的关键。
二.构成中国民主化特殊语境和困境的主要因素
首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制度现代化
史,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民主斗争与民主建构史,更多的是一部失败
而非成功的记录。为什么是这样?有两个因素似乎带有关键性。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悠久的文明与前现代遗产构成中国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巨
大文化障碍。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缺乏现代民主所需要的思想与
制度资源。在二零零零年中国历史中居支配地位的儒学基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
汉代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直至近世,它更多地发挥着维护君权统治与地方
宗法一体化( Integration )的功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
传统之堕性力量仍十分强大,条件适宜时,这种对于民主化而言的文化障碍很容易
转换为制度障碍。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之复辟帝制和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南
京国民政府的“党治”独裁都是证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对中国人来说,欧
洲现代化的先行者是以侵略者的形像出现于东方的,这个问题与哲学人类学水平上
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二律背反(antinomy )有关,我们不可能就此详细展开讨论;但
作为事实,它却迫使中国人做出文化保守主义与防御型现代化的选择,这显然不利
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改造。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拥有较长历史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面
临与中国类似的文化困境。使中国民主化问题更为凸显的也许是下面所述的第二个
因素,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立的政权本来以超越“资产阶级民
主”为目标,结果反倒走向自己的反面,兑变为中国专制制度的当代继承者。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的专制与反民主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遣
责,但人们往往因此而忽略了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曾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推进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一种
比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更先进的民主。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宣
告了毛泽东这种农业乌托邦神话的终结。 往下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的了:
一九七八年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但这个改革设定的目标却是有限的,
即推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坚持共产党对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的垄断。这种经济改
革与政治-社会改革的失衡是造成官场腐败现象蔓延的根本原因,它同时构成了一
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的“法轮功”现象之所以勃然兴起
的深层社会背景。
上述两个因素的并存与互动,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民主化的特有的问题情境
。
三.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回答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学界曾有数次译介西学的热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一九九五年以来,似乎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翻译
高潮,而且多以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为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
明中国知识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中国民主化问题的深层思考,并希望从西方
政治哲学理论中汲取有用的养料,或至少通过翻译,“借他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
话”。
我以为,西方政治、社会哲学传统中的确有很多思想资源可供中国人借鉴
,特别是欧洲反专制主义斗争中的优秀作品,其讨论的主题往往令中国知识分子感
到十分贴近,“似曾相识”。但总的来说,似乎没有哪一部西方作品能回答中国的
问题。道理很简单: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讨论的前提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
要解决的矛盾也不同。以颇受中国知识界尊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John Rowls 为例
,他的《正义论》(On Justice)早在八十年代就被译成了中文。近年,他的《政
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和《万民法》( The Law of People )也
被译介过来。然而,讨论问题基本是美国式的,或者说,他是以美国社会为原型作
为设问的出发点。Rowls 与德国哲学家Harbermas 之间的争论,与威权主义( Aut
horitarian )社会的学术兴奋点很少关联。
中国特有的问题情境正在呼唤自己的批判哲学与政治哲学,它应该是民主
化所内具的哲学人类学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独特经验与设问情境的统一。由于中国是
一个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交叉与互动( Interaction )提供
了足够丰富的背景资源与思想刺激,使得中国学人有可能也有条件去创设以专制社
会和威权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制度经济学、知识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等
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对专制社会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学问是做
不出来的。
四.关于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简要评论
应该讲,目前正处盛年的中国新一代知识者,已经开始向这个目标迈进。
由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控制的相对放松、一些学人开始在学术刊
物上大胆而又谨慎地发表不同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观点。由于这些学人理论倾向
的不同,被分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是坚持八
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批判专制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漠视,认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经
济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新左派”则更多地强调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被
纳入国际资本的运作范围,认为自由主义对“主体性”(Subjectivity )的抽象主
义论无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 Modernity )危机引发的负面结果,主张中国社
会中的“平等”问题更甚于“自由”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等等。
我以为,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他们思考问题的态度都是
严肃的。当然,如果让我对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作出判断,那么我会对“新左派
”持更多的批评立场,因为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并非单纯由讲
效率但“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所致。更重要的是,片面强调中国被纳入国际资本
运作这个因素(尽管这个因素确实存在),事实上□避了本土政治专制仍是中国社
会发展与制度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应该指出的是,有些持“新左派”主张的学者,长期滞留海外,对中国国
内的实际状况不无隔膜,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他们有言论自由,但其言
论是否切中国内问题的要害,就很难说了。身在国内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者
的最大难处则在于:他们并无真正的言论自由,所以他们阐述自己的主张就不可能
彻底。他们深知哪些话不能讲,文章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去发表。像我今天在CMU的讲
演,在中国国内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力量!有人把知识分
子拐弯抹角的抗争自嘲为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言自语”,这话很形像,因为无论自
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都还微弱得很。
上述可悲的事实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自由交往空间
和健全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民主化的独特性与
艰巨性。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敢于正面面对看似可怕而实际很虚弱的专制体制,又
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体察,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能够建立自己的批判话语系统,并以
此贡献于自己的民族,也贡献于国际学界。
谢谢各位。
二00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这是本文作者于二00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美国中密歇根大学所作的学术演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