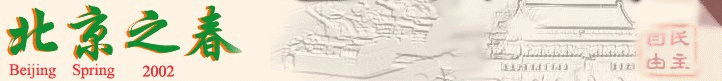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年一度的四月五日。由于1976年4月5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年年此时,公安部门的工作量便会大增,异议人士的自由度便会剧减。然而这样的监视与压迫也掩灭不了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们——中国人民的追忆与思索。今年此时,笔者就在监视的目光下挥笔驰思,浮想联翩。
那一年,十年浩劫,中共党内的极左派特别将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推到一个颠峰状态,也可以说是一个癫狂状态。冤狱遍地,受害人数几近全国家庭总数的七分之一。他们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柬共首领,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得人心,最暴虐的政权)就是得了他们的真传而犯下了世界最骇人听闻的罪行,最终政息人亡。
那一年的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上班的工厂突然召集了所有的党、团员和党团积极分子,每人发给了一套戏装,即所谓的8个样板戏内角色的服装。于是在灰蓝色的工厂里出现了一群描眉画眼,粉黛彩装的人,他们被车辆拉去填充能装几万人的首都体育馆,同声高唱样板戏,构成一幅盛世狂欢其实是帝国末日盛宴的怪异图景。我看到应召去的人们精神都挺不自然的,有点臊不搭的,是一群精神上的被强暴者。四月,人民心中淤积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周恩来的逝世使得没有任何渠道表达自己诉求的中国人民奔突而来。工人们来了,曙光电机厂的工人们抬着钢铁的大花圈;学生们来了,胸佩小白花;艺术家来了,擎着自己手绘制的周的巨幅画像;七机部的干部子弟们来了,身着一式的将校呢的旧军装,即标示自己的出身也显示自己的决心。(我不知道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可能有的人仕途得意,有的人腰缠万贯,有的人如王军涛历经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再度身陷囹圄,亡命海外)天安门成了花圈的海洋,诗歌的海洋、国际歌声此起彼伏:从来就没有什幺救世主,
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笔者那时也接连几天游泳在这波涛汹涌的海洋中,悲愤、激动、血脉贲张,更有着对未来的期冀,不,焦灼的渴望。
那天晚上,由于笔者要赶回工厂去上夜班,避开了那场大镇压,白天我在广场抄诗,贴诗,是个“反革命分子”。傍晚我到了工厂却和工友们被命令停工,领取棍棒,全体上车去“镇压反革命”,工友们都在传递着眼神,传递着心声:到那里也绝不对同胞们大打出手,而是要放行一条信道。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的车队驶过骚乱过后空寂下来的广场,驶进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命令在里面潜伏待命。手持棍棒的我们或蹲或坐在排演场内钢琴和通墙的大镜旁边,每个人的唇边都浮着一丝兴奋又略带讥讽的笑意:这决不是结束,这是一种新的开始。
记得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说过:把由于社会内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千百万人的动荡说成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少数阴谋家煽动的结果,是不顾社会内在要求的胡说。(大意如此)当时的当局就用马克思指斥的这种胡说诬蔑了这场运动(无独有偶,这种胡说我们在八九年又听到了一回),镇压了这场运动。而后来的当局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革命运动”以为就可以框定她的全部意义则同样接近于马克思指斥的那种胡说。他们没有听到或不愿意听到那天人民发出的呼喊吗: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要民主,不要佛朗哥!要自由,不要那拉氏!正鉴于此,当三年后,我和徐文立、刘青相聚在西单民主墙商议创办大陆建政后第一份民主刊物时,虽然想用《人民论坛》等刊名, 最后还是定名为《四五论坛》。因为历史是不容割裂的,因为历史前进的脚步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
于今,似乎时日渐远,血痕渐淡,当你的对手似乎已远去,似乎已消逝了的时候,你的呐喊还需要吗?冷漠与麻木,蛊惑与欺瞒可以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永远得逞。马克思那忧郁的眼神在警戒我们:当社会内在的要求……
当然这种社会内在的要求并不是都需要用极端的形式来解决,如果宪法有了司法权,如果报禁党禁解除了,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如果民主宪政得以建立,如果……
“四五”运动距今已二十六年了,再见了“四五”,再见“四五”
是为祭,抑或是呼唤。
杨靖 2002.4.5 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