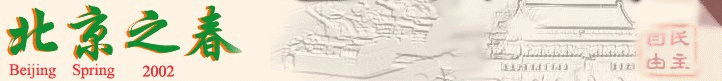一百天以前,我的老伴若望,在不情愿、不时感叹、 回天乏力中,走完了近八十四年的人生旅程。我呢,则在万般无奈,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中,目送着与我同甘共苦二十二年的夫君,在宁静的慈祥中,咽下最后 一口气。当时,我只感觉,握在我手掌中他的手,手指开始变冷,慢慢发硬,他的脸部,由鼻尖开始,一下子 发黄,我连忙俯首倾听他的呼吸:停止了。看上去是那样地毫无呻吟,那样地安详,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他是 与我永别。------我似醒非醒,如痴如呆,接受这一正在降临我头上最可怕的不幸事件。直到医护人员用白布覆盖到他脸部时,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才嚎啕大哭起来。 不久,在思念难耐,无所适从的胡思乱想中,突然想起关汉卿的《窦娥怨》中二句台词:“天啊,你错堪贤愚何为天;地哪,你不识好歹枉为地?”我的若望正 是普天下公认的贤达、善人,是我民族的好儿子,他一路走来是那么辛苦,那么安于清贫,理应长命百岁,然 后寿终正寝,方合情理;不就是肺部有点不适么?至于在短短的十六天内宣召他归天么?莫非,真的人生本无常, 生死本由天么?我必须认命,而且无人能抗拒么?
与夫君相爱三十三载,共度二十二个春秋,可以说,回首往事无遗憾。我们曾经是:涸辙之鲋,相煦以湿,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那是我俩长期生活在中共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中真实的写照,我极其珍惜并忆念 那段经历。真的,想当初,1968年,正是举世大疯狂的文化革命初期,老伴正是鲁迅笔下的“自嘲”所形容的: “运交华盖”的窘境之中,而我偏偏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毛泽东独裁者等人逼我们成为“涸辙之鲋”,从某 种意义说,我俩是“狭路”相爱,爱得那么旁若无人,爱得那么投入、毫无顾忌、那么真挚,好心的世人呢? 也确实为我捏一把冷
汗,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王某人大我二十岁,王某人有七个孩子,王某人是老牌右派,又 是现行反革命,在那个谈虎色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里,像王某这样的人物,别人见状,简直避 之唯恐不及,我何苦钻到猪苦胆中去独辟蹊径活受罪?应该说,同若望相爱,确实好辛苦,尤其是当他突然被 隔离,到后来的无期坐班房,我忽然变成爱上了一位反革命,那还了得?万般无奈中,我只好学当两面派,表 面继续保持独身主义者,把爱“反革命份子”之情深埋心底,白天随同事们一起跳忠字舞,晚上则偷偷写离愁 日记,当我默念陆游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时,凄凉之情油然而生, 随之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不过那个时候呀,虽然痛苦,但总算期待有望,坚信他必能回到我身边,哪怕五年、 十年------。在度日如年中,我想起一首歌:你可知道我爱谁?心上人是哪一位?比你温柔一千倍,比他可爱 一万倍,一点也不虚伪,受到了创伤不流泪,爱的路上不徘徊,像急流中的鱼儿永远不气馁,真叫人敬佩。我 就是怀着看似渺茫的期待,直到门前的桃花开过十次,终于,我们携手共度,从此,鱼水和谐。
后来,我们来到举世向往的美国。他,虽未给我荣华富贵,却给了我人生最珍贵的自由;也给了我不平凡 的生活经历;为了自由,他宁肯清贫,安于寂寞;无论横遭极权迫害,还是小人从中拨乱、诬陷,他都以笑面 对,表现了男子汉刚强气概。他憎恨那洒向人间尽是怨恨的极权统治者,为此,他,始终如一,身体力行,用笔 杆子,不计一切后果,为民呐喊,向极权者投枪,从不懈怠。他,实践了中国古来为人歌颂的“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的正气、风骨。来美的九年中,老伴无论尝尽何种苦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始终是忠厚、慈祥 的长者风度。
89年 "六.四”后,是老伴最后一次坐牢, 熬出狱后,面对岌岌可危的离休工资,感到惶恐,老伴曾对我 说:“任何情况下,我们不麻烦儿女,如果需要,我会拉着你的手去讨饭”。来美后,老伴日益老去,唉,岁 月无情,去年夏天,我忽然意识到,连我都老了,问题还在于,我必须笑着面对我肩上的担子,我对老伴说: “寿大(他的小名),你已属高龄,但我总希望你能超过九十大寿。人身上有五大系统组成,缺一不可,依我看, 你的呼吸系统是你最薄弱环节,我已注意到,今年以来,你感冒过两次,第一次仅服感冒片即愈,第二次却服用大量的抗生素方好转,现在即将夏去秋来,你要特别防止感冒,------从今年九月起,洛特丝的孩子全都上学, 我将减少工作时间,以争取在家多陪伴你。只要我们不追求住宅宽敞,我保证你每晚酒菜下肚乐呵呵。你知道 么?现在该轮到我来说,如果需要,应该由我拉着你的手去讨饭,这就是夫妻间公平责任。不过,在美国,我 们不必步行讨饭,所以,无论如何,我要保留一辆二手车,一来接送你继续关心祖国大业、声援国内受迫害者, 二来载你观光,再者必要时载你去寻饭吃,所以,即使你已经九十高龄,你也不必发愁”。之后,看上去老伴 总是心安理得、无忧无虑。
唉,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做梦也未料,老伴从住院到病故, 才十数天。我,横空痛失我相依为命的老伴,真正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我痛不欲生,几乎精神崩溃,醒来真 有点万念俱灰。这个时候,是相识、不相识的国际友人、我的同胞,向羊子伸出温暖的手,先是孝子孙博士给我 们免费送来了价值昂贵的华阳复方中草药;史女士则给京剧录像带为老伴送行;皮肤科专家崔医生,分文不收 为我切除了脸上的大皮疣;某电台的林小姐及骆女士接我去首都华盛顿小住,为我分忧;南卡的王小姐事先购 好机票,亲接我去她家,让我在优美的环境解闷、散心;还有多伦多的陈小姐,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的翁老师,澳大利亚的杨夫人,先后来电,热诚邀我前往他们处养精蓄锐;当我真正开始孤独日子时,有一位好友阿华,很 遗憾在若望生前未曾谋面,但她是那么敬重他,她赞美一首歌《海鸥》:“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 飞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愈高,看得愈远;它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阿华说:“我想象中的王老,就像海鸥那样,只是他直飞天国----理想之国了”;当我搬家前,由于衔接原因, 本不认识的“家和”地产经纪人愈权正夫妇,为我慷慨支付空房费$800美元。真的,一个人身后给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此生足矣,我为老伴自豪。在这一百天里,我由极度悲痛,逐渐恢复宁静,哭得少多了;至于平素的知心友人,对我之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我今生即使做牛做马也难报;倘有来世,容我再报。
我们的房东,获知老伴去世,送了奠仪,并参加了追悼会。不久,他们坚持要收回租房,我得尊重他们的意愿,想方设法租新居。问题来了,由于老伴现如今是以骨灰箱形式陪伴我,对美国人言,安放房中,他们根本无所谓,就好比市中心的墓园与居家毗邻一样寻常, 在我这方面呢?必须租华人房屋,而华人比较忌讳,怎么办?中共不让我名正言顺捧夫亡灵安放故土,又不宜 进入异国的华人之家,万不得已,突然想到,当年我买汽车正为了支持若望的理念,现在,当我发生居住困窘 时,可以说,这汽车是唯一属于若望的财产,万一不得已,我可能将骨灰箱安放于车内,每天跟我同来同往, 虽不安魂,但若望一定理解我的苦心,因为老伴是那么熟悉中共无孔不入的用心:中华民国老总统蒋中正的棺 木,尽管家属很想安放于浙江故土,中共也曾经放风表示欢迎,并修缮奉化老总统家居,但发觉中共别有用心 的政治需要,台湾方面多年来不予理睬,宁可至今悬放台湾土地,也不上他们的统战圈套;八九年“六四”惨 案,成百上千无辜死于北京屠城,十几年过去了,当局始终不敢面对自己的血腥行为,以致死者的亡灵至今不 得安宁,可怜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晚年丧子,其子骨灰至今仍安放于生前的小床而不曾入土。念及那些不幸的有名无名的亡灵,联想到我的若望骨灰,我得从长计议,只要我难于堂堂正正回归故土,在美国,只要我活着,看来老伴得跟我东西漂泊,也好,在我感觉,仿佛老伴永远在我身边。正在我无奈之际,前述一位王小姐发现 我住宿行将困难,立即贷款,当机立断,仅花二天工夫,为我在纽约购买了公寓,无条件解决了我的根本困难。 唯有此时,我突然意识到:羊子痛失老伴王若望,人间洒向羊子尽是爱。
世上不幸的未亡人何其多,而像我这样幸运的未亡人有几多?所以,尽管忆亡夫难免泪汪汪,而我的内心 知足,充满感恩、感激和感谢。是人们充分理解老伴生的价值,死的荣耀,人们洒爱于羊子,其实是人们认同 老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德;认同老伴从年幼追随毛共到背叛毛共而不再上当,所付出 的毕生艰辛中,显示出历来为人称道的棱棱风骨,临终时形成空前凝聚力,展现了老伴全方位的魅力所在,我 呢,则成了意外的受益者,这,岂不是老伴意外留给我一笔丰硕的人间爱的精神遗产么?诚然,面对老伴的遗 像,老伴所经之处,所触摸过的一品一物,我会情不自禁流泪,但这泪,已是伤心中略带苦涩的、满足的泪, 写到此处,我又想起一往事。 那就是,2001年感恩节前一天,也就是隔天他拉着我手,哭着要我不去上班,我含泪带着他去 上班的第二天,我考虑到老伴的病情性质未定,万一他患肺结核,再去孩子们家恐不合适, 因此,我表示我会很快回家,希望他在家等我下班,不料,他怎么也不愿单独留在家里,我实在心酸极了,又不能让他与孩子同在一屋,幸亏,又是这辆车,关键时刻,又救了我急,虽然已是初冬季节,我建议他坐在我车里,我可以常常从孩子家出来看望老伴一眼,顿时,他像个没病人似的,马上从沙发上一轱辘爬起来,很高兴地跟着我上车了,到了孩子家门口,老板洛特丝(Lotus)和朋友梁女士,去车旁问候他,他还想站起来 招呼她俩,她俩见他如此虚弱和消瘦,连忙使他安卧车内,洛特丝实在于心不忍,立即付了我全天工资,让我陪老伴回家了。这个场景,至今回忆,令我失声痛哭,痛哭之余,让我浮想联翩:“老伴呀,谁能想象: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人、有头有脸的中国异见作家、本该安居在家,儿孙绕膝,琴棋书画,习字吟诗,颐养天年,其乐融融。而如今,客居异乡,我得上班,而当你病魔缠身,我却尚不知情,你还装作健康,孤独在家受熬煎, 实在忍不住了,才哭喊我别上班,才甘愿屈躺车内跟随着我,此情此景,何等凄惨!”四个月来,痛哭之余, 又悟得,老伴这辈子,任何艰难困苦中,从来顶天立地不弯腰。
在与我共同生活的二十多年中,从不求人的老伴, 感恩节前,是唯一本能地依恋我的两天,心想,他也有依恋我的时候,我感到被依恋的自豪和满足,只是,我尚不明白老伴正在悄悄向我告别,我原准备让他一直依恋下去,让他依恋个够的。可现如今,他带着无奈、遗憾和惆怅离开了我;我这边却是无法弥补的亏欠,真是遗恨无穷哪!我还想说的是,再伟大,再坚强的人,总也有软弱的时候。在亲爱者面前,该示弱时,千万不要 刻意克制,否则,一旦永别,活着的会留下永远的痛,和心灵永难卸脱的沉重负担。
近日,我造访了尔品,因为他是老伴生前的忘年交, 老伴临终前,他每隔一天去看望,老伴曾对他说:早在 一年多前,老伴即感到健康大不如前了。听后我大吃一惊,当着尔品面,我止不住泪水直流,我一边回忆,一 年多来,我的感觉是,老伴一直健康良好,声音洪亮,唱京戏有板有眼,中气十足,走路像个中青年。要不是 张学良过世,我还不一定想到为老伴全身体检------。
直到十月中旬,在《黄花岗》创刊号上发言,虽然人消瘦,但还不像病人呀;再仔细想来,其实已有迹象,如, 前几年,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不仅要看到邓小平去世,还要争取活过老邓 (他没想过,他是什么医疗条件,而老邓是何等医疗条件,他是多么天真呀);后来,当我要他以张学良为榜样,做个长寿计划时,他只说先定二年, 我虽说他保守,却并未细究他为何保守,唉,怪我粗心,我没注意到他实际已在衰弱的躯体。在八月为他做体检时, 我还以为我想得挺超前呢,只是老伴显得不情愿跟我去医院体检,等到病入膏肓,我问他:“为何当初领你去体检时,你很不乐意呀”?他说:“要是查出来有病,我们治疗得起吗”?除了心酸、热泪,我还能有何表示? 还是印证了孩子们的话:爸爸从来天塌下来自己担。
我必须振作起来,向广大读者朋友表心愿:当今中国社会,半世纪来,在中共洗脑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斯文扫地,唯利是图,人心涣散,不讲公义。老伴正是公认的道德形象楷模,对我言,恰好化悲痛为力量,为亡夫做点事情。在祖国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我要为老伴建造一座纪念亭,中竖一块大“风骨碑”,碑文刻着老伴的生平, 供后人瞻仰。
借贵刊一角,求教读者诸君,王若望是羊子的丈夫, 更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让老伴的英魂回归,乃先夫生前遗愿,也是人民所期待。羊子愿与全体朋友共同努力,让老伴早日魂归故里。如今祈盼朋友献计献策,如何实施理想的树碑立传?
三十三年前相识,三十三年后永别,要是有人问我: "羊子,与王若望共度的日子里,你后悔”?我的回答是:“当年,在可怕的政治漩涡中,他的前妻拒绝了柯庆施等人的逼迫离婚;下辈子我倘若仍投女性,我还会选王若望作我的夫君”。 2002年3月29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