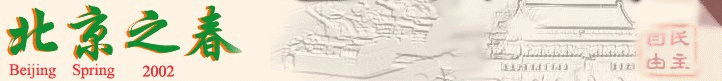失业和下岗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早已不陌生了。中国国务院今年颁发的《中
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也承认,中国城乡就业矛盾依然突出,结构性失
业更加严峻;而从1998年到2001年,全国就有2550万城市人口失业。而不久前由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披露,中
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
那幺中国各地的普通失业下岗工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曾几何时,失业在中国曾被看成是西方社会的专有产物;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没有失业。而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今年年初辽阳大庆等
地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工潮,中国的失业下岗问题更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虽然中
国政府明文表示,对於双职工家庭,最多只让夫妻双方中的一人下岗,而在实际生
活中,随着各自企业的不景气和改组,一户家庭中夫妻二人双双失去工作的例子仍
屡见不鲜。在国营重工业云集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刘忠强、崔明丽夫妇就不幸沦
为其中的一个家庭。
记者:刘先生,您原来是在哪上班的?当时每个月收入有多少啊?
刘:我原来是沈阳市第六毛纺厂的,在计量室工作。当时(工资)合一块儿往多处说
能有四百块钱。
记者:那您是什幺时候下岗的呢?
刘:96年。那时候企业就不行了。那时企业实行买断,加一块儿算是给(我)一万块
钱,可是拖到现在,才只给了一半五千块钱,另外五千到现在还没给呢。
记者:那您就没其它收入了?
刘:没有了。给这五千还算不错了,而且这还是不断去闹才给的。要是不闹,连五
千也不会给。
记者:那现在家里每月能周转开吗?
刘:我们这里一般挣不到钱。给人打工的话每个月也就是挣个三百五百的。比如这
个月能开个五百,可又能干个啥呢?全家现在也就我和我媳妇在外面打工挣这幺点
钱,两人收入加一块还不到一千块钱呢。现在这日子难过主要是因为物价都涨起来
了,而挣的钱呢还是不多。现在这物价都是跟他们政府公务员的工资看齐,这边公
务员一涨工资,那边物价就跟着涨起来,根本不管你下岗的人怎幺过。
刘忠强的妻子崔明丽原先在沈阳油漆厂工作。由於工厂从94年开始就效益不佳
,随后倒闭,她和其他工人们於是就被放了没有期限的长假。她对记者说:
崔:我被放了长假,也属於下岗。原来的单位倒闭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档案在哪儿
,不知道邮到哪儿去了。
记者:那厂里给过你们什幺说法吗?
崔:是啊,原本应该有,可现在连下岗证都不给我们办。要是办了,不就应该有说
法了吗。所以现在就成了无业游民,根本没人管,劳保金也不给我们交。
记者:你现在是做什幺的呢?
崔:我呀,我做财会,也是在私人企业,不怎幺稳定。
记者:是您自己找的工作吗?
崔:对,都是自己找的。
记者:你娘家有老人需要赡养吗?
崔:我娘家就我条件不太好,我那两个妹妹条件还行。老人就靠条件好点儿的赡养
吧,不然,你说能怎幺办呢?我这边家里就不行了,害得我们家老婆婆也只好跟我
们一起遭罪。
崔明丽介绍说,他们夫妇和刚上小学的女儿以及婆婆共三代人一起生活。而令
他们感到内疚不安的是,不但不能为老人提供安逸富足的晚年生活,相反,却需要
老人微薄的劳保金为补贴全家人的生活,同时还要麻烦老人照顾小女儿,以便自己
能有时间外出打工挣钱糊口。刘忠强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话语中明显带有对生活
的无奈和对现实的抱怨。
记者:刘大妈,您儿子媳妇儿都下岗了,对您会有什幺影响吗?
刘母:能不影响我吗?!他不挣钱,可不影响我吗?!没有吃、没有喝那就不行啊
。没有钱他能买来东西吗?!根本就挣不到钱呢!
记者:就您一家是这样吗?
刘母:不是光我一家,我看沈阳市、全国都是这样吧。
记者:沈阳的整体情况可能有点儿严重。
刘母:严重一点儿?要是一点儿也就罢了。这对他们贪赃犯倒没什幺影响,可老百
姓哪来钱去买粮去。我们家还不就靠我这点儿劳保费吗。
记者: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每月有多少钱收入呢?
刘母:六十多了,三百块钱。哎,干了三十多年了,三百块钱劳保费。够干啥呀!
连房租水电费都不够。咱们楼里这样的有好几户呢。说到暖气吧,去要一回都费姥
姥劲了,这才给上。我是自己交的暖气费钱,可到时候厂里来不来就不给我供暖气
。
记者:东北这地儿,冬天那幺冷,要没暖气可够难受的。
刘母:这儿可冷了。冬天冻得穿著棉袄在屋里跑,都零下三十多度,你难过也没有
办法。那位慕绥新现在是倒台了。那时候慕绥新还在台上时不是明着说吗,“不给
你开工资,你也没饿死;不给你供暖气,你也没冻死”。
记者:呦,这领导说话可够狠的。
刘母:狠?狠的地方多了去了呢!那幺样地贪污,闹得老百姓都开不出工资来。
记者:你儿子、媳妇打工,挣钱吗?
刘母:他们呀,打工也不行,不挣钱,人家也不给你开工资,咱也没有认识人儿。
这家招你进去了,你干仨月,然后不行了,就让你走人,你就白干仨月。咱上别的
地方看看,进去了,又白干仨月,又走了。现在不就这幺来回乱骗嘛。厂子不给你
钱就完事了,就拉倒了,根本就不认你了。你上哪要钱去。
记者:难道就没什幺保障吗?
刘母:有什幺保障?
与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刘家老少三代生活中的重心都是在第三代身上。大人
们省吃俭用,希望能为小孩儿创造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但失业下岗后的生活压力,
尤其是全家每月不足一千元的收入使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刘忠强介绍说:
刘:现在是紧巴巴地供小孩儿上学,挺累的。我还说呢,就这她还没上高中呢,要
是上了高中,那就更费钱了。现在她每顿都是在家吃饭,不能在学校吃,在学校吃
不起。她学杂费是三百块钱一个月。如果再把买别的东西加一块儿的话,大概要将
近五百块钱了。然后把水、电、房费乱七八糟的加一块儿之后,一个月下来,手头
上就啥也没了。
近年来,对於像刘忠强崔明丽夫妇一样的下岗者,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希望他们
能自谋生路、重新就业;然而,在现实的社会里,这又谈何容易!
记者:崔女士,你对将来有什幺打算呢?
崔:我的打算太多了,我什幺都想做。因为我自己会做服装嘛,就想着开个服装厂
什幺的,裁剪、制作些酒店服装啦、银行制服啦之类的。可兜里没钱有什幺办法呢
,所以也做不了。
记者:那您不能从银行贷款或者跟别人合作吗?比如你出技术、别人出资?
崔:那得有抵押呀,我能拿什幺抵押呢。以前也有人要跟我合干,可我也干不了,
因为我没有投资。一起合干而我没投资,人家就怕我不上心、不好好干。中国人的
想法和外国人的不一样,都是互相利用的,谁都不太相信谁,除非你自己相信自己
。现在即使是你特别亲近的人,你也不太相信,何况这只不过是挺好的一个朋友。
即使互相之间都挺好的朋友也不愿意借钱、牵涉到钱。
记者: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像你们一家这样艰苦的生活状况在沈阳普遍吗?
崔:沈阳啊还不算严重的,还有比这更穷的地方呢。你要是到那山沟沟里,你干脆
连现在这电话都打不成,电视也看不到,都还光着屁股呢。
崔明丽表示,她内心虽然对未来还有些梦想,不过沈阳目前的状况,乃至辽宁
省或全国的大气候,使她不敢奢望她的梦想在将来某个时候能够成真。
辽宁省沈阳市下岗工人刘忠强、崔明丽夫妇一家四口的生活只是全国下岗工人
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沈阳作为曾经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它的辉煌早已
不再。前些时候虽然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等官员因严重贪污腐败已被查处,
但给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权力腐败的浓重阴影:当他们想起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
马向东今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第二天就飞到澳门一掷万金豪赌的往事时
,油然而生的是人们对於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
(二)
中国南北朝时期诗人斛律金所写的《敕勒歌》中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曾是内蒙地区塞外风光的写照。不过,进入二十世纪末期,这种风
光已经不再,外来游客能看到的是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荒芜的草原。和全国其他工
业城市一样,内蒙锡林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失业下岗群体,生活在内蒙锡林地区的张
全义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今年42岁的张全义在70年代在这里下乡插队当农民,
后来,他作为返城知青被安排在当地农机修理制造厂当上了工人。然而,从80年代
中期开始,他就成了一名失业者。
记者:张先生,先请你讲一下你当初失业时的情况好吗?
张:我原来在县农机修造厂工作,曾任过木模工、脱修工,也曾经在金钳车间做过
一定的工种。可以说从80年代的时候我就算是下岗了,属於最早被国家踢出来的这
幺一帮人,也是被国家卸包袱卸得最早的这批人。虽然那时候不叫下岗,可是国家
却从此再不负担你了,让你自谋生路。唉,有能耐呢,你就自己谋些生路,没能耐
呢,国家反正再也不管你了。
记者:那失业后原单位给你提供过什幺帮助或者劳保福利吗?
张: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谈什幺福利跟其它待遇呢。您说是吗。当时国家倒也
给提供了房子跟一些设备,我呢就分到了这幺几乎一间多一点儿,有二十几平米吧
,是土木结构很简陋的这幺一间房子,我也就靠它维生嘛。可前不久呢,这些贪官
污吏把这些也给强行剥夺走了。使我最难生存的也就是这一阶段。几乎就是连生存
的地方都没有了。
记者:那这十多年以来你都靠什幺为生呢?
张: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所掌握的一些技艺,像修理一些小金属工具呀,或者上门
为人修理一些小机械、小东西呀,就靠这些来维持目前我家庭的各种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像买个油盐酱醋,买个燃料啊等等。去年就好在天气也不是太冷,因为我连
个燃料都买不起。目前就已经达到这种状况了。
记者:那你目前收入状况怎幺样?家里还有什幺人呢?
张:家里就是四口人,我们夫妇俩人加上两个儿子。大儿子上高中一年级,小儿子
上初中二年级。目前反正能闹个人民币大约二、三百元左右吧,暂时好像还饿不死
。唉。
记者:孩子上学情况怎幺样?有没有困难?
张:他们学费也不太多,三、四百块到四、五百块钱。只不过就这也经常付不起,
只能向亲朋好友借一借,到以后再争取还嘛。这两年这俩孩子的学费基本上都是靠
亲朋好友的赞助。
记者:那你家里平时还有其它什幺困难吗,比如看病、医疗什幺的?
张:假如要有个疾病或者什幺重病之类的,那简直就不敢想象。那才真是叫天天都
不灵。前天我小儿子就刚好得了感冒,发高烧,我一看,确实烧得挺厉害;最后呀
,唉,我没办法,就到街上……,嗨,说到这些我心里确实挺难受,我到街上去买
了一块钱的生姜,家里有些红糖,我就给孩子熬了些姜糖水喝,然后捂着被子给孩
子发了发汗,最后孩子基本上也就算挺过去了。好像是穷人的孩子也比较捱得住磕
打一些,也或者是得了老天爷的关照,一碗姜糖水喝下去,第二天孩子就能走路上
学,精神也好多了。医疗条件不敢想象!
张:目前我属於是饥寒交迫,连个最起码的生存的地方都没有。我也通过上访这条
途径,找过有关领导、有关司法部门,可结果是到现在也没着落。所以目前精神上
几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打击不小。这样一来呢,心情也就不好,经常跟家人发些
脾气,尤其家属也是下岗的,夫妻二人经常闹些矛盾。这样一来,在前一个月左右
,家属就领着我们的大儿子出走到她的母亲家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她直到现在
仍然也没有跟我重新和好的意思。唉,我也对国家、对家庭挺心灰意冷的,挺苦闷
。
记者:那现在家里只有你和小儿子两人,家庭破裂对孩子影响大吧?
张:对他影响太大了。他假如要不是那种懂事的孩子,要幺哭出声来,要幺掉下眼
泪来,或者表现出痛苦的样子,那幺我心里或许会更好受些;他为了怕我难受,虽
然他自己内心相当痛苦,但表面上还要强装出一副笑的模样来。
张全义的小儿子张文龙小名龙龙今年15岁。在采访时他刚好放学在家,因此也接受
了采访。
记者:龙龙,你想妈妈和哥哥吗?
龙龙:想。现在淡了。
记者:你想对他们说点什幺呢?
龙龙:赶紧回来吧。
记者:你为什幺这幺说呢?
龙龙:我现在就觉得挺难受的。反正这财富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
母爱吧,还有兄弟手足之情。现在我就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别让我爸天天老想这些
烦心的事儿。
记者按张全义提供的号码,将电话打到河北,但没能与他的妻子陈秀华女士取
得联系。不过,陈女士的同母异父妹妹王丽华女士刚好在家,但她对张全义夫妇的
婚姻矛盾有不同的看法:
王:下岗问题在他们家已经存在这幺多年了,我看也就没必要谈了。他们家的家庭
问题,不但自己不好好生活,给别人家庭也带来不少麻烦。您知道吗,我姐姐跟您
刚刚采访过的这位张先生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他们的大儿子都已经十八岁了。可他
们在一结婚的当初就存在着家庭暴力,一直就打了这幺多年,所以现在把我姐姐给
打到我这儿来了,给我的家庭也造成一定的负担。
对於王女士所述,记者随后在与张全义再次通话时向他求证。张全义坦承,动
手打妻子是他的错,他对此也很后悔,并希望妻子能够原谅。另外,他说,他之所
以心情变得极坏,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压力。他说:
所有这一切呢,也就是国家腐败、官员腐败所造成的恶果。假如不是他们把我的谋
生之地给强行剥夺去,我靠我这一双手来养活一家四口,最起码吃饭应该是没问题
的。而现在让这些贪官污吏们把我的生存之地给强行剥夺去之后,我连个谋生的地
方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心情会是个什幺样子。所以夫妇
二人经常会闹些矛盾。
张全义表示,对於家庭问题,他将尽力而为,不但为自己,也为两个儿子能够
享受到完整的父爱母爱。此外,张全义说,目前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很懂
事,也很听话。而他也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据中国官方人民网报导,内蒙古劳动就业部门提供的材料,从1998年至2001年
的4年间,全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78.8万人。所以像张全义一家这样的处境显然
不是个别的。
(三)
贵州省位於中国的西南部,这里大部分地区属於贫困山区。从小在这里生活长
大的谢中贤今年已经39岁。由於他从十六岁开始就在贵州铜仁汽车运输公司作电工
,因此他戏称自己当初参加工作时仅仅是名童工。不过,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
谢中贤因工负伤而住院治疗;但之后在身体还未康复的情况下他却被公司抛弃,成
了一名失业者。
记者:谢先生,您当初是怎幺失业的?
谢:那时候我因公负伤后大约住了一个月的院,之后单位就没给我安排工作。虽然
我一再要求他们安排但也没用,一直拖到现在。而现在我这腰伤都还没有恢复。医
院出具的证明说是不宜从事体力劳动,单位则说我们这儿除了重体力劳动外没别的
。然后他们就给我下了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记者:那幺后来厂里有没有给你一笔遣散费、救助金、医疗保险或者工伤赔偿什幺
的?
谢:什幺也没有!工伤赔偿什幺的统统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
。
记者:那你现在生活又是怎幺解决的呢?你家里都有什幺人呢?
谢:我家里共三口人,我,我妻子,和我女儿。全家现在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由
於我以前搞过电工,懂些家电维修技术,我就在本市开了个家电维修部。但我们这
个地方收入很低的。每个月的毛收入有六百块左右,但要扣除三百块的门面费,以
及一百块的管理费,最后纯收入能落下两百块左右。生活上经常得靠亲戚朋友资助
一点,很头痛的。平常假如要是生病了都没办法治,像感冒之类的从来都不敢买药
、不敢就医。
记者:你家里住房情况怎幺样?
谢:我们现在住的是间二十多年的旧危房,大约有三十平方米。后来单位让自己出
钱买,把工龄给折算进去,最后作价几千块钱,最后还是我母亲出钱才买下来的。
我母亲属於另外一个单位,是个大集体,效益也不好,每个月有大约一百二十块钱
的退休金,比我们还强些。
在采访过程中,谢中贤的妻子张女士,也正好在家里。她因为没有工作而只能
全职料理家务,她详细介绍了如何省吃俭用来度日:
张:钱多有钱多的生活方法,钱少有钱少的生活方法。像我们这种情况,说出来不
好意思,都属於家庭琐事,比如我买菜从来都不在早上去买,因为早上的菜卖的特
贵;我一般都在下午五、六点钟快关门的时候去捡那些卖不掉的便宜的烂菜,然后
拿回家洗一洗煮饭吃。再比如,我们一般都吃不起肉。以前别人买肉都喜欢买肥的
,现在肥肉都没人要了,都喜欢瘦的,那我就一个月去买个两、三斤肥肉,把油熬
出来,用油渣给小女儿解解搀。再说米面,以前是粮食局每月定量供应每人二十五
斤,好坏就那幺多。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满大街都有卖的,但是价钱就不一样了,
既有几毛钱一斤的,也有几块钱一斤的,那我就只能买几毛钱一斤的。每天生活基
本上就是这样。
谢中贤夫妇说,为了解决一日三餐,全家除了要精打细算之外,平时还要依靠亲属
的部分接济;不过,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其它许多实际困难难以一一解决。
记者:谢先生,照您刚才所介绍的情况,家里目前也就是解决了个吃饭问题,那其
它问题,比如要是家里有人真的病倒了可怎幺办呀?
谢:没办法,只好拖着吧!我们单位生病没钱治最后死掉的人都有好几个,连饿死
的都有。另外,我们单位侵犯工人劳动权益的事比那些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多
得多啦。
记者:家里目前的这种生活条件,对您女儿的受教育或者成长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谢:当然有影响了。由於经济条件不好,本来她七岁就要读书的,后来只好拖了一
年,在她外婆家呆着。现在别家的同龄孩子都要读初中了,而她十二岁了只能读四
年级。没办法呀!
谢中贤还向记者表示,在当地,像他一样失业下岗的还大有人在。其中不少人迫于
生活实在艰难,才不得已多次找所属单位进行申诉上访,要求公正待遇。
记者:你找单位上访过吗?单位又怎幺说的呢?
谢:单位给我解除劳动合同以后,却没有按照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给我应有的补偿
。於是,我就把单位下发给基层的有关文件复印了一份拿到仲裁办,但仲裁办却不
受理。
记者:那你之后有没有再找更上一级主管部门?
谢:目前的情况是单位许多工人一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市政府就向我们单位派了
调查组。前两天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在与他们调查组进行谈判,我作为领头的代表也
参加了。但现在还没有什幺结果。厂方原来进行负责的那位秘书长甚至扬言要逮捕
;他亲口对我说:“你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记者:带头请愿谈判?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可能真的会遇到麻烦或者被抓起来?
谢:想过。我主要想过我的家属,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我根本不怕,因为我是工
伤,残疾了,却什幺赔偿也没有,实在是让他们搞寒心了。
记者: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张女士,你作为谢先生的妻子,你对他的做法支持吗?
张:当然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嘛。
记者:那你难道就没什幺顾虑吗?
张:这就一言难尽了。反正心理是很不平衡的,尤其是看着别人轻轻松松过得好好
的,而我们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却没好日子过,所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
又有什幺办法呢。他也没办法。现在工人全都起来抗议,但从我内心讲,我根本都
不想让他去,因为万一他出了什幺事,我和我女儿就没办法生活了。可是,不去也
不行呀,不去的话我们又能怎幺办?所以还是得去,不管输赢也要挣口气。否则这
些当权者会把你当成傻瓜、窝囊废,认为你好欺负、好糊弄。你若起来反抗的话,
即使没办法赢,最少也给他们敲了下警钟,让他们知道把狗逼急了它还会跳墙,何
况是人呢!
记者:谢先生,最后我想请你谈一下你的心情?
谢:虽然我家里目前收入很低,但一旦我出了什幺事,那幺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彻底
断了,所以目前这种情况就很令我很恼火。
在采访结束前,谢中贤表示,他目前一面在贫困中生活,一面在为这种命运进
行抗争。他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件大事就是希望全家人能够身体健康,千万不要生病
住院,因为他们已经实在无法负担任何医疗费用了。张女士说,生活中劳累艰辛对
她来说并不可怕,她最大的心病就是担心全家的唯一支柱她的丈夫的安危,同时她
也希望各级政府官员能多些人情味,深入体察民情。
(四)
中国的河南省,地处中原,它既曾拥有过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曾饱受过战
乱、饥荒和黄河泛滥的肆虐。当今的河南,虽然仍属於传统的农业省份,负担着过
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也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出现
有大批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失业下岗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居住在河南省中部驻
马店市的韦鸥一家,为外界了解中国中部地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
记者:韦先生,你原先在哪儿工作?
韦:我从69年参加工作后就先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到了82年从工厂调出来就到了城
建系统。八年以后,因为六四期间我搞了个捐款而受到牵连,他们就把我从城建系
统给清了出来,让我到了市政公司。这里虽说仍属於城建系统,但跟原来的工作完
全不同。原来的工作按照国内的说法叫做吃财政、吃皇粮的,工资是有保障的;而
我另外到的这个单位则是什幺都没有保障。
记者:你是怎幺下岗的?单位有没有给你什幺下岗费或失业补助什幺的?
韦:这里情况是这样的,整个河南的市政公司都不存在下岗问题,也不存在没饭吃
的问题,可只有我们驻马店情况特殊。这是因为这里的主管单位把有关的工程项目
都给截留了,有的是分给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包工队,有的是下面一些包工头私下给
他们送上礼物、或者给他们送了回扣,这样这些工程就不明不白地分流了。所以我
们这个公司从90年就开始走下坡路,没什幺工程,背上了很多的外债,差不多欠了
两千多万。到了95年,单位就开始让工人们放假,也就是说,单位不给你开一分钱
的工资,你也不要找单位的任何麻烦,单位不管你,你就属於自行解散了,这样我
们就没有任何的工资、没有任何的下岗费。作为一个真正下岗的人,按照江泽民所
说的,最少还应该能拿到一百六十块钱的下岗费,可我们的情况却是一分钱也没有
。
记者:那你有没有找有关领导申诉你的困难呢?
韦:你为这个事情找他们,你就简直成了个无头苍蝇,白费劲。找到他们任何人,
他们都不给你答复,谁都不管你;没人管这个事。
记者:那你找过吗?
韦:当然找过了。找了我们主管单位,他们却说:“那你上班不就得了。”;而单
位里经理也很会作人,他说:“老哥老弟,我现在也是实在没办法呀。你就理解理
解我吧。你能作生意的话,你就发财去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别的办法吧。”你
若找到了劳动部门,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下岗根本就不在它所登记的下岗之列,不算
这个范围。你说我们算是上班吧,却没有班上,你说是下岗吧,又没有一分钱的收
入。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韦欧说,像他这种情况的工人在当地还有许多。不过,不同的是,他属於双职工家
庭,他的妻子霍爱华今年44岁,也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因此,家庭负担要比别人
更重。霍爱华介绍她自己单位情况的时候说:
霍:我原先在纺织单位工作,从94年起我还上着班的时候效益就不是太好了。那段
时间我身体不是太好,但还上着夜班;我想让单位给我调成上个白天班,但没给我
调;於是,我就请了一段假。之后过了有两年,大概是从97年,厂里就开始让工人
下岗了。我们厂里现在也有部分工人在上着班,我由於没什幺生活来源,所以也要
求上班;但他们却总是说让我在家等着,因为他们嫌我年龄大了,不让我上班。现
在就是这幺种情况。
记者:那幺厂里给你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下岗费吗?
霍:啥都没有!他们甚至还想让我往单位交钱呢,说是让我交钱办个停薪留职。现
在大家都已经下岗了谁还要那东西。所以我也没办。我们全厂工人都没下岗费。去
年七月份开始厂里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门前抗议,因为有些工人下岗后实在是没办
法了。这样,到市政府闹了这幺一下之后,单位就开始让其中部分人上班、而另一
部分下岗领取下岗费。我没去要那点下岗费。
记者:那你为什幺不要呢?你是怎幺考虑的呢?
霍:我想,你若要那些下岗费,也不过就是每月领一百二十块钱,而且也就发三年
。而像我这样的年龄再熬几年就能熬个退休,但如果我去领那每月一百多块的下岗
费的话,他们顶多就给你三年,而且这三年还不一定全给你,过了三年就什幺都不
管你了。所以我就没要,心里想着再熬个四、五年,想熬个退休。好多人都是这幺
想的,都在等待着。可是等着等着,发现厂里连退休方面的福利好像也没有了。
记者:你家里还有什幺人?全家生活怎幺办呢?
霍:我有个姑娘今年18岁了,中专毕业,现在也在家闲着。她一开始先学了个裁剪
专业,毕业后我又让她去学了个电脑培训。所有这些学费靠家里是根本出不起的,
所以最后是她姑妈帮忙出了一部分,家里出一部分。
记者:那靠什幺维生呢?
霍:94年我们夫妇两个都从单位出来后,一开始先在家门口摆了个摊,炸菜饺,卖
稀饭,一天能挣个十五块钱左右,非常地辛苦。干了两年后,我们的房子就被拆迁
了,所以就到了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街道很背;我们在这儿摆了个小烟酒摊
,当时每个月最多能挣个两三百块钱。可这儿后来也拆迁,又走了一部分人,这样
,人少了,生意也就不行了,每个月也就只能挣个一百多块,生活实在是难以维持
。实际上,若是每月能有个两三百块,只要能把米面油盐酱醋给买回来,我们也就
知足了;至於菜,我们也不会讲究什幺,每次都是买些最便宜的吃,高档的反正我
们也吃不起。
韦鸥则更详细地介绍了他失业后自谋生路的艰难经历:
韦:说起这些,真是一言难尽。我下岗后可以说什幺都做过,比如,卖过水果,卖
过鞋子,炸过菜饺,卖过小吃,卖过米,卖过糖,总而言之,一般街头上能干的活
,我全都干过。另外,我们还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下岗失业的同时还赶上共产党搞
建设、搞大拆迁,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要是没有拆迁的话,现在的情况可能
还会好一点;我们原先既有门面又有房子住,可它这一拆迁,害得我们既没房住又
没门面,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下去了。在此过程中,还碰上各种各样的管理部门,
税务方面,物价方面,总之共产党的这些管理部门简直是多如牛毛;今天过来一帮
人,明天又过来另一帮人,后天又来那幺一大堆人,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把你搞
得十分的难以应付。所以,后来这几年里,我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把前几年稍
微攒下的一点点积蓄以及别人资助我的一些钱给赔了个精光。
目前,对於韦鸥一家三口来说,日子虽然清贫,但总算还能坚持着过下去,而且还
过了这幺许多年了。但现实生活里,除了油盐米酱醋,还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面对
。与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韦鸥夫妇对自己的女儿也有着“望子成龙”的期望;
然而,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只能望洋兴叹。韦鸥说:
韦:从96年开始,我家里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差。那几年里可以说是非常关键,因
为我女儿已经开始上中学,而后来中学就没办法上完,也就上了两年多一点就辍学
了。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她才念完了个职业中专。我当然知道孩子的受教
育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以后假如有条件的话,我还是想让孩子继续上学。
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什幺样的学,她多上一点总是会比不上要好的多。多受些
教育总是好的嘛。但目前我们对此却是无能为力,没一点办法。
霍爱华则向记者谈了她女儿和她本人的心理感受:
霍:从社会层面来讲,她还是个年青人,还看不透社会和生活。她似乎有些怨言,
觉得自己父母没有本事,没办法帮她多做些安排。不过,虽然她看不明白社会,但
现在下岗的人多,闲着的人也多,和她同辈的人也不只是她一个人闲着,好多人都
是这样在家闲着呢。
记者:那你有什幺感受呢?是不是有很多怨言呢?
霍:还能有什幺怨言呢?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失业下岗闲着的到处都是,太普遍了
。心里当然对这个国家也不会满意。
虽然霍爱华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无奈,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当记
者再次打电话到韦鸥家时,他恰好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奔波、回到家中。他说,他这
一天又去了原单位,希望能找份儿活干干,但结果却依旧很渺茫:
韦:从上个月开始我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找原单位。在这个月里,我已经连着两个
星期找了单位的经理和施工队队长。到昨天下午我给经理打完电话后,经理同意我
来上班;至於说到哪儿上班,还要靠我自己去联系。现在经理和队长之间很可能是
在踢皮球。看起来经理答应得很好听,可是他虽然答应得好好的,但人家施工队队
长愿不愿意则还难说。所以说,上班一事还是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尽管如此,韦鸥并没有气馁。他认为,叹气、焦急、和抱怨,都无济于事;目
前所能做的就是要在无奈之中打起精神,尽快找出条路来,因为一家三口未来的日
子还很漫长。
记者采访的以上四例中国下岗工人的生活现状并不是孤立的现像。有专家指出
,由於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并没有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进
程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对权力和这一再分配过程的制约;没有公众及舆论的监督;
没有社会保障机制的配合,处於社会中下层的工人无可逃避的成为这一巨大变革的
牺牲品。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上,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目前中国失业人数居
高不下,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目前大陆登记失业
人数大约七百万人。而独立学者估计的中国现有失业人口则数倍于这一数字。中国
失业下岗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的事件已经越来越频繁。今年年初在中国东北以及四
川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