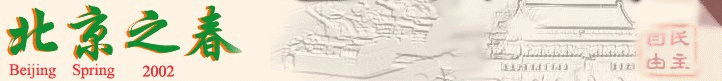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提及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他的态度令我惊
讶,因为他非常不屑的给了李四个字的评价:-出卖故主。
也就是指责李某的个人操守。这种指责尤其又从个人操守上升到政治操守。因
为李志绥与毛泽东不仅仅是故主长随的关系,而且还有一层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关系
,叫做“同志”。“同志”这个称谓从二十世纪初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切口,
演化为革命政权建立後对於“公民”身份的替代。显示出由孙文起始、而由毛泽东
推入极限的党治国家的的秘密特征。“公民”这个概念指向的是个体的主体性,“
同志”指向的则是将个体放入人际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一种“主体间性
”。在一个“同志”的国度,按照梅因的说法,每一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他自己
,而是被视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这种尚未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性转变的
群体主义文化,成为了现代党治国家的本土资源。
“同志”者,志同道合也。当革命团体的政治理想随着革命成功而僭越为全社
会的共同理想时,也就强迫性的将全体国民纳入了这个共同理想之下。同志的称呼
表明单个的国民不要说是公民,其实首先连“臣民”都不是。每一个国民首先的身
份是一个信奉者。他们不是以臣民的身份接受了君王的统治,而是以信奉者和追随
者的身份接受了一个教主的统治。
在同志之间,在追随者与教主之间,作为个人操守的“忠诚”就上升为政治上
的立场。一个革命团体或任何宗教团体,都是依靠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忠诚而获得统
治的稳定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背叛和任何来自於这个共
同理想之外的异端,都会对这种稳定性与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一个信仰者的
背叛,首先必定是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背叛。这就是一个党治国家为什么必然要以法
律诛心、必然要以思想获罪的原因。因为它所建立的首先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政权,而是一个由一切主动的和被迫的信奉者组成的皈依者团体。在一个四海之内
皆“同志”的国度,任何对那个一元的共同理想不敬的念头,都是对教主和所有革
命共同体成员的背叛。而“忠诚”就不再是儒家意义上的个人操守,也不可能是与
法定的职责相联系的现代“诚信”概念。而首先成为维系一个党治体制合法性的灵
魂深处的保险金。
大陆近来热播的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改编自作家周梅森的小说《中国制
造》,剧集名字就叫做《忠诚》。它讴歌和呼唤了党的官员对“革命事业”和对“
党和人民”的忠诚。这符合时下的“以德治国”的药方。它的主题歌在最高潮部分
声嘶力竭的高唱“一切是忠诚”。如上所述,在一个政教合一党治国家,所谓“忠
诚”首先不是言行上的,而是灵魂深处对於共同理想的思想忠诚。在一个腐败横行
、千疮百孔的多元化的时代,依然意图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的“忠诚”来应付合法
性的危机,反而显示出一个革命政权的脆弱。
如果我们以对忠诚的强调和对於背叛的容忍,来评价一个党治国家和一个民主
国家的生命力,我们会发现,任何政教合一的体制,都无法接受来自於体制内部的
任何“背叛”或来自体制外部的任何“挑战”。而任何一个民主政体,从来没有也
无需刻意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诚”。反而我们可以说,民主政体恰恰是一个充满
了“背叛”和“反对”的体制。
一种是来自体制内的“背叛”。如果我们将所有国民(同志)在意识形态上的
“忠诚”看作一个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那么事实上每一个老百姓关於“效忠”
的意思表示是永不可撤回的。假如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走上街头,对一个超越於
一切人的共同理想及其领导者表示了欢庆,你曾经敲起锣打起鼓,那么“忠诚”就
成为了你一生中的重负,你甚至还替你的子子孙孙在一份思想的“效忠书”上按下
了手印。任何在组织上、在思想深处对於那个共同目标的脱离,都会被视为“背叛
”,被视为不忠。这种背叛和不忠又会对党治体制构成渐渐积累起来的打击,和合
法性的荡然无存。
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每一个公民(不是同志)在政治上似乎都是朝三暮四的
,他们不对任何一个政党效忠,他们没有义务继续把选票投给曾经投给的那个候选
人。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家一旦被选民抛弃,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或指责支
持者的忠诚度。正如多恩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政治市场
”观点,民主政体下的政党在政治的市场上追逐选票的最大化,就类似於经济市场
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的企业家。而一家手机生产商是不会哀怨的指责那些喜新厌旧
的老客户的。
一旦将政治视为市场,忠诚与背叛这种将个人操守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就失去了
方向和说服力。萨利托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时指出,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
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对政治的驯服”。所谓世俗化,
就是“神的王国与凯撒的王国”的分离,即价值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而这一点
又是对政治的驯服的前提。刘军宁谈到米诺格的《政治学》一书时指出,现代政治
与古代政治的一个区分就是,在古代,“政治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古代政治中通
常都存在一个官方的、一元的和整体的政治理想。而在现代,政治被认为是第二性
的,是消极的。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於完美社会的抽象理想,而是现时的况
境”。
一个关於现时况境的,消极的和“市场化”的民主政体,也就是萨利托所谓的
被驯服了的政治。在世俗化的和被驯服的政治之下,政治领域内的“忠诚”,就仅
仅局限於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对於自身职责和对於法治秩序的法定责任。忠诚这个
词,不再指向思想,不再指向普通的公民。而退回了个人道德的范围和属於私法领
域的契约当中。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会看到1931年麦克唐纳“背叛”工党组建联合政府,
并成为首相。看到1995年泰国大选中Palang Dharma“背叛”民主党所领导的天使
派,进入差猜政府。看到1994年在台湾,新党从国民党中分裂而出,又看到几年後
,宋楚瑜“背叛”国民党自组亲民党参加总统选举的一幕。毫不夸张的说,民主政
体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朝秦暮楚的“背叛”与“分裂”,更离不开广大
选民“有奶便是娘”的反复无常。而民主政体的开放性或者说韧性,也就体现为对
於背叛的包容。他不怕背叛,不怕分裂,不怕“同志们”的反复无常。在民主政体
下,没有“忠臣”与“奸臣”的分别。
但这一切是党制国家无法想象的,足以让他惊恐万分甚至灰飞烟灭。尽管事实
上,任何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党,其内部都充满了分裂和派系,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
与保守派,按顾准的说法这已是党内两党制的雏形。但“搞分裂”一直是党治体制
下最严重的政治罪行。一个党治国家名义上的合法性,也就仅仅维系在对於内部派
系和冲突的极力弹压和苦心调和上。这种极力弹压和苦心调和的有效性,又往往取
决於一个威权主义领袖人物的铁腕。所以在当代日益多元化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
的威权化和政治上的集权倾向也就不可避免。因为领袖的威权一旦镇不住台面,内
部活跃的派系与路线之分就随时可能井喷而出。而这个政体的特性对於背叛又没有
基本的承受力,那么执政党四分五裂的解体危险就并非是危言耸听。
可以想象,如果在一个世俗化和被驯服的政治下,允许“背叛”的存在,林彪
也就不会仓皇出逃了。林彪当年如同宋楚瑜一般拉一帮子人出去,不就有了第二大
党,而不会被扣上分裂党、进而就是分裂国家的帽子。建国不久,高岗事件就已经
彰显出维系大一统政党的难度。应付这种难度的方法,还是只有拼命加强集权一途
。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毛泽东应付这种党内危机的最後一着。这样的回
顾不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面临的危机在今天的统治者面前依然存在,并由於社会
在其他方面不可阻挡的多元化和世俗化趋势及国际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的背景而显
得更加紧迫。今天的共产党一面加强威权体制,一面借助於“忠诚”的名义和道德
的名义,企图继续一个非世俗化的政治,这么做的危险实在是太过明显。
另一种则是来自於体制外的反对。与洛克和孟德斯鸠强调“以权力制衡权力”
有所不同,从托克维尔到当代的政治思想家达尔,则非常强调“以社会制衡权力”
。在政党以外,达尔非常看重非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中介性团体的重要性。
马基雅维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荒时期大开粮仓,接济穷人
。後来罗马人将这个富人判处了死刑。理由是那个富人在收买人心,罗马人认为他
有野心成为独揽大权的僭主。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专制政体对於任何“非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中介性团体”
的戒备之心。这个故事的现代版本,我们在中国对於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打击,
以及这之前开始的对於所谓“经济邪教”(语出李铁映)的传销组织的打击取缔中
,也可以看出一二。这两个组织最大的罪过是“怀璧其罪”。以一个典故说明:蜀
汉时刘备下令禁酒,把一切家中藏有酒器的人绳之以法。一个谋士陪同刘备外出时
,为劝阻这项政策,叫手下人把过路的一男一女抓起来,罪名是行淫。刘备问道:
“他们并没有行淫啊。”谋士说:“他们现在虽然没有行淫,但他们身上却有行淫
的工具。”
法轮功和传销组织之所以遽然上升为政治运动的矛头,也就如同此一男一女一
般,身上有着意图行淫的工具。即拥有上千万的成员和将之组织起来的巨大能力。
尽管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自由企业作为最重要的一种“非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中
介性团体”,其发展已经不可逆转。但各种非经济性的独立社会团体以及像法轮功
和传销组织这种可以投鞭填河的民间势力的存在,符合逻辑的成为一个党治国家的
眼中钉。因为一个独裁者只有在降伏和消灭了一切异己的独立力量(甚至不一定是
反对力量)之後,才会感到安全。一个一元化的,建立在所有社会成员的“忠诚”
之上的政权,无论是背叛还是挑战,都没有丝毫可以承受的经验和信心。尤其当法
轮功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地“背叛”了全社会的共同理想的情形下,对他的政治
打击是对於这个政权的非世俗性的再次强调,对於政教合一的特性的、最後的拼命
重申。
超越於党治国家的体制之上,如同萨利托所言,首要的前提是政权本身的世俗
化,一个是教主对於信徒的灵魂统治,它要求思想上的绝对忠诚。一个是宪政国家
对於公民的有效管理,他首先强调的是公民的个人生活和精神的独立,并以对於公
共权力的制衡来保证这种独立不被侵犯。这两个国度不能重合,不能掌握在一个非
世俗化的政党手上。在政治或说公共事务的领域,我们要求有背叛和分裂的权利,
有反复无常的自由选择的余地。
一种将背叛视为罪行的政治,就是专制的政治。一个民主政体下的公民,没有
义务做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主义的忠臣。□(2001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