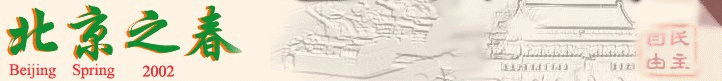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人民”二字为古今中外的各色政客所衷爱,也是各种政治理论中说不完
的话题。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民第一
,领袖第二,国家第三。在历史上,这种说法颇为国人称道,既受民欢迎,也受君
欢迎,皆大欢喜。民高兴是因为这种话听着耳顺,社会地位越不高的人越喜欢被称
为“贵”,就象越缺少智慧的人越喜欢听别人表扬聪明;君高兴则是属於偷着乐,
因为就凭一句话就把孰贵孰轻的大是大非颠倒过来,这等智慧好生了得。只是这么
句空话喊了两千多年,该贵的却从未贵过,该轻的也从未轻过,反倒是不该贵的越
来越贵,不该轻的越来越轻。
毛太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的国叫“人民共和国”,他的政府叫
“人民政府”,他的官员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服务”。不知不觉间,“人
民”成了随手贴的标签。一个人如果不是太倒霉,爹妈有幸不属於人民的敌人中的
某一类,那么他一生下来就属於人民群众,自此就与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校里
的教书匠叫人民教师,长大了挣的钱叫人民币,如果花不完可以存到人民银行,得
了病去人民医院,犯了法让人民警察捕获,人民警察玩不转了还有人民军队;如果
立了功,活着可以做人民代表,死了则成为人民英雄。因为君不再叫君了,时髦的
称呼叫“领袖”,所以不好再讲“民贵君轻”的老话,又不能改成“人民第一,领
袖第二”。索性把“君”去掉,改成“人民当家作主”,除了人民之外,其他都看
不到了,还谈什么孰贵孰轻,谁第一谁第二,人民就是绝对的第一。但“人民”并
不知道自己如何当家作主,也就不知道自己贵在哪里,第一在哪里。到头来,家反
倒让人家当了,主反倒让人家做了,头上顶着“暴民”的黑锅,却还洋洋自得。
邓二世改制,人民的招牌照挂,只不过他曾被“人民”几番打倒,尝过暴
民的蛮力,不免心有余悸。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其实最不相信中国人民。谁
会相信那群几年前还高叫着打倒自己,且永不让翻身的盲众呢?只要他们过上几天
象样的日子,就不会整天嚷嚷着要打倒谁了。只是二世跟头翻了不少,却到死也没
有跳出太祖的掌心。民无民权,依然如故。好在不管白猫黄猫,总算能捉住几只老
鼠;人民群众苦干加乱干,开始由饱暖阶段进入思淫欲阶段。一旦告别了革命,暴
民政治便再难成气候,乌合之众变成了一盘散沙。“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照喊,
只是照样有人当人民的家,做人民的主。等轮到江核心头上,则是不管聋猫瞎猫,
碰上死老鼠就是好猫。但位子可以传,头脑却传不了。邓二世一去,转眼间,白猫
黄毛都成了一群只知吃喝吹牛沾便宜的谗猫。眼看家也当不好了,主也做不稳了,
只好猫学犬吠,做张牙舞爪状,让“人民”看看到底是马王爷在当他们的家,做他
们的主。
当年孟轲讲“民贵君轻”,虽流於空谈,却不失为一种充满道德勇气的创
造;到了二十世纪後半叶还讲“人民当家作主”,则完全是重复一句大而无当的空
话,因为世上根本不存在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民”这样一个群体。只要有不同的群
体,就有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君不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领导”,就把农民阶
级打入十八层地狱,至今不得翻身。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既不可避免,近代西方人就
想出以权利为中介来做调节,以不至发生流血。而权利必须具体到个人,才有实质
意义,因为某种权利若不体现在个人,则完全空洞无物,徒有其名,实际上等於不
存在这种权利。况且,只有先清楚地界定个人权利,才能进一步界定个人与群体的
权利,以及群体间的权利。近人严复把穆勒的名著《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
,可谓抓住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实义。毛太祖当年所批判的那种自由主义与政治学中
的这种自由主义根本不搭界。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学的祖师爷,他曾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指的就是
那种既无民权又不争民权,甘心受主人支配的人。中国圣人的头脑中多的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无论如何反求诸己,还是生不出权利观念。两千年间,国人在这方面
没有多少长进。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我等至今仍不知民权为何物。而没有民权,民
就什么也算不上,只是一群供主人驱使的乌合之众,不是暴民,就是一盘散沙。何
谈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刺激-反应式的爱恨冲动而已。一百年以前,孙文闹
革命的时候,就知道民族、民权和民生不可分的道理,今天的“爱国”反美志士却
在这个问题上重又犯糊涂,是不求进步反求倒退,还是把倒退当成了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