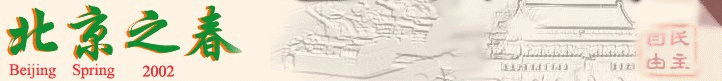尊敬的蒋亨兰会长、
尊敬的马悦然教授、
尊敬的各位前辈和各位朋友们﹕
首先,我要谢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谢谢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令人激动而又令我惭愧的荣誉。大约也正因为激动和惭愧在我的心里交相并作,难分难解,所以,一时之间,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幺才好。我想,我还是简单地说一说我个人的心路历程,说一说为什幺中国的一个普通文化人,中国的一个普通学者,居然就能在他年将半百的时候,还敢于自我流放到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个朋友的北美洲。而且,仅仅是为了写一本书而已。好在我于北美的一百多场讲演中,从来没有讲过我自己。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作一个老实的“交代”。
一九四七年深秋,我有幸生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却无幸长在中华民国。和我的许多同年人一样,此后便“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了。我不会忘记,在孩提时代,最叫我害怕和兴奋的事情,就是骑在哥哥的肩头上,追赶着那一辆又一辆押满“囚犯”的卡车,去看“解放军”枪毙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如果要说我们这几代人都是看着鲜血长大,便一点也不过份。
等我长成一个少年时,我的父亲不仅成了“右派”,而且也成了“反革命”。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深夜,在中共安徽省委对全省知识分子的统一大逮捕中,父亲从家里被抓走了。我至今仍然记得,母亲不敢在邻居面前流泪,害怕被人指斥为跟反动丈夫划不清界限,只能将眼泪偷偷地流在枕边。
此后,我小小年纪便遭遇了难熬的饿饭岁
月,看够了那一个个只要被人轻轻一推,就会倒毙在路旁的农民。更为饥饿的游民曾从我手里抢走了那一个黑馍馍,而伤心不已。
此后,我这个曾被老师在课堂上公开斥为“小右派和小反革命”的无辜少年,便在中共八
旗子弟和形形色色“根正苗红”同窗的轻蔑、歧
视和欺侮里,在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整人、害
辛灏年著作《谁是新中国》在美出版
人和杀人的政治运动中,心惊胆战地长大成人。
此后,当我亲眼看见红卫兵和造反派一边嘶叫着“红色恐怖万岁”,一边用他们的军用皮带抽打着一个个无辜的老人和孩子时,看着他们浑身迸流的鲜血,我内心深处的抗拒,虽然只能被越来越深地压迫下去,但是,它却为我对共产党和共产制度的彻底觉醒,积蓄了足够的感性和理性力量。
我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就是在共产党不得不开始推行专制改良来救社会主义命的时候,成了一个作家。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极其短
暂的所谓思想解放岁月里,我仍然感到了做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羞耻。特别是当我要将自身的真正觉醒熔化在我的作品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共专制文坛的重重打压。以至一个真正想说真话、想做真文学的作家,不但要学会甘守寂寞,更要学会眼看着铺陈在专制文坛上的种种名利和
官职,还有那一块可以引诱你归向“凤池”的红地毯,丝毫不动凡心。其时,只因我在民间尚负名声,中共便也要将我变成一个御用的“统战花瓶”,我却因目睹中共层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黑暗,还有中共层层体制内形形色色“知识精英”们与中共沆瀣一气的行径,直至与中共狼狈为奸的事实,我才更加明确地要求自己﹕绝不可以在这家马列王朝劣迹斑斑的店堂之上,与其中的任何角色同流合污,同气相求。于是我给自己写下的座右铭便是﹕“做一个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这句话就发表在一九八七年上海《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上面。
一九八三年,我自动放弃了赴北京参加中共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将名额让给了一个做过二十年右派的老作家。
一九八四年前后,我不仅数度拒绝了北京那几份足以令人羡慕的“调令”,而且明确地拒绝了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也要将我提升为中共处级干部的“恩宠”。因为我深知,那些宣称“要改造共产党才要做官”的知识分子们,其中的绝大多数,只会被共产党所改造。
一九八六年,我最后一次拒绝了安徽省文联党组敦促我参加共产党的好意,对一位关心我的老大姐──我们机关党委的书记说,“你们的整党是不可能有成效的,还是让我清清白白地过一辈子吧“。当时她脸上的苦笑,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八七年,我曾闭门五日,以公开拒绝参加安徽省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于他们要奖赏给我一个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诱惑,毫不动心。因为,我已经看够了中共作家们为争夺层层专制文坛权力而表演出来的一幕幕丑剧,我委实厌恶已极。
一九八八年,面对着一百多位要哄选我担任副省长的“人民代表”,我只好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我只是共产党的一个统战知识分子,请不要逼我做政治上的嫌疑犯。”不仅当场退出了会议,并从此拒绝参加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八九年,运动初起之时,我因对那场运动“心存别见”,特别是对那些正在天安门前长袖善舞的中共上层知识分子“心怀偏见”,所以,我才没有披挂着“作家某某某”的布条,游兴方酣。直到六月四日的黎明,我才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走上了街头,直至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为止。我甚至干脆借此机会,将一九八六年以来中共强迫我接受的一个个统战花瓶,诸“全国青年委员、安徽省人大常委”等等,如数地还给了中共。
一九九一年,当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将一顶“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的称号和可以大加工资的诱惑,送到我的家里来时,我让来请我填表的文联办公室主任带回的条子上写的却是﹕“我只是一个靠卖文吃饭的作家,没有任何特殊的贡献。这份光荣,谁要就给谁吧。”中共安徽省委派驻文联蹲点的沈付部长终于说出了令人诧异的话﹕“他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就是心怀异志。”
其实,我既不是一个书呆子,更非心怀异志,我只是想尽量保住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和操守而已。
我承认,因为文坛给我的痛苦,反而使我挣脱了专制文坛的名疆利锁,心,反而沉静下来了。我同样承认,也因为我要逃避现实,企图在历史里寻找创作的出路,我竟在不期期然之间,陷入了历史,特别是陷入了中国现代史的“重重迷雾”之中。适逢其时,幸运的我,居然欣遇了那一场刚刚涌动在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潮流;然而,我的不幸的人民,竟又被正在高喊着要实行政治改革的专制统治者,用坦克车的沉重履带,在长安街头辗成了一个个无形的血人……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汹涌的历史反思潮流之中,要用觉醒的理性,去观照那一片“用胜利者的谎言所编织”的虚假历史;更在抗议中共六四大屠杀的日子里,公开地面对着漫漫的游行抗议队伍,迸发出了我人生追求的第一声响亮嘶叫。此后,我终于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学者,使一个仅仅是意在写一部历史小说的文人,居然免为其难地将一副完全挑不动的重担,挑上了自己的肩头。因为,我深知,“要想拥有一个正确的未来,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史观”。
就这样,我才在对亲人朋友的难分难舍之中,告别了故土;在对个人前程的忧心忡忡之间,决心自我流放;更在海外别一番难言的艰难局面之中,完成了我的《谁是新中国》一书。而唯一支撑着我的信念的,就是﹕只要罪恶的共产专制复辟制度不能成为历史,只要中国的马列子孙们还在继续蹂躏着我的祖国,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历尽苦难的人民,我们的好文学和好文化,就永远没有出头的那一天。
我仍然想说的是,面对这样的奖励,我真的是激动而又惭愧。因为我实在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文化人而已。
再一次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