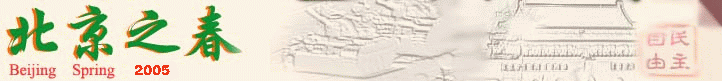《观察》画了一个句号——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五
傅国涌(浙江)
国民党当政以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法律、条例、细则等,如《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出版法》(1930)、《出版法施行细则》(1931)、《新闻检查标准》(1933)、《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标准》(1938)等。
但知识份子的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1934年2月上海各书局以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1936年1月上海71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禁。1938年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局发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国民参政会上也多次提案。对审查制度最有力的反抗发生在1945年,5月,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名作家、学者、教授提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并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8月17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被搜禁后, 重庆《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宪》(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等16家杂志联合发表拒检声明,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其中10家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当时整个重庆也不过是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些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写下了中国言论自由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
接着,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立即宣布坚决支援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时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八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不再送审。9月15日,《联合增刊》第一期出版。
9月8日,成都《华西晚报》等16家报纸、刊物、通讯社发表叶圣陶执笔的公开信予以回应,"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10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机构增加到22家。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发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昆明、桂林、西安等地也纷纷回应拒检。温和的叶圣陶连续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发表的自由》等文。
9月1日记者节那天,面对抗战的胜利,《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直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
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等十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要求。
11月,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
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联名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并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等五项要求。
在舆论的呼声面前,蒋介石1946年1月10日公开作出了他后来没有兑现的包括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四项承诺。
“我们的抗议”
抗战的胜利并没有迎来言论自由的全面胜利。1946年1月1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开放言论自由的第二天,杨潮在杭州狱中被迫害致死。190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的杨潮,笔名羊枣,是记者、军事评论家,还是翻译家,长期从事军事评论和国际时事评论,在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37年11月,教育家、民俗学者李敷仁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这是一家通俗化的报纸,以普通工农群众为主要阅读物件,宣传抗日,主张民主,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老百姓的疾苦与心声,并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国内发行13个省,甚至在苏、英、美等国也有订户。194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5年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对社会教育贡献极大,被青年农民尊为导师。1946年4月30日他遭到特务绑架枪杀,重伤未死,得咸阳百姓相救,才幸免于难。
1946年,西安《秦风。工商日报》持论公正,倡导民主,连续被特务捣毁、火烧,5月2日被迫停刊,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因为仗义执言,被非法枪决。
内战发生以后,封报馆、捕、杀报人的事屡见不鲜,言论自由当然谈不上了。在内战白热化、政权即将移手、面临王朝更叠的前夜,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份子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对当时发生的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他们几乎都作了抗争:杨潮之死引发了全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1946年1月26日,上海新闻界金仲华、柯灵、孟秋江、刘尊棋等60多名记者联名在各报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当局的抗议声明》,"羊枣先生无故被捕,时愈半年,既不公开审讯,复不宣布罪名,囚死狱中,实为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直接结果",“新闻记者失其保障,民意尽遭窒息,中国新闻事业必将走向绝路”。许多报刊发表社论文章,予以谴责。5月19日,发表《上海文化新闻界祭杨潮文》。
3月25日由《世界知识》、《周报》、《民主》、《文萃》、《新文化》等组成的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受迫害的同行。
5月,徐铸成等102名记者要求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6月,在"下关事件" 现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等人也被打伤,新闻界纷纷发表社论、通电,呼吁严惩凶手、保障新闻自由。39位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
7月,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联名抗议当局勒令50多家民营电台停播。
闻一多、李公仆因为反独裁、争民主的言论被暗杀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1946年6月北京七十七家报刊被取缔、查封以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柯灵等办的《周报》、黎澍办的《文萃》、郑振铎的《民主》被封杀,《文萃》三烈士遇难,他们都抗议了:有马叙伦、茅盾、叶圣陶、吴祖光、巴金、郭沫若、郭绍虞……等的抗议,有沈钧儒、徐铸成、赵超构、孟秋江等的抗议,1946年10月31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封面上就有“我们的抗议”五个大字。
1947年、1948年,上海《文汇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时,他们也说话了、抗议了。
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们深深懂得自由绝对不是一种恩赐,自由永远是人民斗争才能得到的果实。
这是言论自由史上最悲壮动人的一幕。
联名表达政见的传统
伴随着压迫言论自由的是杀戮、是牢狱、是查封、是流亡,然而,历史始终贯穿着知识份子群体抗争的声音。今天读一读这些报道,我们可能感到陌生,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见惯不惯的——20年代有胡适他们群体的声音,提出"好政府主义",那是军阀混战时代,大一统的权威丧失了,言论结社的空间是前所未有,也是后所未见的。
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亡国危险,知识份子联名发出群体的呐喊,组织社团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如1935年12月,《大众生活》曾发表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陶行知等281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3月,《生活教育》发表马叙伦等148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1936年7月、8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等等,虽然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但空前的危机及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终于造成了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大局面。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西南联大十教授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先生毛泽东先生","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要求尽快成立"立宪政府"代表了十大教授共同的见解。他们还提出四条"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的意见:一、"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二、"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摈弃";三"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四、惩处叛国奸逆。这些以教学为业的书生,在面临"治乱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是不能沈默的。当时和他们这样联名发表了意见的还有很多,比如成都文化界、昆明教育文化界等。
在这之前,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312个知识份子曾联名在《新蜀报》、《新华日报》发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
在这之后,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和平。同样的呼声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孤立的。
1947年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十三个教授在《观察》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份子的话,那么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名抗议政府迫害"手无寸铁"、"善良纯洁"的青年学生的90位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对学生和学潮的态度可以说是衡量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首要标准。
1947年5月发生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五二0运动,27日31位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声援,32位燕京大学教授发表宣言回应。
1948年7月5日,东北学生五千人要求撤消"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到北京参议会请愿,军警枪杀吴肇寿等13人,12人受伤。12日,404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七五"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闻一多、李公仆的血没有使知识份子闭上他们的嘴,放弃手中的笔。整个40年代后期他们动不动就发表政见,或联名集体表达对国事、对其他公共事务的意见。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数百人。即使在1947年11月大变革的前夜,国民党当局原形毕露,撕去民主的遮羞布,强令取缔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同盟时,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北大、清华、燕大教授当即联名在《观察》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签名者中还包括了钱伟长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是民盟成员,而是以"自由国民的立场"抗议政府不容异己的"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48个教授行使"无权者的权力",捍卫了人的尊严,捍卫了言论自由的原则。
在大变动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作为社会良心的自由知识份子几乎都没有沈默,而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20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传统,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谢泳先生说:“在40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他们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批评政府,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论去治他们的罪,大学教授在抗议政府的腐败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一致性是他们不畏强暴的力量源泉。”[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376页]
《新华日报》呼吁“笔的解放”
1938年1月11日,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凌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它的民主呼喊曾倾倒了千千万万知识份子,延安成为无数青年学生心中的圣地。《新华日报》以其民主言论在百年言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虽然《新华日报》创刊仅7天,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指使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到19日才刊登出来。1939年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八周年时曾发表一篇社论,回顾了八年办报的坎坷历程:“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报纸,但却经常受着非法的阻挠和破坏。讲发行,寄出去的报纸经常要受邮检,几乎完全被扣了,读者经年累月收不到我们的报纸。外埠报贩如要分销本报,轻则被封,重则坐牢。本埠发行,报贩被迫不卖本报,我们只好自雇报童,但仍还要经常受到威胁、毒打、拘捕、撕报等等阻难,使本报不能广泛的、经常的、及时的到达读者手里。还要对读者施出花样百出的迫害,不准看新华日报。工人、学生看新华日报的,就有被开除、被禁闭、以至于失踪的危险。总之一句,要使本报自己不能发、人家不敢看。试问这还谈得上新闻自由吗?
还有,我们的采访处处受到歧视,人家可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我们的广告受到封锁,在我们报上登广告的,就要受到威逼或者敲索。敌人投降,别的报纸纷纷复员,都到南京、上海、天津、北平、汉口等地出版去了。本报筹备于南京,创刊于汉口,迁移于重庆,八年来始终跟着政府为坚持抗战而服务。至抗战胜利,却不能和别报一样复员出版。所有这一切不合理、不公允的待遇,我们实在忍受够了。“
尽管如此,这张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的日报总算在他的眼皮底下毕竟存在了9年之久。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允许与自己打了十年内战的死敌在自己的心脏创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日报,这不仅在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空前绝后,在整个中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利用《新华日报》这块合法的舆论阵地,漫长的九年中,共产党高举民主、人权的旗帜,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赢得了人心。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收录了许多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今天重读依然能令我们血脉愤张。那是民主的号角、自由的号角、人权的号角,也是庄严的承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读到当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歌唱美国民主的评论。1943年9月12日发表的《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以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美国的理想——“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铁枷,1776年的独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3—117页]《新华日报》在蒋介石垂拱而治的山城重庆,不断地以美国的理想、美国的民主精神为武器,向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发起一次次的冲锋。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一文,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131页]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毛泽东说得更加明白:“‘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多么动人的文字,这是多么美好的承诺。
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言论专制制度,《新华日报》曾在《言论自由与民主》、《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等一系列文章中,为言论自由而大声疾呼。1945年9月1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记者节”,《新华日报》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社论,谴责“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的检查官,“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呼吁“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191—192页]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无论如何还是容忍了九年。九年的时光也许算不得长,《新华日报》那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如同黑暗天幕里的点点星光,确曾激动过一代青年。
《观察》绝响,余音已绝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周刊达到了百年言论史上书生论政的最高峰,成为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
9月1日,确乎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接续《大公报》的星火是这一天。1933年,因为刘煜生之死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9月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定为“记者节”。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也诞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巧合。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51页]接着,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以及“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半岁月中,储安平信守并践行了他在这一天提出的这些“信约”。《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近70位撰稿人几乎都是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由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储安平本人金石般的政论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在1949年前夜的中国,《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知识份子自由论政为提供了一块平台。1947年5月,当国民党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对此储安平说:“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政府磨刀霍霍,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7月17日,储安平发表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储安平文集》下, 248页] 1948年10月,离《观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为时不远,国民党败像已露,《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尽管哲学家别无动机、别无背景,仅仅“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还在呼吁和平,那是多么不合时宜。储安平曾说:“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要坚持“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又何其困难,何其难能可贵。他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观察》为百年中国言论史树立了一个最富有个性的批评模式,公开的评论、公开的批评,思想、立场、观点容或不同,但对批评权利的珍视,对公开批评的追求,成全了《观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时之选也”,其中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份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份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有真才实学、声望卓著的自由知识份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的学有专长、不左不右的知识份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份子的道义理想在战争的喧嚣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观察》最高一期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它以深刻的文人论政为一个黑暗、丑陋的时代画了一个句号。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依然为那个不幸的、生灵涂炭的时代曾有过这样一本周刊而感到温暖。
《观察》并不是孤立的,在风雨如磐、炮火连天的年代里,不说《大公报》这样有着世界声誉的民间报纸,差不多同时的民间刊物就有《世纪评论》、《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来之前嘎然终止。1947年1月,何廉、张纯明等在南京创办《世纪评论》,宗旨为“超然独立、公正客观”,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时与文》在上海创刊,发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复亮、张东荪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日,《周论》在北平创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潜、贺麟等,12月停刊。《新路》诞生于1948年5月的北平,与钱昌照、吴景超的关系最密切,当年12月30日就遭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刘不同在南京创办《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个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1949年是一道休止符,“时间”结束了,一切都嘎然终止。言论自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让多少昔日慷慨悲歌的志士感激涕零。那年头有什么言论自由,那就是呼喊“万岁”的自由,歌唱“时间开始了”的自由,“我们歌唱北京城”的自由。然而,不幸的是真诚讴歌“时间开始了”的胡风1955年就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头,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我们歌唱北京城”名动一时的青年诗人邵燕祥,1957年也成了“右派”,被剥夺写诗的权利长达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