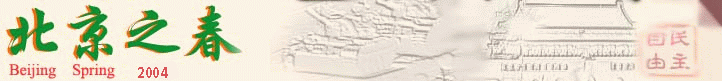百年惊梦——余杰《中国教育的歧路》序
陈奎德
“中国教育危机”的说词,挂在人们口头已多年了,然祇闻雷声,不见雨点,迄今仍未见其缓解的迹象。眼前这本书——《中国教育的歧路》,正是青年作家余杰对此痛定思痛的产物。
作为一本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著作,它收入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以作者的母校北大为对象,探讨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衰败轨迹及其象征意义;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的大学制度及其问题;第三部分讨论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问题;第四部分以几位代表性人物为脉络,讨论中国知识份子问题。
作者痛切命笔,自觉地以一个北大薪火传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剖析了当今中国教育界的乱象、怪像、丑相,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当代学校的衙门化、官商化、封闭化,为中国当代教育界现状勾勒了一幅令人忧心的总体图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今日北大之殇和昔日北大之光,看到了当代大学官本位的种种怪现状及其人文精神的沦丧,我们看到了仇恨的泛滥,看到了暴力与戾气是如何侵入中小学校园的,看到了公民受教育权的被剥夺,看到了孩子们是如何被置于死地的,我们还看到了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众生百态,看到了浦江青、钱钟书、余秋雨、谢泳、贾平凹、张维迎、杨帆等各各不同的知识界人物的身影和文辞。
不难看出,作者用以比较中国教育界的参照系,主要是西方国家(如芬兰、美国等)的现代教育制度。众所周知,在中国,自从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后,以学校教育为主轴的现代教育系统大规模诞生。这种新体系,迄今在中国不过100来年的光景。如果把这100年大致相等地划为前后两段,人们会注意到二者之间极其鲜明的对比。倘若暂且先按下其后半段——即20世纪50年代后——教育界所受的摧残不表,我个人更惊异的,却是其前半段,刚刚引进西方式的学校教育体制不久,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是的,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大学传统。近代中国,最为奇特的教育景观出现在上世纪的3、40年代(1937—1946)的中日战争期间,在烽火硝烟的边缘,在偏远的穷乡僻壤,像神迹一样冉冉上升,居然浮现出了一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大学——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上承蔡元培时代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不,它甚至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历史最悠久的巴黎大学,追溯到近千年长盛不衰领袖群伦的大学双子星座——牛津剑桥,追溯到“现代大学之母”的德国洪堡大学,追溯到“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大学,追溯到吸纳了最早中国留学生容闳等人的耶鲁大学,追溯到爱因斯坦晚年驻足的幽静深邃的普林斯顿……。这些千姿百态的大学,虽然赋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不同的独特传统,却享有共同的精神之母——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而西南联大承接的,正是这一伟大传统的核心,它铸造了联大的精神主流。同时,倘若仔细寻觅,西南联大所传承的精神脉络中,我们还能隐然辨析出中国东汉时期太学生学潮的遗绪、明代东林及复社的士大夫的以道统学统抗衡政统的那一脉精神遗产,以及中国传统中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潜在影响。于是,在这里“产生了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美国学者语)正如舆论所说,西南联大“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这所外有强敌环伺,内无高楼校舍,实验设备落后的校园里,承担了为社会“祛魅”的核心功能,肩负起为国族守护和传递普世价值的重任,从而诞生了近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代学术大师和知识精英,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教育的伟大典范。
但是,这一奇迹式的传统被中国政治的变迁嘎然中断了。
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不自今日始。实际上,1949年以降,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谬种就已播下,之后连绵流传,灾祸迭起,积重难返,鲜有宁日,以至今日已难于收拾了。
面对深重危局,人们急切探求的是:何以至此?
其源盖出于其基本制度: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委治校,官本位制。政府控制式的衙门化,“狼奶灌输”式的意识形态化,以及最近十几年来所新添的过度商业化,是教育危机的根源。
此外,也源出自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毛反复强调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由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份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和蔑视,从而实施了空前严厉的愚民主义,使中国教育与世隔离,倒退至蛮荒愚昧之境。
邓小平接替毛主宰中共之后,虽然一度使中共与知识界的关系有所缓解。但由于党管教育的基本构架未变,因此“面向世界”给教育界带来的活气与旧教育制度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张力,最后演变为1989年惨剧。 90年代至今,有“教育产业化”以及教育界精英融入权贵利益集团的变迁,然而,从基本体制未变这一角度观察,教育界仍是共式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一座堡垒。
如此,中国教育自1949之后的历史性断裂,严重影响了二至三代中国人的基本命运。回望其主要轨迹,从纵向看,自1949年以来至今,在诸种政治运动的折腾下,中国教育的轨迹中所刻下的重大历史印痕如下:
一、院系调整
中共建政不久,就把苏联模式强行推入教育界。1952年大学的“院系调整”,打乱了既有的教育格局,效法苏联的工具主义结构,取消国际通行的一些学科,如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企业管理等等。影响更严重的,是把过去素负盛名的一些综合性大学,通过拆解合并,弄成了分科很细的纯粹工科院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其目标是阻遏拥有广阔视野能够独立思考赋有人文精神的知识份子出现,务使学生变成“技术文盲”。其后遗症,至今犹存。
二、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言而无信,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左右的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变成“贱民”。大学成为该运动的“重灾区”。运动被整肃者,不少是民族精华。他们从此堕入地狱,坎坷一生。自此,教育领域受到严重摧残,万马齐喑,元气尽丧,言论和学术自由荡然无存。
三、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在极左狂热的“大跃进”以及知识界鸦雀无声的氛围下,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育界颁布《高教六十条》,公然明确规定“党委挂帅”;施行“教材改革”——以零碎的具体技能代替系统的基础知识。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度划线,而非以学业和品行为准,实施政治歧视。
四、1962—1964年,调整回潮
大跃进失败,大饥荒降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教育界返还部分常识,以“又红又专”代替空头政治;智育获得一定重视,社会上出现了一点非政治教条的艺术,中国学界获得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
五、1964—1966年,深入贯彻阶级路线,
文革准备期
毛泽东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击,在学校“深入贯彻阶级路线”,大肆宣传“反修防修”,“全国学解放军”,教育界重新意识形态化,政治气氛压抑而沉闷,“山雨欲来风满楼”。
六、1966—1976年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废除高考揭开序幕的。继而大学停办,“革文化的命”,全国整肃异己,“全面内战”。随着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此时,教育界已不复存在,被彻底摧毁。
七、1978—1989年,改革开放
以恢复高考复苏教育为先导,中国教育开始尝试与国际接轨。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界逐步淡化意识形态,校长负责制、学衔制等出台。特别是开放留学政策,它导致了近代中国第二波最大的留学潮,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多的互动。但鉴于意识形态的“狼奶”灌输仍然贯穿于从小学到博士的各级政治课,与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有内在的紧张,二者相互激荡,此起彼伏,使80年代的校园成为新旧观念的战场,成为各类思潮的渊薮。
八、1989年之后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从教育界爆发的,后来扩展到了全社会。它实际上是教育的“三个面向”的逻辑后果。这一后果最终指向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遂导致残酷镇压。之后,有一段向毛时代倾斜的倒退时期,重弹“反和平演变”的老调并加紧思想控制,在北大和复旦的新生中实行一年的军训等等。但是,由于这些举措受到广泛抵制,并且导致邓本人的经济改革商标变色。因此,“邓南巡”之后,教育逐步复归前十年轨道。但是受到意识形态化及过度商业化两头夹击,权力精英把知识精英逐步整合进利益共同体,知识界的批判性弱化,权力、经济、知识三精英集团模式日渐成形。
在本书中,余杰对中国教育的上述各个阶段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和分析。当然,由于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缘故,对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教育界,其着墨更为翔实具体。书中那些对中国教育界现状与历史的白描文字,对那些我认识的或神交的学界友人的一言一行喜怒哀乐的呈现,富于现场感,鲜活真切,如临其境,最容易吸引我的眼球。当然,无庸讳言,对远隔重洋观望中国教育界多年的笔者个人,也正好可借此一解乡愁。
事实上,在2002年6月,在一个基金会的支持下,我自己及一些同仁曾组织过一次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曾邀请中国内外的一些教授、专家、学者朱学勤、高华、何清涟、程晓农、陈小雅、周琪、戎雪兰、邵剑平、陈小平……等,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共聚一堂,畅谈教育。面对中国教育现状,与会者痛心疾首,描绘并分析了其中一些根本问题。如今,将近6年过去了,虽个别问题有所缓解:譬如政府预算中教育投入比例过低的问题,教育获得问题,大学招生数量少的问题,办学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化问题等。然而,大多数问题依然故我,有的甚至愈演愈烈,同时还生出了一些新的“怪现状”。
譬如,余杰在书中描绘的一所实施 “红色教育”的私立小学“德全学校”,种种“特色”,就是新的“怪现状”之一。它令我大开眼界。过去我如何能想像到私立学校居然也会有如此红色样板,而且做得如此跋扈夸张俗不可耐。这一怪胎,打破了我的一个成见:官办学校与私立学校——红色与白色,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当然,几许怪胎,并未影响我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总体判断。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仍是我的基本愿景。过去多年来,中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惟一由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国家。改革开放后,这种单一办学体制已遭遇严重危机。近些年来在办学主体方面,虽然有了一点松动。当年在夏威夷开会时,据说已有了几所民办大学。6年之后的今天,据有关资讯,“民办大学”已经有1000多家,在校学生数百万人。在我自己的乐观想像中,一幅多元化的中国教育界前景,似乎正破土而出。然而,本书占有的大量鲜活材料以及我从各个渠道获得的真相,犹如醍醐灌顶,把我从自造的美梦中浇醒。真相是,那些学校根本还算不上民办大学,算不上私立大学。因为这些民办学校并没有独立办学权,大部分民办大学没有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而且,所有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与公立学校一样,都受到政府严厉管制监控,都必须设置那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课。这种党化教育,算什么私立大学,不过是公立学校的附庸和预备班而已!
无论诉诸上世纪3、40年代中国自身的教育传统,还是诉诸国际发达国家卓有成效的教育制度,抑或是诉诸中国大陆近60年来教育失败的教训,中国教育改制的方向应当是很清楚的:政府退出学校。政党退出学校。办学主体多元化:开放私人办学,社会办学,外资办学,教会办学,创建各类学校生气勃勃的互相竞争环境,从而达成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目标,这才是改造中国教育的根本之道。
敏感的人当可看出,诞生上述教育界所需的条件,不多不少,正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应当而且能够提供的。除了在义务教育层面,政府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外,其余的,祇要政府松开钳制民间的那一双巨手,一个崭新的教育界——成百上千的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将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地遍地风流。
教育乃天下之公器。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变革,有赖于制度与人的互动性的变迁。有制度变迁而无人的变迁,则新制度将难于运转而归于无效;有人的变迁而无制度的变迁,新人将在旧制度的绞肉机中重行退化坠落。对人的素质变迁而言,教育将承担最基本的功能——塑造心身的功能、塑造新公民的功能。而中国老话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人”,的确是需要悠远深厚的土壤长期滋养的。
如果缺乏一个传统悠久、文明滋养深厚的教育界,“人”会被“树”成何种形态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这58年“ Made in China”的“产品”——批量生产的愤青、市侩和犬儒,与20世纪前50年大师辈出的时代所造就的人,相互之间,何等鲜明的反差!上世纪前50年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象,正如余杰在书中所引的谢冕礼赞北大的话所描绘的:“这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的魅力。” 那种声音,那种气息,似乎已是久远的回响了,似乎已是古代的韵味了,似乎已是“出土文物”了。以致我常常听到有不甘沉沦的朋辈发出“魂兮归来”的呼唤,以致余杰要以鲁迅早年的痛切呼吁“救救孩子”为中国教育呼救了。
当下的国人,喜欢谈“国运”;而我自己,更关注“人运”。然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无论你想为未来的“国运”还是“人运”占卜算命,预测他们的前景,你祇需在到中国的大、中、小学校里走马观花,考察一番,一切就了然于胸了。而本书面对中国教育界披肝沥胆所欲说的千言万语,实际上,可以凝结为一句预警: 人们,千万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2008年3月 陈奎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