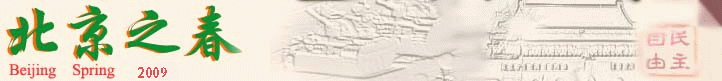中国政治传播学的新年思考
(海南)毕研韬
一、中国极需政治传播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老百姓承担的成本压力与其分享到的改革成果却不成比例。一方面,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生活成本逐日增加、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官员贪腐蔑视苍生、官商合谋巧取豪夺、社会矛盾日趋显性化;另一方面,网络、手机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快捷便利,利益多化化伴随价值多元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民意已成为不容决策者忽视的社会力量,同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全球化,国际因素对国内事务的因素日益深刻。按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不容易。我看(中国)大陆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管治语境下,中国要维护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愿景,就必须及时调整管治理念与管治手段,大力提升其象征性施政能力、全力维护“象征性秩序”,切实提高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尊重信息传播规律、提升对社会舆论的塑造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管治者混淆新闻与宣传,试图以粗暴的信息管制来制造“社会共识”。
如今,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不少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而中国的很多政治智囊还陶醉在《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经验主义政治智慧中,国内还没有几所大学开设政治传播学课程。中国亟需把传统的政治智慧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内加以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
二、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严重滞后
中国的政治传播学发展严重落后于实践需要。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者完成的含有“政治传播学”字样的专着祇有3本,分别是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1991年)、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2005年)。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被誉为“政治传播学《圣经》”,可该书中译本2005年8月才在国内出版。2008年8月30日晚,笔者在“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中搜索,论文标题中含有“政治传播”字样的论文祇有两篇,分别是中共中央党校宋黎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2007年)和华中师范大学李广的“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2007年)。
关于国内政治传播学发展滞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如下:
1,引入国内较晚。传播学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中国。
2,社会需求不足。中国的政客们习惯于研究传统政治智慧,对新兴的政治传播学的强大威力并不了解。
3,避讳谈论权术。中国尊儒、重“道”的文化传统使得权谋之术长期囿于密室,人们虽潜心钻研却不公开探讨。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4,学术环境限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学者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无法充分领略政治传播学的魅力。加上,学者们缺乏对政治运作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大多是纸上谈兵。
三、推动中国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设想
笔者在拙着《用信息颠覆世界》中曾指出,“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而政治传播学更是一门需要道术兼修、知行并重的新兴学科,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深谙政治运作的奥妙。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都诞生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
要有效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需要首先厘清传播学的边界。笔者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的理解过于宽泛。有人藉口传播学的多学科性而有意或无意“泛化”传播学,从而把自己归入传播学这门时髦的新兴学科中来。事实上,国内的个别的所谓传播学者充其量是游荡在传播学的外围学科。“泛化”传播学模糊了传播学与相近学科的界限,淡化了传播学的实战特性。传播学不是难民收容所。虽然笔者深信传播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学科,但鉴于中国学术界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我们至少需要清晰界定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的边界。
要切实推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就必须支持独立研究机构对中国高校、学科发展进行评估、排名。笔者已经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学习、工作了23个春秋,对中国高校的诸多内幕一清二楚。笔者认为,对高校排名(包括学科排名)是有效推动中国高校发展的有力手段。在中国传播学界,每年都有学者撰写传播学年度发展报告。不过,笔者希望每年都有更多不同的学者分别独立地撰写相关报告,从而使对传播学的发展描述更加多元、更加全面、更加真实。要保障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批评家。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倡“问题研究”:敢于直面中国现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优秀传播学者必备的素养与技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传播学者迟早会被淘汰。为此,笔者一向提倡“参与式研究”:政治传播学者应直接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而不应该远离社会、闭门造车。至少,政治传播学者应该倚重“田野调查”。实践出真知。祇有在现实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阻碍或推动社会前进的重大课题,才能实现自己推动社会进程的人生目标。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必须克服“单打独斗”的学术陋习。对全球媒介研究、大众传播具有深远影响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简称GUMG)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常常以团队的名义出版学术成果。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但是美国人提出的诸多传播学基本原理,都是研究团队在美国政府、军队、财团的支持下发现的。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有计划地译介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惟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开阔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才能帮助国人看清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而根据笔者在2008年8月初的检索表明,中国祇在2005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和美国W.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第5版)。
为切实推动中国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笔者希望能早日构建一个学术平台,为各地同仁交流、合作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学术氛围的持续改善,逐步完善推广、竞争、批评机制。笔者愿为此殚精竭虑,矢志不渝!
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毕生研究文韬武略(毕研韬)”,这既是祖辈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个人的奋斗目标。政治传播学正是实现我人生理想的手段与平台:用平生所学扶弱济贫、匡扶正义。事实上,政治传播学是一种道术合一、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它将政客们操纵舆论、愚民治众的种种伎俩大白于天下,从而为民众参政议政、实施监督提供了时空便利。这也是最终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由之路。
为此,本人正在筹建中国首家公益性政治传播学研究基地——岱宗参修室。这将是全球同仁交流合作、扶掖后学、传承薪火的绝佳平台。本人将虚心向全球各界前辈同侪学习,努力提升个人专业与学品修养;充分利用各种组织资源,全力倡导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模式;主动利用高校讲台和媒体便利,大力普及政治传播学知识,培养品学兼优的后学;创造性地运用专业特长,开发培植新的作业平台,有效推进中国民主化建设。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