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中的文化氣質及感悟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之四
仲維光
“Wie wenige, auch die Tapfersten haben jemals den Mut, klar einzugestehen,ihre Anschauung von gestern sei irrtum und unsinn gewesen.——Zwei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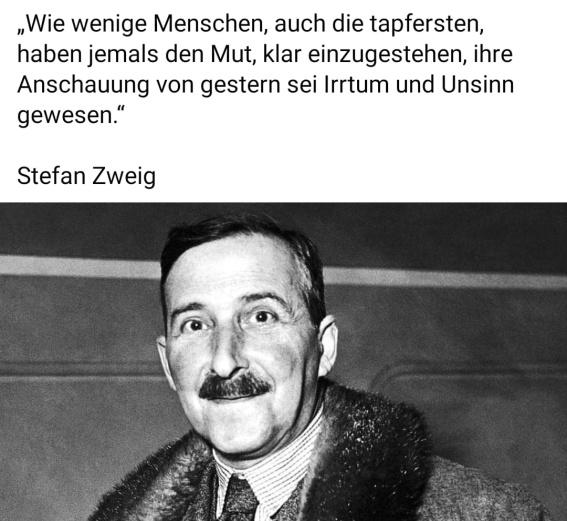
“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很少有人曾有勇氣明確承認他們昨天的看法是錯誤的和無稽之談的。”
——茨威格
文化氣質、文化感悟,圍繞的是“文化”問題。
文化,就廣義的文學性含義來說,是包羅一切生活方式內容的總體性指謂。但是就力圖準確地描述使用來說,文化一詞卻涉及了帶有不同傾向及性質的具體的指謂。
首先對應中文“文化”一詞的西文Culture,它明確地開始具有中文所具有的“文”的意謂,不過是最近三百年的事情,至於“化”則可以說剛剛開始有這種傾向的萌芽。具體說,馬勒有著很強的這類企圖,茨威格覺得自己所處的那一“文”境出了問題,但是還只是一種無望與絕望。而阿倫特,則幾可說沒有這類感覺,她是自己所存在及經歷的生活與教育中、文化中的勇敢寫手。
對於開始了“文”之過程的Culture,在其變化過程之中,亦有不同的對於“文”理解及追求。
自然,對於中文之“文化”領域中的文化性追求,同樣也是有不同的理解及追求。所以文化氣質、文化感覺可謂是一個非常細膩,且具有豐富內容的問題;在不同文化氛圍中,使用文化與Culture來描述某些現象,則一定會引出各種各樣的微妙問題,形形色色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而這就要求我們,在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更是要以“提出問題”,及“描述、對比問題”為要,而不是貼標籤式的,一錘定音。至於誰,哪種傾向的文化及其感知,能夠未雨綢繆地為未來帶來更多解答和希望,還要未來的經驗事實來證實,或者說不是一個能證明對錯的問題。
14.
在文化問題上,文化感知與個人感知的關係決定了作家及作品的性質。在這個問題上,馬勒、茨威格和阿倫特是很典型的三個人物,三位生活在基督教社會的猶太人藝術家、作家,其所從事的領域及其作品性質各不相同。
馬勒運用的是音符、旋律——音樂,感知的是歐洲、西方文化海洋中的人所遭遇到的問題。
茨威格從事的文學、文字,感知到的是歐洲,二十世紀文化及政治社會的災難。
阿倫特與之搏鬥的是政治問題、政治文化問題,直接面對的是社會問題、現實問題,用拉克爾為她的定位是政治評論家。
由此比較三人的文化態度及文化觀,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化思想史題目。
他們之中一人沒有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音樂家馬勒;一人經歷了兩次大戰——作家茨威格;一人只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政治社會問題評論家阿倫特。三人都是猶太人,卻對於歐洲文化的感受、認同,以及在人生中的反應各不相同。
馬勒公開說自己是個三無之人,無家可歸。他的音樂中處處顯露了這點。茨威格享受了近代精神及思想為歐洲文化帶來的輝煌燦爛,以及由此引起的來自文化基礎的反彈及衝突,及其導致的崩潰性災難,對此,他感到絕望,以自殺向這個世界宣示。阿倫特則經歷了災難,但是同時享受了災難後的個人輝煌。準確說她的名聲鵲起是在流亡後,在美國,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及其思想的評論中獲得的。她弄潮泛起的波浪激起現實的爭論。
與她不同,前兩個人,一個是音樂家,一位則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家、作家;結果則是或死於苦痛,或直接自殺告別文化帶來的苦痛及政治社會災難。然而阿倫特賴以成名、批評政治問題的文化思想基礎,卻正是造成前述兩人苦痛的,與她相聯繫,可謂是水乳交融的歐洲的某種性質的文化,準確說是德國社會的文化及思想——二百年前羅馬主義運動帶來的德國文化思想。
對於一個時期具有相當社會影響的一位“名人”的頌揚及其各種效應、影響,總會伴隨時間而隨著新一代人的到來而變化。絕大多數人是慢慢退去,退出人們的視野,只具有考證歷史事件的意義。能夠留下來的,其存在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定是由於他們提出及思索的問題具有超越時代的特點,是和人性及人的社會性相連的內容。就此來說,文化氣質及文化上的感知是和人們基本的社會性的生活方式,個人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連的存在。能留存下去,被後來的人記住的人一定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具有過人才能的人。
為此,在影響深遠的文化問題上,這三個歐洲的猶太人,馬勒、茨威格和阿倫特各不相同。在與西方文化、歐洲文化及猶太文化的關係上,對三者都不認同的馬勒,在他辭世一百年後顯示了強勁的影響,且有勢頭越來越大的,不可遏制的趨勢。
認同歐洲近代文化的茨威格,與猶太文化及猶太人毫無羈絆,但是在超離政治及社會現實的地方,在反思文化及人生的地方再次被人們發現,並且沿著他的生活及存在方式思索……
至於阿倫特,她的存在,聲明及思想工作的存在已經與猶太文化不可分割,但是卻是對猶太文化的不認同,與猶太文化的撕扯。在與西方文化及歐洲文化的關係上,她不僅與在歐洲文化中生活的馬勒的三無的感覺截然不同,甚至可謂毫無馬勒的文化感覺,人生感覺。同樣,她的文化認同和茨威格也不不相通。她認同的不是茨威格所說的歐洲文化——開放的文化,帶有自由主義氣氛的維也納的文化,她認同的是德國文化,是歐洲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如果概括地說,她的精神及思想的氣圍,她的文化遺傳符號信息,可謂完全是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而產生的Romantik運動,基督教宗教性文化及其塵世化的運動的潮流中的德國文化。說的更為直接則是——產生共產黨及納粹傾向運動的那種潮流中的文化及思想。
這一傾向導致了她對於近代、對於德國社會及艾希曼的態度,導致了她治學態度及傾向,對個人與國家關係的看法,導致了對社會人生的態度以及與她的那些左派意識形態分子友人無區別的社會行為。在文化問題上,阿倫特雖然批評茨威格沒有投入猶太人與納粹的鬥爭中,但其實她自己對猶太文化及猶太人並不認同,她的投入不僅反向,而且在猶太人遭受巨大災難的時候及其後,遭到猶太人的厭惡。
在我看,不僅馬勒、茨威格,而且阿倫特的文化態度、文化思想也是一個很好地研究題目。而不能夠輕易地判斷。現在,在對於這三位不同的藝術家、作家及其不同的文化認同的認識上,在中文世界出現的用阿倫特來臧否茨威格,其結果不是判斷內容,而是讓我們直接關注到“李歐梵先生的文化態度”。
這一關注,進而讓我在這個方向上想到:包括林毓生、余英時先生在內的李歐梵先生那一代人的文化觀、文化感及其人生感悟,當然是如認識馬勒、茨威格一樣的重要問題。文化觀、文化感對於了解三位先生這一代人——五四後,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的文化思想氣質、治學方法及其學術工作,乃至為人的重要性,它是用來解析這一切的背景及思想基礎的一個很好地切入點及視角,打開文化史、思想史的一把鑰匙。
在文化觀、文化感、文化氣質問題上,不僅有橫向的中西之對比思索,而且有縱向的近代中文文化領域中的王國維、陳寅恪之比,當然也有從胡適到五四後一代,以及我這兩三代人之比。而這個交叉立體性的對比思索,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壞問題,而是不同形式的生活方式,精神和思想方式問題。我們無法為某種傾向貼上好壞性的標籤。
15.
A.從最表面的層次看,李歐梵先生談茨威格的由於文化遭遇及其反應——自殺,如果不說是犯了文人“以小博大”的忌諱,至少也是過於輕率。因為時下誰都知道,不能夠把王國維的投湖自盡只是看成是對於北伐軍隊就要到達北平,黨軍來了;更不能看作是他欠了債,生存及生活出現了嚴重問題。自然茨威格的辭世也是如此。文人,以己度人,尤其是近乎以小博大的事情,是很危險。因為首先是在思想上,你力圖談你自己沒有能力把握的問題、思想及知識。其次是你忘記了子非魚。你可以不投入生活,偷閒尋樂,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不是用生命的激情熱烈而忘我地生活。第三是在為人上、人生觀上,你以小事度大為,很可能是不知好歹。“以小度大”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距離不遠,而這就犯了大忌。
與之相對,陳寅恪先生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之文氣、之文化氣質及感知,之中學西學之體認,可謂轉折時期開天闢地之作!
B.在我看來,從涉及到文化問題的深層意義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可謂是個“文化危機的世紀”。因為在二十世紀發生了史無前例的人類大災難,數億人死於由意識形態所導致及操控的戰爭和迫害,因此最初這個世紀被稱為“意識形態的世紀”,繼而由於一九八九年發生了柏林墻倒塌,共產黨集團崩潰的事件,而它是繼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失敗後,歐洲產生的另外一個極權主義的失敗,很多西方人甚至以為西方文化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因此在反省總結極權主義的教訓中認為二十世紀可以用“極權主義的世紀”來稱謂。對於二十世紀的災難,實際上我們透過這些政治及思想現象,從馬勒、茨威格及阿倫特的藝術及思想追求以及各種遭遇,乃至世紀初的王國維絕望,其後陳寅恪的磨難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可謂是個文化問題叢生、危機四伏,乃至不斷地發生及陷入崩潰性災難的世紀。
為此,生長於二十世紀中葉及後半葉的學者,如果對於文化問題沒有感觸,那麼這位學者或者說藝術家、作家的感覺及精神思想,一定會影響及導致他的思想追求,學術研究深度、範圍及成就。這一問題不僅反映在馬勒、茨威格和阿倫特身上,而且也一定表現在我這一代所直接接觸到的,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後出生的第一代後人——余英時、林毓生和李歐梵的治學、思想及社會影響上。
C.從歐洲社會最近二百年的政治文化史來看,近代化加速了歐洲世俗化、物質化的發展,從而加速了歐洲社會的開放性。但是這一開放性也帶來了問題,它使得傳統的歐洲社會的載體——歐洲社會的精神及社會結構,固有的文化及政治機能,是否能夠承載這一發展為歐洲社會及其擴張到全球後的西化了的人類社會帶來的問題,而不發生動蕩及混亂性的災難成為問題。
發生於十八世紀下半期、發展於十九世紀的Romantik運動即是傳統的宗教社會對於這一近代化帶來的問題的反彈和反動。這個反彈和反動在二十世紀更加加劇,它帶來了人類史無前例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及極權主義國家。這使得族群屠殺成為不斷發生的常規事實。所以可以說自從進入二十世紀到今天,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年代。這個時代的特點是頻繁發生的社會撕裂、族群撕裂對立,新舊文化碰撞、東西交叉混亂。它們不僅帶來了更為深切的懷疑、彷徨及思索,甚至也帶來水火不容的對立。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馬勒深刻地感到了,固有的生命及其感知對於這個西方社會中近代化和曾有的宗教社會的文化的衝突及反彈,而這讓他更深刻感到在更廣泛的意義下的西方式的二元化的文化所特有的,對於生命和伴隨生命的精神及感情,感覺及知覺的有限性的壓榨及禁錮。對此,馬勒不僅有能力感到,而且有能力用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當的表達及探索。他對自己才能的自信心讓他即使在極為孤獨不被人解的狀態下,也確信他的感覺及音樂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他說自己的音樂是屬於未來的音樂,五十年後的人會理解他。
茨威格對導致政治及社會災難的深層的這個文化危機,有相當的感覺,但是他只感到問題,沒感到或者說沒有如馬勒那樣感到应该試圖去掙脫它。現實,讓他感到的是原地掙扎,這個原地是原來的文化氣圍,而不是原來的生存境地。旧的文化氣圍、新的生存境地讓他感到的是,他已經六十歲,重新開始尋找一種精神的和生存的未來,幾無可能——這讓他陷於絕望。他的絕望是精神性的、對自己的絕望,發現自己在現實社會曾經和正在取得的成功,已經並非是真實的成功了;他的絕望絕非是現實性、物質性的社會存在的絕望。
至於阿倫特,和茨威格相比,那個時候她還掙扎在生存線上,思想領域的開場階段。究其努力的性質,她其實是個弄潮兒,由於她從來沒有從根本上對於這類深處其中的潮流的根源產生本能的反抗及審視,因此對災難及混亂,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阿倫特其實是熟悉的。她感到陌生的是馬勒和茨威格的精神感覺及思想狀態,所以她會嘲笑茨威格的精神及思想狀態。
阿倫特不僅嘲笑猶太人茨威格,而且還有猶太人以賽亞•伯林和法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阿隆等很多人。她提及他們的語言甚至惡毒。例如對於阿隆,阿隆不僅幫助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在法國傳播,而且在自傳一書中謙虛地說,他為在三十年代對於阿倫特的流亡有所幫助而感到欣慰。但是阿倫特在給他丈夫的信中說:
“那些歐洲人,真的是上帝懷著譴責懲罰的心情創造出來的最大的廢物。昨天我才見到雷蒙•阿隆和馬內斯•斯珀伯(Manes Sperber)等人。他們所有人都對我懷著極大的尊敬和些許畏懼。我表演得很友好,因爲擔心蔑視太明顯會被看出來。”1955年9月13日致布呂赫信)
對於她不僅和各類猶太裔知識分子,而且和一般猶太人格格不入乃至直接的思想衝突,研究她的學者都感到了其中所隱含著的文化傾向,以及文化氣質的不同。蹊蹺的是,事實上所有的人都看到阿倫特代表的是德國文化的反應——德國Romantik運動帶來的那種文化及思想氣質的延續,一個滿由於這個潮流中,認同這個潮流的猶太人的反應。而這可以讓任何一個人看到:阿倫特顯現給我們的文化問題,和馬勒及茨威格不同,是另一層次及領域的。
而這就使我們可以更可以進一步肯定地說:在談論馬勒、茨威格和阿倫特的問題時,最重要的是文化問題,尤其是深層的文化問題,乃至深層的人性品格。
文化認同及其帶來的危機及反彈,是無法迴避及必須細緻地分析描述的。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可以輕易處置的問題。
D.文化感知、文化認同,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氣質及思想傾向不僅對於上述西人學者、藝術家及作家,而且對於處於近代化、西化漩渦中的中國知識人更是一個逃不掉、迴避不了的問題。從上代文人、知識人王國維、梁濟、陳寅恪,到我這兩代知識人,莫不是人生初醒、識字就面臨文化問題……,戰亂、流亡、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文化毀滅,精神屠殺,莫不是切膚錐心的文化事件,哪一件都比馬勒、茨威格以及阿倫特經歷的歷史和社會動蕩更為劇烈。能否感知、如何及感知到什麼、感念是何,全看一個知識分子的天生感覺及後天的教養,全看一個知識分子浸泡過的文化濃度與底色。
在這樣一個時代及社會動蕩中,如果以為西方的文化是天堂文化,是歷史發展的終極道路乃至人類終結文化,而二十世紀歐洲社會的災難竟然沒有讓人感到危機及無望,即對這種交叉對立的文化及現實無感、無動於衷,一定是藝術家、思想家對於生活及世界感知的疲弱,以及治學能力的遺憾。
細想我的上一代,五四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的以余英時、林毓生和李歐梵先生為代表的“第一代知識人”,在上述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李歐梵先生在“文化問題”上是有能力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感知到了文化問題,在不同思想及文化,中國傳統的,西方近代、現代的,以及五四後極端化了的,來自西方徹底的意識形態化的黨文化的碰撞中,對於最極端化西化的大陸學者、作家、學風、學識他清楚地感到了問題,但是,他手下留情,保持了必須的距離。對於應該說的,且能說的他基本上都轉彎抹角地說到。然而,對於“文化情懷”而來的“文化關懷”,我卻也感到,他似乎對現代問題的嚴重性體會不深,著墨不多——談的過於輕描淡寫了。而現在,他在茨威格和阿倫特問題上的談法,則第一次讓我感到,他的文化感知的性質及厚度、限度,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不僅是他的觀點,而且更是他對於文化問題的視角以及對於引述文獻的認識及使用方法,是值得討論的。
這一發現進而讓我想到了他的同代人——余英時和林毓生。這讓我想到,和我對於他們對西學的理解及他們治學的方法的質疑相比,他們在文化問題上所顯示的態度及看法,更加值得思索辨析。因為文化感覺及文化態度可以更為直接地說明一個人在一個時代中,社會動蕩中的氣質及教養,人性、學養的品質。
在此,藉此機會我同時要強調,林毓生先生和余英時先生無論在問題還是文化關懷上,都是該說的沒說,不該說的卻說了不少。如前說述,林毓生先生在和參與建立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真理部創建者,且從來也沒有徹底脫離過真理部的王元化先生的思想交往史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余英時先生和真理部後代——《河殤》的作者群的關係也是一個案例。他們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似乎是和上述人有所距離,但是在談文化思想問題時沒有顯示出,也確實是沒有根本性的不同質。所以李歐梵《漫談茨威格》所顯示的文化關懷,讓我感到的不僅是長遠的文化問題,而且更是直接的眼前的,我們這幾代人的文化精神思想問題。
因為文化感知,是長遠的政治及社會關懷的基礎,它們展開的形而上學前提;文化感知影響到的是根本的人性及人類存在的精神思想品質!
2024.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