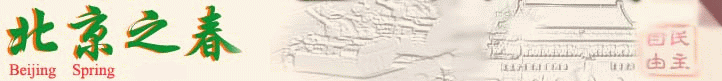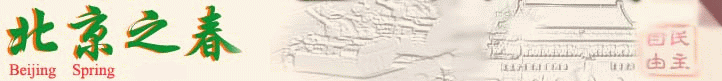文明開化與中國的自由出路:
批判極左僣政與民族幻想,回歸秩序現代化之道
岡本尚文
-
前言:中國自由化的核心問題
過去百年來,「中國如何實現自由與現代化」是政治思想與改革論辯中的核心議題。但歷史證明,中國並未如某些自由主義理論所樂觀預測的那樣,隨經濟發展自動轉型為自由民主政體。事實上,百年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始終繫絆於兩個虛幻的信仰: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者沉溺於歷史仇恨與文化自戀,另一者崇尚平均幻象與集體主義,在實踐上則共同構成極權政體的民意基礎。
中國之所以始終無法邁向真正的自由與現代文明,根源不在制度設計,而在於大多數人民的素質與價值觀深陷這兩種意識形態中,成為鞏固極權統治的基本盤,難以接受「文明開化」的洗禮。
-
中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構性障礙
-
民族主義的仇外文化與「道統接收」
孫中山雖創立民國,但其思想根本仍建立在「百年國恥」與排外民族主義之上,之後北伐、抗日的民族敘事幾乎被中國共產黨「接收」。中共將其轉化為一種反西方、反個體自由的統治工具,讓民族情緒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正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現代化不是僅靠制度移植,而須建立在特定價值文化之上。」中國民族主義強調集體仇恨、道德優越、文化本位,與西方資本主義所需的個人責任、自我約束與理性倫理根本不兼容,無法構成自由社會的價值基礎。
現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卑轉自大、自我感覺良好、排斥西方價值的文化沙文主義。這種「義和團式」的民族情緒,在中共政權的詮釋下,成為延續暴政的群眾動員工具。
-
社會主義的巨嬰依賴性與經濟制度阻礙
中共的社會主義不僅是經濟控制,更是文化控制的工具。大量中國人深信「奶媽式」國家能為他們打理一切生活事務,從就業、醫療、育兒到言論道德,期望國家是全能家長,這種巨嬰文化導致極權具有高度民意基礎。
奧地利經濟學派尖銳的批判社會主義,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調:「計畫經濟的實施最終必然導致自由的毀滅。」因為在中央計畫的架構中,個人沒有選擇的餘地,資源無法透過價格機制有效配置,暴力機器就必然壟斷資源分配,從而催生極權主義。米塞斯也在《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中指出:「社會主義無法計算成本,因此無法形成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導致普遍的匱乏與官僚化,進一步強化國家干預與個人依賴的惡性循環。」
-
中共極左僣政的巨嬰與暴民基本盤
中共打著反帝反殖、民族復興的旗號,奉行極左暴民政體的統治邏輯。他們鼓吹鬥爭、消滅資本、拒絕個人自由與物權神聖,並藉由資訊封鎖與意識形態洗腦,使廣大民眾甘願放棄自由,只求被國家「管好一切」。這類暴民與巨嬰型群眾構成了中共政權的基本盤,喪失自由意志、拒絕自律,只求家長式國家為其規劃人生,其三觀與自由世界人民迥異。
「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在中國網路防火牆內,筆者親歷過無數支持極權的「順民」,他們厭惡自由,恐懼變革,希望國家如奶媽一般包辦生活。這種深層文化心態,是中國政治病灶的根本所在。
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反賊,雖有對言論自由、民主制度的真誠追求,但其發展受限的根源,並不在於其主張錯誤,而在於這片土地上絕大多數人尚未擺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洗腦。
個人主義、私有產權、法律平等和理性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但這套思想難以被沉迷於「強國夢」與「共同富裕」的中國大眾理解與接受。更遑論那些仰賴國家「打理一切」的社會主義巨嬰與暴民,他們對自由的態度從來不是渴望,而是厭惡與排斥。
-
威權現代化與文明開化:台灣模式的啟示
-
蔣經國與「秩序先行、自由後置」的實踐
與中國大陸的極左僣政相對,蔣經國的台灣現代化路線提供了一條可借鑑的「威權下的自由化」典範。他並未走毛澤東的群眾動員與階級鬥爭老路,而是以國家機器維持秩序,保障市場經濟,推動基礎建設,吸納本省知識菁英,扶植中產階級的崛起,最終促成自由化與民主轉型。
自由不是自上而下灌輸的抽象概念,也不是草莽革命中自然誕生的產物,而是有賴於經濟自由、社會秩序與思想啟蒙的配套建構。這正是「文明開化」的真正含義。
這與杭亭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論述的「政治現代化」路徑高度契合——當社會動員與政治參與快速上升,但制度能力不足時,民主化反而可能導致無政府狀態與失控動員。唯有透過穩健威權先建立秩序,國家能力增強,才有條件轉型。
-
日本殖民台灣:非西方世界成功現代化的範例
同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也展現了威權現代化的正面力量。後藤新平等殖民官員以專制手段建設基礎設施、引進現代教育與衛生制度,使台灣擺脫落後窪地進入文明之門。李登輝曾直言:「若非後藤新平,台灣今日可能仍如非洲落後地區。」
韋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論說明,現代化的關鍵不在於政體是否民主,而在於是否具備制度化的專業官僚結構與行政效率。日本殖民政府正是以非民主手段,實現了比清國更理性與有效的統治結構。
若當年由余清芳、莫那魯道等農民、會道門或原始部落領袖領導的抗日運動成功,台灣恐早在民族革命浪潮中被共產政權併吞,甚至獨立也不過是個資源匱乏、缺乏治理能力的第三世界小國,無從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
-
自由化的條件:中產階級、資訊開放與社會自治
-
經濟自由是行動與思想自由的前提
哈耶克認為自由市場本身就是一種秩序,它容許個體根據自身知識與偏好進行選擇,並在自發秩序中創造知識的分散傳遞。當中國仍維持國企壟斷、公有制導向、土地國有制時,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難以落地。
-
自由非群眾運動產物:顏色革命的反面教材
許多反賊期待通過顏色革命改變政權,然而中東與北非的失敗例子正好說明這種思路的危險:
歷史證明,光有民主程序並不足以帶來自由與文明,民主化運動在失去秩序保障後迅速淪為宗教狂熱、軍閥割據與族群內戰的溫床。這些例證警醒我們,顏色革命並非通向自由的萬靈丹。在人民缺乏公民素養、社會缺乏中產階級與自由市場基礎的前提下,貿然推動民主往往只是導向新一輪暴政的開始。
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提醒我們:「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或弱國國內,政治真空容易被極端勢力填補,而非理性秩序的自由政府。」換言之,無秩序的自由不但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招致混亂與暴政。
必須務實地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尚未完成啟蒙的社會中,單靠選票或街頭運動無法實現制度性轉型,必須依賴有秩序、有紀律、有理性推進現代化的統治權威。中國若一旦進入無秩序的政治真空,極可能不是走向自由,而是陷入民族主義或極左暴政的再次迴圈。唯有有序的現代化,才能為真正的自由奠定根基。
-
未來中國的可能出路:三位一體的文明聯盟
基於以上理論與實例,我們得出結論:中國的自由化,必須由商人、知識分子與開明專制者組成的三位一體共同推進。
-
商人推動市場經濟,創造財富與中產階級,為公民社會提供穩定根基;
-
知識分子提供理念與理性工具,引領觀念啟蒙與價值轉型;
-
開明專制者負責以鐵腕維持秩序,鎮壓暴民和愚民,抑制極端動員,推動現代制度建設。
這種模式既非自由主義式「先選票、後制度」的冒進之路,也非社會主義式「國家全能」的專制幽谷,而是一種制度建設與文化啟蒙並進的文明開化工程。當經濟自由實現,個體才可能追求行動與思想自由;當資訊開放,人民才可能學會判斷與反思;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民主才有生根發芽的可能性。
-
結語:文明不是投票的結果,而是秩序與理性的積累
今日中國,不缺自由的想像,但缺文明的土壤。唯有認清:自由不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直覺,也不是人人配享的自然權利,而是一種透過秩序、財產、自律、教育長期積累的文明果實。一切自由都以秩序為前提,否則將淪為暴政的工具。
中國的自由化與現代化,不會來自革命,不會來自選票,也不會來自一群尚未擺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幻覺的群眾。而只能來自由上而下、由秩序而自由的文明開化工程。我們需要的是新一代的後藤新平、蔣經國、李光耀,而不是新的毛澤東或造神式的民主鬥士。只有當知識分子敢於啟蒙,商人捍衛市場,開明威權敢於擔當,華夏大地才可能真正從東方暴政的幽谷中走出,迎向屬於自由人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