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解讀: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們的畫像(下)
仲維光

我之所以非常推崇奧威爾這篇《評註民族主義》,因為它幾乎是我一九七五年第一次拜訪許良英先生,和他爭論的大綱。其後我花了三十多年才逐漸說清這些問題,所以我不僅深深地感到奧威爾的深刻及功力!而且也被深深地觸動——如果在五十年前的一九七〇年代看到這篇奧威爾發表在一九四五年的文章,我的一生會節約多少時間,少走多少彎路!
現在,我希望時下能接觸到更多信息及書籍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有類似奧威爾的這種衝動、有能力——在精神思想上、學術上挑戰及辨析自己的社會,以及大學、學術機構中的那些所謂專家、教授,尤其是那些“意識形態分子”!
因為現在,和二〇一八年奧威爾這篇文字重新出版時相比,俄烏戰爭及新冠疫情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
這個世界最不能夠讓人信任的就是那些專門從事政治的黨派教團人士;
最不知要臉的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那些依附於政治黨團及其意識形態的知識人、媒體人!
——引自作者推特
目錄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註民族主義》: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1-3.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1-4.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啟蒙及啟蒙運動——啟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A.解讀的意義
如果說“導讀”是對於在另一種語言中的重新解釋性的翻譯譯文是否把握了原意的梳理,它介紹的是對奧威爾著述原文的理解,那麼“解讀”涉及的則是關於奧威爾表述的這一內容如何理解,即它在一個思想、文學、歷史的時空式的框架中的具體位置及其走向是什麼。這就是說,在一個多重維度,眾多可能的時空中,究竟設立什麼樣的思想及精神框架,或者說參考系,亦或描述系統,才能夠更簡單準確地把握奧威爾的著述。而這不僅涉及到奧威爾,也涉及到解讀者對於整體的思想史,對於具體的描述方法及框架的理解和把握。由此可知,“解讀”涉及到的是解讀者看到的及想到的對於奧威爾這篇著述的理解——從奧威爾的這篇著述中能夠得到什麼啟示及教訓;在一般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如何理解它;在奧威爾自己最重要的著述中的位置;以及隨之而產生的,它對一個東方人,中文讀者來說,理解奧威爾的著述會有哪些重要的特點——帶來什麼問題及及啟發。
B.我對奧威爾及其《評註民族主義》解讀的思想基礎及專業認識:
解讀“奧威爾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這也就是說奧威爾的文章在西方社會的一九四五年——文章發表時的“針對”的是什麼,其意義是什麼?今天,二〇一八年,七十三年後再次發表,在西方,又是為什麼以及再次引起的反響的性質的異同是什麼?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於奧威爾思想及其傾向,以及對於時代及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狀況的理解及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我的解讀建立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準確理解及把握奧威爾思想首先必須看到,在近代思想史的潮流中,奧威爾是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及整個西方知識界、文化界中,最為典型地承繼了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作家之一。在政治及社會問題上,他則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然這就意味著,理解奧威爾的關鍵問題是理解什麼是啟蒙以及西方近代產生的自由主義是什麼。在這兩個問題上不清楚或者說有誤解的人,不可能理解及把握奧威爾及其著述。當然反之,誰如果想了解何為自由主義及啟蒙,認真地理解奧威爾的思想及言行可謂是一個非常具體且準確的方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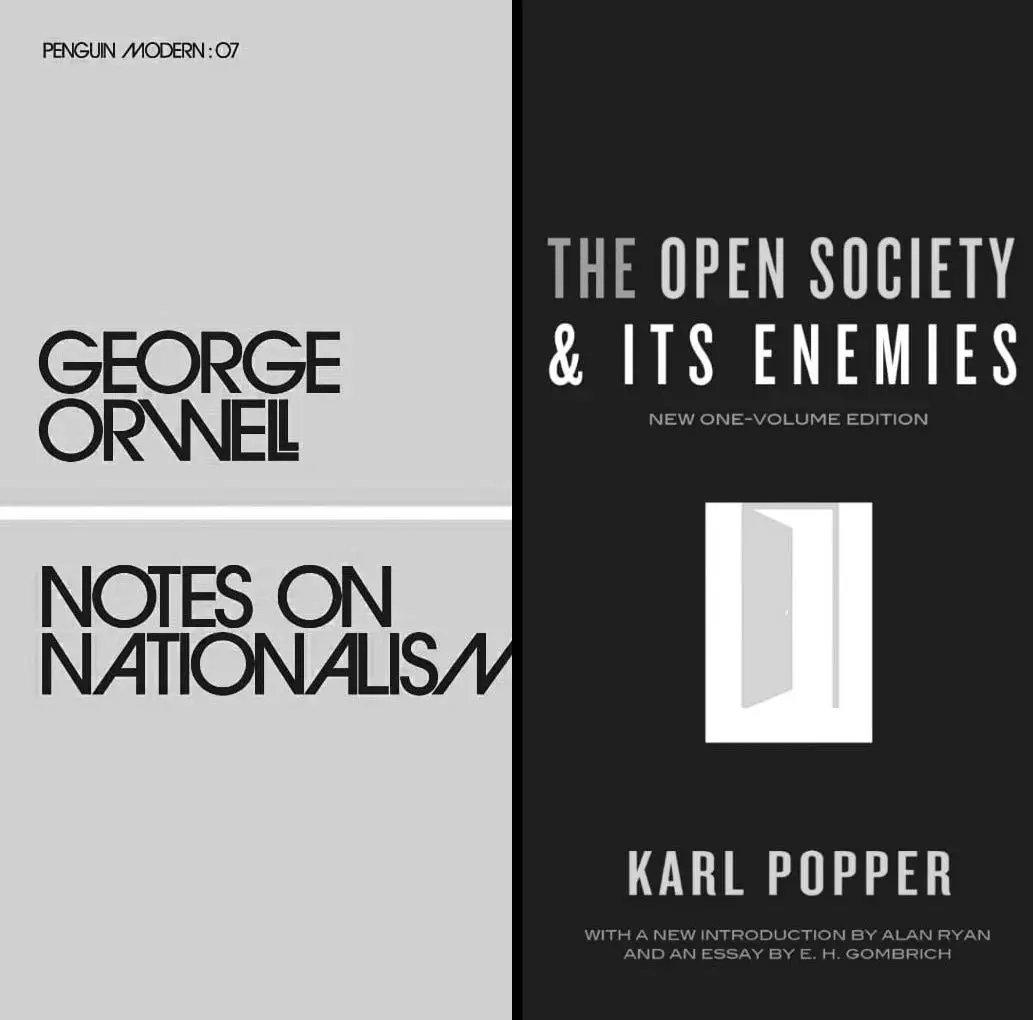
②準確理解及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必須看到奧威爾關注及研究的問題——當代極權主義問題。這篇文章是奧威爾這一關注、對其認識及描述的產物。為此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了解及認識,對於二十世紀在知識分子中呈現的對於這一問題的提出及討論,以及它在不同知識分子中呈現的不同傾向及不同方向的關注,都是認識及把握奧威爾的一般思想及這篇《評註民族主義》所必須要有的思想背景及認識基礎。
③關於極權主義,二十世紀被自由主義學者等称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它是貫穿二十世紀百年,造成二十世紀所有最重大的人類災難的根源問題。我因為生在這個世紀及極權主義國家中,因此它也是我畢生關注及研究的題目。
在我對於西學及極權主義的關注及研究過程中,此生私淑或者說追隨過乃至認識了一些把握極權主義問題必須知道,必讀的著名的西方學者。
我追隨及從師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因為他們從事的是哲學探究,和我對於認識論方法論的關注息息相關,對於思想史問題的認識契合;我私淑德國戰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代表布拉赫(Karl Dieter Bracher),是因為他從事的是歷史學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我追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因為他的政治學、社會學思想及其極權主義研究。在這些人中,當然還有奧威爾,而他從事的是Literature,即被中文翻譯成文學一詞的Literature所具有的文學及文獻性方面的,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描述和研究。
我的追隨及私淑讓我明白,所有這些西方學者關注的是同一歷史時期中的同一歷史性的政治及社會現象——“極權主義”現象。但是他們運用的方式、方法不同,所呈現出來的思想形式及內容也不同。
就奧威爾所運用的文學性的方式方法而言,這樣的描述及分析所具有的文學-文獻性的特點是,它們不是抽象的、由理論所構成的知識性的知識,而是描述性、講述式、現象性,具象、具體思想的羅列式、對比式的。這一特點無論是在奧威爾的小說中,如《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還是在他的文學思想性的評論中,無不顯示出作為文獻的文學的這一特性——言之有物、有形,有思路及其系統。而這一切又都在另外一個層面或說領域,具有二元論的西方精神及思想領域中的各種精神產品的“知識性”的特點。它甚至讓我看到并深切地認識到,西方文學所具有的與東方文化中的文學的最本質的區別就是——西方文學的文獻性。
其次,Literature式的揭示及解釋的特點,正如奧威爾自己在“我為何寫作”中談到的,它首先是涉及個人性的感知。其次是他對於文字及思想的美學性的要求。第三是渴望發現歷史本來面目,供後來人思索的歷史衝動。第四則是廣義,渴望將世界推向“好”的方向的政治衝動,以及對於人活著就必須面對的道德要求的追求。在這種意義上,在我看,奧威爾的作品可謂西文純文學的典範。對此有關西文Literature與中文文學之不同,西文文學是什麼的理解,還可以參考奧威爾的“政治與文學”一文。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解讀奧威爾這篇有關“廣義的”“民族主義”的著述的思想史背景、知識框架以及專業性——Literature性的要求的思想基礎。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A.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奧威爾開宗明義地說:有一種思維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它影響了我們對於每一個問題的思考,但還沒有被賦予名字。在現有的名詞中他選擇了這個最接近其這一思維方式內涵的“民族主義”這個詞,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他用的並不是這個詞的具體指謂的含義,而這是因為他所談論的這種“情感”並不只是和“民族”聯繫在一起,而在人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會依附於不同的內容及形式而存在,並且會產生類似的政治及社會影響。
由此我們看到,奧威爾運用民族主義一詞,要描述的不是狹義具體的民族主義問題,而是一種心態、精神氣質及思維和語言方式。這種心態、氣質及思維方式在英語中還沒有對應的單詞,所以他姑且使用了“民族主義”一詞來代表它。
其次,這就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及個人的心態及思維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當代新發生的一種現象,所以在英文的“文學”領域的描述中還沒有約定俗成的對應的術語。
然而,如果這個現象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及社會生活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那麼它一定會被不同領域中的敏感的人及學者、作家所關注到,也一定會被持續地討論及研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奧威爾關注的這個心態及思維以及語言方式問題,早在十八世紀末期產生時就開始被注意,當時在法國被稱為ideology——後來在中文中藉助日本譯法翻譯成“意識形態”,或者直譯為“觀念學說”。
各類意識形態、觀念性的學說,在十九世紀百年,在歐洲社會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過程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及展開。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它給社會帶來的劇烈運動乃至動蕩災難,在一九一七年激發出“俄國革命”。繼而在二十年代初期以後,在意大利發生了法西斯主義運動,在德國則產生了納粹主義,為此在歐洲乃至世界各地,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的劇烈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使得這一思想傾向及其影響在不同的領域引起具體的討論及爭論。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韋伯對於學術生活中的價值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問題的辨析——學術研究的非價值問題;明確地被弗格林具體地談到的“意識形態”問題;卡爾•波普等哲學家們關注的整體論問題,各類形而上學性的思辨性真理論的哲學問題,以及三十年代弗格林和阿隆所開始具體研究的政治宗教問題,後來他們轉向的替代宗教和世俗宗教問題;在奧威爾之後,五十年代初期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到的意識形態問題、暴民運動問題等等,都是對同一性質的思想及政治社會問題的討論。
這一思想問題在五十年代初期後,由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開啟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框架中,得到規範性的討論後,即如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開始提到的法語“longeur”被英語界借用,而開始廣泛地接受產生於法國,并被法國社會稱為“意識形態”的這個術語。且從此,正宗的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也和對於極權主義的討論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使得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歷史學家布拉赫教授在研究了二十世紀歐洲發生的兩次史無前例的歷史性的災難、戰亂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稱二十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這一稱謂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地接受。十年後,由於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的解體及冷戰的結束,在九十年代則被約定俗成地接受為,二十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這其實意味著的是——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說明的是同一種歷史性的政治社會問題的不同方面。
正是這個原因,二〇一八年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一書專門發行後,立即被所有的寫書評及討論這本書的作者點明——這是一本專門論述“意識形態問題”的著述。
基於這一點,在解讀奧威爾的這篇著述的開始,我要強調的是,凡是看不到《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的談的都是意識形態問題的中文學者,都可以說是對思想史完全缺乏感知及研究能力。
B.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涉及到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巨大災難的一種文化和精神心態,思維和語言方式,一種曾經幾乎席捲歐洲及世界的“意識形態”的描述及辨析的意謂上,我們可以看到,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是一篇經典性的文獻。它不僅涉及到歐洲政教分離後,即啟蒙運動和對啟蒙運動反動的羅蠻蒂科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思想史問題,而且它讓人們一眼就看到,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沒有過時,我們每天依然在面對相同的問題,相同的威脅及危險。
同樣在這個意義上,當人們回溯百年來知識界對於這個“意識形態”問題,翻譯成中文更為準確地說——“觀念學說”,“觀念思想系統”問題的研究時,熟悉這方面文獻性的人能夠立即發現:無論是在思想史領域的學術研究範圍,還是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以及文學與文學批評領域,在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及辨析的“所有的文獻”中,奧威爾的這篇著述,就其簡練、清晰、涉及範圍及深度,都幾可說是無出其右者。
這篇寫於七十八年前的文字,之所以在二〇一八年一經再次出版立即引起非常直接的反應,讓人們甚至感到,它就是針對時下的問題及情況而撰寫的文章,而這就讓它在思想史的“文獻”上稱它是一篇極為經典的文字,名實俱副。為此,我把這篇我所看到的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文獻中,最為經典的奧威爾的文字,用“意識形態”或“觀念學說”等思想史的術語來替代,解讀返原成一篇專門論述意識形態問題的文字:
——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C.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關於ideology,及翻譯成中文的“意識形態”,更清楚地直譯為“觀念論學說”,奧威爾認為,它是一種精神及心理態度,思維與語言方式。它有兩個特點:首先它認為可以把人像昆蟲一樣地,按照其認同的觀念分類、分群,并決定好壞。其次,這個群體把對群體的認同及群體的利益置於凌駕於每個個體的首位。對此,他特別強調,一切意識形態分子都只會把追逐權力及利益,作為該觀念組成的群體及黨團壓倒一切的最高追求。他眼裡只有勝利和失敗,只有弱肉強食。
奧威爾認為,有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封閉及自大心態,以及把這類觀念置於個人之上的群體認同,就也使得任何一般性交流的言語方式成為不可能,人們之間,群體之間也就無法溝通。
對於這類意識形態分子,奧威爾說,他們對於一種觀念的依從使得所謂知識分子進一步喪失了判斷和面對事實,看到事實的能力。在當代的知識領域中,這類知識人的表現讓人們看到他們:
一.被敗壞了真偽政治評論,
二.被扭曲變味的審美趣味,
三.指鹿為馬的道德錯位。
這方面知識分子最典型的代表是追隨共產主義思想、共產黨的知識分子與作家,依附於天主教等宗教的學者與文學家,以及各類沉迷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地域主義的思想及知識精英。
奧威爾說,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和族群所具有的形式,形態以及精神氣圍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還是有三點共同的性質。
其一是偏執:各類陷於意識形態、觀念學說體系的知識分子的言行思考及著述,只有他自己的思想及群體的優越及正確性。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對其意見的批評乃至与其相左。他所選擇的觀念及團體,什麼都好。而對手則一定是什麼都壞,都通向死路。
其二是不穩定、易變:由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是一種心態和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事實上並不是固定在一種觀念或由其形成的學說上的,而是在其不變的心態及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上的忠誠狂熱感讓他們可以因為有利於這種思想氣質及傾向,而能隨時轉移它運用的方式及其對象。如在過去百年中,各國的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情懷曾經不容置辯地讚美和支持的是並非自己祖國的蘇聯及中國;亦如斯大林不是俄國人,希特勒不是德國人,拿破崙不是法國人,卻各自是這三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煽動者、代表者;在歐洲很多法西斯主義者原本就是共產主義者、共產黨人;以及固執的共產黨員幾天內就會變成固執的托洛斯基分子。
奧威爾認為,不變的是意識形態性的,意識形態化的精神狀況和思維方式!而為了自己的觀念化認識,其情感及表述內容則是隨時可變的,甚至可以虛構和編造。
其三是無視現實:由於心態及精神氣質,思維模式,所有的意識形態分子,觀念主義者都一定會,因人、因對象而至“肯定”或“否定”;意識形態分子一定是——只會根據現實依附的“對象”而決定其對事實的性質的認知是肯定的還是負面、否定性的,而不會根據其事實如何,是否相似。所以,凡是意識形態分子註定了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對它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在意識形態分子的眼中、思想裡,對於不同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及其人發生的事實,可以在此處是真實的、被承認的,彼處卻是不真實的,一定要否認的;既可以看到知道,又可以熟識無賭。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團體一定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為此,奧威爾特別指出,每一種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族群,都一定會作繭自縛地深陷“歷史是可以被隨時改寫的”,以及由於這種指導思想及其結果所造成的困擾中。由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尋求的是壓倒對方,因此使得所有具有意識形態思維性質的知識分子的爭論方式及其內容,永遠陷於茶館爭論水準。每人都覺得自己是爭論的得勝者,有人甚至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沉醉於自己幻想中的對權力與征服的迷蒙中,與現實完全脫節。
對於具有上述三種性質的意識形態分子,奧威爾具體描述了他們的在言行表現上顯示的三種類型:
1.正面的肯定性的:這類意識形態分子的表現是,他們圍繞著一個實體或觀念,以正面的、肯定性的認同為其主要表現。
2.易體轉意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這類意識形態群體及分子,由於堅信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就把自己的愛徹底地轉移到那些和他們的論斷有關聯的觀念或實體上,如在拋棄白種人優越論的運動中,一切有色人種的文化傳統及存在都受到追捧;把他們的恨完全傾瀉到那些不屬於他們的觀念或實體的對象,如推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對一切不屬於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乃至販夫走卒都是充滿惡毒的、理論上的痛恨。再如反對拿起武器對抗侵略戰爭及暴政的和平主義者,甚至會為此把感情寄託轉移到希特勒與共產黨身上。
3.專注於負面否定性論斷的意識形態及其群體及分子: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來說,也會以對他們的作為最高訴求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為標準,絕對地否定及反對那些凡是對他們持有負面乃至否定、反對看法的那些群體及其觀念。為此他列舉了對於“仇英”的知識分子——凡是英國支持的就一定是壞的;對於反猶的意識形態分子,則公開及潛藏的一切罪惡都源於猶太人;這樣的情緒甚至並沒有因為二次大戰後希特勒的反猶受到徹底審判就消失,相反戰後不過是悄悄轉入地下——它在當代西方依然非常普遍地存在。這種傾向的表現也極為典型地反映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思維方式中——斯大林的一切都是錯的。事實上,就恪守馬列教條及其智力和道德要求,就思維及語言方式來說,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和斯大林及一般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區別——他們都是意識形態分子。
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奧威爾在總結了他們的特點、品質及具體存在的形式後,特別指出:它是西方社會獨有的一種心理狀態,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它不僅造就及主導統治了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產生及存在,而且在民主以及其它形式的西方社會中也普遍地存在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它們給西方社會帶來了嚴重問題乃至災難。
由於它是一種心態、精神狀態,思維及語言方式,因此,雖然它們以各類具體的觀念及實體,如民族、國家、宗教、教會、種族、膚色、地域、文化、階級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及其族群,但是,它們之中的成員卻是隨時可能改變自己的觀念及內容,而轉變成其它一種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例如法西斯主義、納粹和共產黨人之間的互相變化,托派和斯大林主義者之間,地域主義和共產黨人之間的變化,都是隨處可見。
同樣出於這種原因——意識形態是一種心態、精神狀態,思想及語言方式,一個意識形態分子可以同時也是另外一類,甚至多種意識形態的追隨者。
至於對外的區別,奧威爾在論述及辨析中則一针見血指明:馬列主義、共產黨、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理論、不是哲學及學術思想。某些地域主義、種族主義、狹隘、專斷的文化要求甚至是建立在根本就不存在的、虛構杜撰的基礎上的觀念學說。
綜上所述,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非常實際的診斷各類意識形態思想、觀念論學說及其分子的工具。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第一次作為單行本是在其發表七十三年後——二〇一八年發行的。它一經發行就立即被知識界及媒體認為,它和《動物莊園》及《一九八四》一樣,成為奧威爾一生最重要的三部書。為此,對於這三本書的寫作及三本書之間的聯繫,無論對於理解奧威爾關於廣義的作為一種心態和思維方式的符號的“民族主義”,也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的看法,還是對於整個奧威爾有關極權主義的認識以及文學貢獻的把握,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奧威爾在他寫於一九四六年的“我為何寫作”一文中說:
“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那種以為可以回避寫這些題材的意見在我看來是無稽之談。每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寫它們,無非是簡單的選擇何種立場和用什麼方式寫的問題。一個人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傾向,就越可能達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犧牲自己在美學和思想上的誠實。”(《一九八四》,孫仲旭譯,譯林出版社,2010,第6頁)
“過去全部10年裡,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創作。我的出發點總是有感於黨派偏見和不公。”(同上)
對於出版於一九四五年的《動物莊園》,他說,“《動物莊園》是第一本我寫作時對自己所做有完全清醒的認識,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書。”
關於《動物莊園》,雖然人們都看到,且奧威爾自己也在寫給伊馮娜•戴維的信中稱,《動物莊園》是一篇諷刺斯大林的故事。這個寓言反映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展到斯大林時代的歷史事件。但是,刺激他寫出這篇寓言小說的卻不只是俄國極權主義暴政的殘酷,而更多的是英國及西方知識界的對於蘇聯的歌頌氣氛及思想狀態。
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四四年二月間創作這本書,是因為當時在二次大戰中,針對另一個極權主義的德國,英國及西方盟國和蘇聯在戰爭中屬於了同一個陣營,而為此,英國的百姓和知識分子對斯大林評價很高。這一現象讓奧威爾感到十分厭惡。《動物莊園》一書的手稿在出版前的遭遇,也說明了這點,起初它被很多英美出版商拒絕。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它終於問世後,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很大的現實性的原因是因爲德國被打敗後,蘇聯立即開啟了與英國等西方民主世界直接對立的冷戰。
所以《動物莊園》,不只是針對極權主義的蘇聯國家及社會情況,而更多的是針對英國社會的知識界及民眾對於俄國的極權主義的看法及態度,英國社會的文化思想氣氛。這也就是說,奧威爾針對的是更為普遍的,在西方社會無處不在的思想方式,心態和精神狀態的問題。
正是這個針對,使得奧威爾在四五年八月出版了該書後,在十月就發表了他的《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由此可知,自一九三六年以後,奧威爾完全集中在關注極權主義問題,而這個關注又不僅是政治,而是更為普遍的思想方式、語言方式,心理和精神狀態,或者更為廣義地說——一種文化!這個文化土壤導致了西方社會的混亂及極權主義的發生與發展。
也正是這一關注,導致奧威爾由政治問題的描述——《動物莊園》,走向對於文化思想問題的文學性的探究及描述,即四年後發表的《一九八四》。所以緊接著一九四五年八月出版的《動物莊園》,十月發表的《評註民族主義》揭示的正是作為導致產生這種政治國家及其文化,並且此後作為極權主義的大洋國的文化基礎的“意識形態”問題。於一九四九年發表的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一九八四》,在《評註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全面展開,徹底地揭示了極權主義國家的文化及精神問題。
奧威爾这三部著作,對於伴隨一種政治制度的這兩個問題: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真理部文化的認識,完全超越了形式上的政治及社會領域,全面深入到西方文化在認識世界及人類精神文化上可能或者說已經出現的問題。
為此,對於這三本在奧威爾生命最後五年出版的系列性地揭示極權主義問題的書籍,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不只是政治性的諷刺性讀物,而是關注、涉及到更深刻的西方人及當代世界的精神及文化問題。
其次,這三本書顯現了奧威爾所說的,把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創作,顯示的才是作家的真正的能力。相反把藝術創作變成政治,更變成以論帶史的為政治服務,顯示的卻是作家、學者——被稱為知識分子者在知識和精神世界的無能和病態。
第三,我們看到連接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決定了其深化方向的正是《評註民族主義》一文,即它在二〇一八年重新被結集單獨出版後,知識界對他的讚揚及討論,甚至可說是追隨討論的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如果說《動物莊園》集中在對於政治事件的形成及發展上,而《一九八四》則集中在對於具體的精神及文化思想,在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中是如何被扭曲、被蛻化的。那麼,作為《評註民族主義》談到的“意識形態”問題,即可謂是理解極權主義的政治及社會的文化思想基礎的鑰匙。
意識形態不僅是導致極權主義社會建立的精神思想基礎,而且是其統治這個社會的工具。極權主義國家及其社會之所以和古往今來的其它的專制不同——有著自己獨有的文化,全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元論的觀念學說——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國家。所以,廣義說——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究其根本是他三六年以後所有工作的思想基礎。正是這篇文字所涉及的“意識形態”問題,形成了《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構成其所有思想的基礎。狹義說——意識形態問題是他在《一九八四》中詳細論述的新話、新思維的描述框架。
為此,回顧奧威爾一九三六年以後的全部工作——圍繞極權主義問題的描述及辨析,以及他在英國的精神和知識經歷,寫作這篇《評註民族主義》的動機,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不僅是理解及把握大洋國-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問題的思想基礎,而且更是清楚地認識一般社會中的知識人的精神、心態及思維和語言方式所存在的問題的鑰匙。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A.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除了核心的意識形態問題,另外一個獨屬於奧威爾的問題是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
在這篇總共不到八千個英文單詞的文章中,奧威爾竟然有二十五次直接提到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並且都是很具體的批評性的描述及解釋。
由於長期以來關於西學、西方帶來的文化及其知識分子問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混亂,因此奧威爾在這篇文章談到的他對於當代西方知識分子群體的具體認識,對於他們的思想以及社會影響的揭示,對中文讀者可說是具有教科書般的意義。
關於知識分子,奧威爾認為,受意識形態問題最大影響,並且在意識形態問題的傳播及運用中,在政治及文化上產生最壞影響的是“知識分子”。
如前所述,奧威爾在不止一處坦率地承認,他之所以寫出《動物莊園》以及《評註民族主義》等文,完全是因為英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個問題上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的著述對抗的對象就是這類知識分子及其思想。而這就讓我們看到、想到,知識分子在西方,以及在奧威爾這類自由主義知識人那裡究竟意謂著什麼?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角色或位置是什麼?從事知識和精神工作的人,應該有哪些規範和義務責任?以及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這些問題實際上也是世紀性的問題,因此在上個世紀初期,與奧威爾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具有不同傾向的很多歐洲知識分子也都直接或間接地關注及討論過,如馬克斯•韋伯、弗格林等。
B.奧威爾之所以在一九四五年還非常迫切地感到必須直接對抗某些知識分子及其思想,一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要求了作為知識分子所不應該要求的位置及作用,二是因為他們運用了不符合以知識和精神為職業的人應有的職業要求及方法,第三則是這類所謂知識分子嚴重地擾亂了其所生活的社會正常的精神及社會秩序,為社會及個人帶來了惡劣影響甚至災難。
由此,奧威爾讓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三個問題上兩類知識分子的對立,而這個對立顯示的是——文藝復興及其帶來的啟蒙運動後引起的“復興的古希臘的知識傳統”,與中世紀前佔據社會主體位置的“宗教秩序及其心態和方法”遺留下來的教會教條式的所謂知識人的對於知識分子職業作用的不同認識以及對抗。
例如在第一個問題上,在古希臘的思想傳統中,哲學家、知識精英只有對其應該對知識採取什麼態度,以什麼方式探究論說的要求,而沒有對於社會位置乃至真理的要求。這一點在古羅馬後的基督教社會中,不必說教會,他們直接要求的就是他們代表了神和真理,就是一般知識人首要考慮的也是其學說及思想和神及真理的關係。而這一傾向直接遺傳到近代世俗社會的世俗知識界。故此可知,某類知識人,那些意識形態分子,提出的所謂“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代表了良知”,“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以及“知識分子的啟蒙責任”,都是這一宗教精神及其文化思想的變體。
對此,直接返回希臘傳統的認識是,知識分子是以知識為職業的一類人。他們的好壞、是否有積極作用完全取決於他們所能夠貢獻出的知識的質量及效用,其清晰性及可證性。而這一切又由其使用的“方法”——對方法的認識及把握程度所決定。至於這類知識人多呈現的工作與價值與真理問題的關係,即如韋伯所說——完全無關。價值和真理的認識,完全屬於知識分子個人的事情,不過是他自己在進入工作前的一種純屬私人氣質的假設。
為此,在第二個問題上,對於知識研究問題的規範及方法的把握及認識就可以進入到具體、專業性的要求,在一個共同的規則下比較和進行。而這就是近代學術有著自己的學術要求,其思想根源在古希臘;二百年來為何會對於形而上學及玄學進行過不斷地辨析,以及何以波普稱黑格爾、哈貝馬斯說的是黑話,為什麼弗格林、阿隆一再說,和意識形態分子完全無法討論。
C.奧威爾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以及他在這篇文字中從始至終針對的都是知識分子,以及奧威爾一九三六年後針對極權主義的工作,究其實讓我們直接清醒地看到的是: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
而這就顛覆了我們另外一個觀念——知識分子的對手是專制政治。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是以知識為職業,而不是以政治,當然就更不是為政治及權力服務。知識分子之所以必須對抗專制,其實不是必須,而是不得已。因為專制,尤其是徹底地把統治深入到文化及精神,且有其自己的所謂文化的極權主義專制絕對性地封閉了任何對於知識研究的可能。所以極權主義國家從根本上說——沒有“知識”分子,只有意識形態分子!這個社會的所謂知識人如果想要以“知識”為職業,其前提就是必須反對或反叛其意思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要求,反抗及反叛極權主義社會。而與之相對,對於一般專制社會,如果它不幹涉知識及文化問題,知識分子還是有存在的可能。在某些時期,甚至會有部分知識分子因為其社會的需要和平安定而暫時地支持專制形式,這都無可否非。如二次大戰初期,五十年代中期後,歐洲國家都出現過知識精英建議,為行政權力有效、迅速,國家暫時實行權力集中的威權政府;再如暫時實施的“戒嚴”及“戰時法”。然而,就知識分子的一般定義來說,在一個民主,或者說帶有部分民主性質的社會中,在校園及研究機構推崇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卻是犯了大忌,我們說這類知識人是“最惡質”的知識分子——絕不為過!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啟蒙及啟蒙運動——啟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由上所述,我們看到,在現代社會乃至在古希臘的知識人所從事的不是政治,而是知識問題,專制政權及制度不是知識人及其知識生活直接針對的對象,知識人活動的對象及內容是知識,知識分子的對手首先且最根本上是知識分子。而這就讓我們在思想史問題上看到,啟蒙的對象絕非是意識形態分子所妄斷的——受教育低的民眾,相反,啟蒙的對象永遠是知識問題及知識分子。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奧威爾的這篇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發表的時候沒有被廣泛地認識到,那麼在七十三年後的重新成冊、獨立發表,則首先讓人們不約而同地看到的就是——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是反啟蒙的產物。
奧威爾這篇文字的這一思想意義,二〇二〇年第一次出版的德文版的奧威爾的《論民族主義》,納塞伊教授在後記中反復強調了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產生及克服和啟蒙的關係。
這意味著,各種類型的馬列主義及其分子,各類地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以意識形態為綱領的政黨,是最沒有資格談論啟蒙問題的個人及群體。
為此,這就讓人們看到,近百年來在中國大陸乃至港臺中文媒體及所謂學術刊物上的各類有關啟蒙的討論——荒腔走板。奧威爾的這篇文字可以讓人們很具體地看到:作為典型的意識形態分子——無論李澤厚還是推崇所謂“科學和民主”的我的某些馬列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導師們,所談論的啟蒙,由於認識論方法論沒有任何觸動及改變,都可謂是妄說!他們對於各類具體的概念及思想史問題的看法,逐字逐句地顯現了奧威爾所談到的意識形態分子們具有的所有最典型的反啟蒙的特點。
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這種特點,奧威爾在這篇文字中指出,化解及克服意識形態,讓意識形態分子走出來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上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努力進行自我反省——認識到自己的認識及方法的界限。
對此,奧威爾說,意識形態分子能否做到這點涉及的不僅是思想,而且更有道德問題。他們必須在道德問題上也做出努力——必須誠實地、公平地對己對人都一樣地面對一切事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意謂著,無論是在認識論方法論上,還是在道德上,所謂知識人,尤其是曾經的意識形態分子,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一切,進行自我批評及反省,絕對不能繼續誇大自己的想法及要求,繼續以意識形態式的方法把啟蒙作為旗幟揮舞。
對於染有意識形態傾向的人——首要的是自我批評、自我啟蒙。
綜上所述,對於人們關注的知識分子問題。奧威爾提出極為明確的看法。他認為:
知識分子不僅是受這類思想影響最大的群體,而且甚至是直接助長了這種性質的思想的蔓延,加劇了這種傾向在社會中的負面作用。
其次他直接指出,知識分子所主導的這一傾向的本質是反啟蒙,對抗啟蒙。而這一切涉及到知識分子的道德。這類知識人,由於意識形態化而使得他們在道德上產生了嚴重問題,喪盡知識分子的顏面。
而這就讓我們看到:
啟蒙的對象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社會的良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要求這一地位,只能盡可能誠實地要求自己尊重、遵守普適的道德規範;從根本上說,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自己,反省審視的是自己知識的性質和道德。因為他們的專業內容不是政治及其權力,而是知識及對知識和事實的態度。
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及認識,思想史讓我們看到: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問題及談論知識及精神問題的各類分子!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A.對於一個生長在中文社會中的讀者,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幾乎是逐句逐字地擊中中文知識界、學界的各方面問題。
具體對比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中列舉的具體的案例,中文世界可謂五毒俱全,在所有的各類情況中,都不僅典型,而且極端地顯現了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特點。其中,中國大陸和臺灣堪稱為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問題在極權主義社會,及在一般所謂民主社會的模板。這也就是說,關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及黨團問題,大陸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臺灣民進黨及時下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生活的氛圍,分別為理解和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提供了其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最好的教科書式的驗證案例。
而對於香港,由於地位特殊,文化社會歷史特殊則不僅顯示了大陸和臺灣的雙重特點,而且居然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所有各類只有英國人,白種民族才會有的要求及主張,如奧威爾文中提到的英國的“新保守主義”——所有英國的都是好的,在所謂“港獨分子”身上都匪夷所思地更為變態、堂而皇之地絕對化張揚出來。
當然這其實不過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大陸的意識形態分子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論”的翻版而已。而這類傾向在百年來放洋到歐美的華人及其學者們身上同樣存在——奧威爾文中提到天主教主義及其知識分子作家的表現,用在華人及其學者身上,都甚至變成放大及扭曲的卡通版。
B.那麼,為什麼當代中文社會,無論海內還是海外,都如此容易地受到各類意識形態感染,并且迅速擴張及意識形態化?
從文化及社會的角度看,本來位於歐洲之外的東方的中國社會有著先天的免疫力。因為他們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化遺傳基因。明確地說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基因,由於產生它的形而上學前提——天人合一,以及演繹其文化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是陰陽五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存;而與西方的二元論的認識論、知識論,以及其極端化的一元論的一神論根本不同,因此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形成這種“意識形態”的基因符號及其基因排列,即沒有帶有一神論基督教性質的觀念學說的成因,所以本身的文化符號及其實質帶有先天的免疫力。
對於百年前他們所不得不面臨的大規模全面地湧向世界各地的“西方文化”,這個文化自帶文藝復興激發出來的,對於過去的宗教性的、整體性的一元論專斷教條思維的“免疫體”,即如奧威爾等知識人所繼承延續的思想關注、文化努力。
本來這樣“兩種因素”——天生的免疫力及後來的免疫體,應該給中國,或者廣義說中文社會帶來足夠的對於意識形態——觀念論學說傳染蔓延的免疫能力。但是歷史發展由於偶然,上代,五四後兩代知識人的偏頗,發展並非如此。
發生於一百年前的所謂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主要引入的不是文藝復興後的,對於西方來說復興的古典的古希臘文化,新興的啟蒙主義潮流,卻更多的是屬於中世紀基督教社會性質的經院學術,宗教性的文化。
這樣的情況當然和文化及語言的隔絕,以及不同的思維及表達方式,不同規範不可直接通約,難以溝通有關。因為這一切,先天地造成使用中文思維的華人對於西方的知識論以及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把握和理解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性質的簡單化,尤其是不用動腦的各類“附會”——牽合附會、尋聲附會、穿鑿乃至假借附會……,讓尚無西式研究能力的第一代放洋的學者,如胡適們淺嘗輒止地引入西學。放洋兩三年不過咿呀說幾句洋文,居然就可橫掃窮經皓首的學人。而這類引入最廉價的就是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的開始所說的,利用觀念或實體的學說作為分類的標籤來對於思想、人群乃至社會及文化進行分類,並且作為評斷好壞的標準。
所以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引入的是西方極端化的“舊文化”心態、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囂張地長驅直入的是極為典型的各類意識形態——如伴隨炮聲而進入的馬克思主義。
五四後的中國社會的思想潮流,實際上不是具有探討、辨析,認識論知識論性質的思想運動、啟蒙運動,而是一場非黑即白的標籤運動。貼標籤式的所謂“研究方式”一瀉千里地統治了華人社會的文化及思想,且一統就是百年,一統就是徹頭徹尾。“附會”,為各類意識形態的進入提供了最好的條件,而意識形態的全面進入又讓“附會”獲得了其對於所謂西方文化的了解的似是而非的合法性認證。
對此,余英時和林毓生先生則可謂是離我們最近一代的五四後引入的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其對西方學術研究中的概念的理解方式,不是知識性的,認識論及方法論的辨析,而是教條性的、“附會”式的;其由此而來所謂研究方法,不是構成性的、理論式的描述框架形成的系統的描述,而是以拾到了的西方觀念,硬行運用、重置中國文化的論斷、以論帶史的史觀,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甚至把這類思辨方式應用到對於中國文化原材料的處理及運用上。現在,對於兩種方式的治學的根本性的區別,對照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楚地看到,五四以來的,余先生和林先生所繼承的治學方式,堪稱是奧威爾所說的“意識形態式的分類法”,“貼標籤法”,以及陳寅恪先生所言的“附會”治學的實例。
今天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正是這一背景造成——二〇一八年在英國及歐洲重新出版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在歐洲及西方世界引起相當的關注及討論,但是在中文界卻幾乎毫無影響,尤其是涉及到對於根本性的近代西方問題,他們幾乎全然沒有與西人學者類似性質的關注。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喪失感知能力,比無知更危險!
2023.9.11 德國•埃森 初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