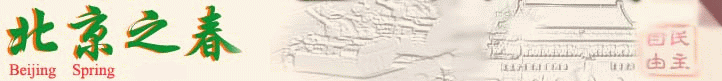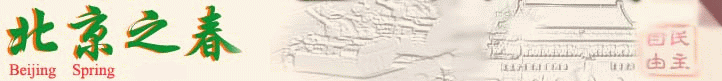臺灣經濟發展方向
張萬同
臺灣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兩岸關係,另外一個是經濟發展。這兩個問題不解決,臺灣很難有出路。其他問題都較次要。兩岸關係為臺灣帶來外交上的限制,而經濟發展停滯導致島內生產與資源累積帶來很大的危機。
而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經濟與政治完全脫不了關係。政治就是法規及制度的制定者,政府擁有國家大部分的資源,最重要的是控制了貨幣的發行,另外國土規劃及稅收的運用,都嚴重影響到私人企業的商業行為。因此政府的一舉一動對大企業影響甚頗,早期經濟是屬於倫理學的一部分,後來發展成為政治經濟學。
到二次大戰過後,在美國開始被稱作經濟學,表面上是脫離政治,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在經濟學上還是很重要的一環。臺灣過去在兩蔣時代的經濟發展頗成功,之後就逐步下滑,原地踏步並且開始落後於世界各國,包括東南亞國家,我們原本是遠遠超過他們的,現在開始要跟他們並駕齊驅了。
談經濟發展,政府在國土規劃上有一個很大的責任。第一步就是奠定經濟基礎的倫理關係。倫理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相處上的關係。現代經濟是大家共同努力、分工合作的社會。馬雲說過:一個人抵不過一個團隊、一個團隊抵不過一個平臺的制度、一個制度抵不過一個趨勢。
分工合作即由倫理關係主導,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團體內部優先順序及主從關係和比例原則又是一門學問。假如在這些方面大家有共識的話,運作起來即非常順暢,因為沒有很多的摩擦。但當彼此之間沒有共識,摩擦很嚴重的話,那就會像現在的臺灣一樣,做什麼都動輒得咎,抗議聲連起。任何一個政策都會有人反對,因為沒有一個政策是讓人滿意的,也就是說天底下沒有一個完美的政策可以讓所有人都舉手贊成,因為在人間本來就沒有完美的這回事。
所以大學就講,「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事有輕重緩急,不能夠本末倒置,捨本逐末,更不能因小失大。所以主從關係就是倫理關係,雖然不滿意,但是如果執行會顧及全局,對全體更好,那就應該去執行。
以團體關係舉例,團體將來如何更好,這是倫理學上非常重要的議題。亞當.斯密在倫理學的奠定上,伴有舉足輕重的角色。社會如何相處才有生產力出來——經濟學因為科學化的關係窄化了倫理學,變成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不講倫理,因此現在的經濟學非常狹小,導致許多問題無法解決,所以現在經濟有很嚴重的問題,但是甚至連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因為失去了宏觀。
所以「倫理」和「思維模式」是政府第一個要樹立的要件。你到底怎麼想、依循的基準在哪,這些基本的思維要有,孔子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些基本的思維要有。每一個國家、團體都有不同的思維模式,天無絕人之路,每個團體都有生存發展的空間,只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樣的發展方式,反而要依據不同的思維模式和環境來做不同的策略。可以互助、也可以參考,但絕對無法模仿,要能夠活學活用。我們的歷史文化、倫理很重要,地理環境也很重要。中國人講:「天時地利人合」,有了這些,第二步我們就有戰略計畫。
發展策略也必須要有前瞻性,因為所有的計畫不是為了現在而是為了未來。前瞻性其中必須符合經濟原理,包括如何創造經濟價值。政府的責任,是要製造一個好的環境,像公司的董事長,負責製造好的環境讓員工有努力奮鬥的動力。董事長引導的方向會影響整間公司的運作,同事之間的氣氛,能夠讓員工自由發揮就是好的環境,因此公司就更容易有好的發展。反之,如果董事長不懂的佈局和提供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不會提供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的話,底下的員工雖然很努力也卻覺得力不從心、白忙一場。
中國人的理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每一個都是一個小宇宙,自己對自己是一個小宇宙,家庭對個人又是另外一層的宇宙。那國家對家庭又是更高一層的宇宙。一層比一層大,國家在最上層。國家主要的責任是如何讓以下的每一層有好的發展。因此,國家該如何佈局、什麼樣的戰略思考,如何發揮動態利益及在國際間如何有好的生存空間,這是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而非管理國內的事務。公司內部事務是給總經理在管的;公司外部事務是給董事長在管的。就像我們以前的憲法規定得很好,總統管外交和軍事,行政院長是管對內的。就像我們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內一樣。總會有一個管家管外面,那如果你是一個女強人的話,你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內。一個單位很難有兩個太陽,因為如果兩個人都要主內、兩個人都要主外的話,很容易發生鬥爭。因此國家就很難發展,一個人不是完美、不是全能的,所以你主外的人就很難主內,也沒有時間主內,那主內的人也沒有時間去主外。所以分工合作是一個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原理。不能夠一腳踢、一手包,什麼都一個人獨佔、獨絕。這就是中國人以前講的獨夫。寡人獨夫,這種政治經濟一定不會好的,因為一個人抵不過一個團隊;一個團隊抵不過一個制度,這個制度是外在條件所提供的制度。
以臺灣作為國家為例子,國際規範就是我們的制度,一個國家在怎麼玩也沒有辦法跑到國際規範這個限制外,一個公司再怎麼跳,也沒辦法跳脫國家的規範。一個人再如何頑皮也無法跳脫家規;每一層都有一個次序、有從更上一層來的規範,很滑順的運作,這就是宇宙的次序和運作。那設計制度規範必須要有永續性,就是知道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我們的發展是為了未來的生活,尤其是子孫的未來比我們現在的發展還更重要。
因為我們希望永續發展的話,就必須要靠子孫。我們現在就把所有的資源吃光、用光,然後汙染了整個環境,留給後代爛攤子,那就不可能永續發展,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是一個短命國家。人類的理想是希望可以永傳萬代的,所以慎終追遠才可終後。慎終就是對未來終結的時候,留給後世什麼東西。追遠就是:我從哪裡來?我的祖先是如何過來的,我要感謝誰?以前的人犯了什麼過錯,我要如何改進?
老實講,孔老夫子和老子這兩位聖賢所講的哲學道理,完全可以套用在經濟上,並且可以解決經濟問題。這是戰略性思考的方式,那以臺灣來說,現在我們的天時受制於兩岸關係,天時就是國際,還有極端氣候、資源的浩劫以及汙染問題。地利就是本地在地的資源。我們的在地資源幾乎是零,只有一群勤奮的人民,還有良好的文化素養。
因為老百姓相對來講是比較忠厚老實,受到中華文化的洗禮沒有斷續過。因為蔣介石當時到臺灣來,一直以道統傳人自居,不敢像毛澤東這樣打倒孔家店,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因此臺灣在儒家、道家方面有歷史上豐厚的傳承,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延續。所以人民的文化素質在全世界來講算是領頭羊的地位,這就是人合的部分。所以如何利用現在的資源環境來發揮臺灣,這就需要智慧。
解決問題的話有三種策略,第一種策略是最笨的策略,跟著人家跑、跟別人硬碰硬,那沒有任何的創新,只會看別人怎麼做就說 me too,然後來對幹、競爭。在政治外交上,別人講一句你就回一句,賭氣式的英雄好漢,輸人不輸陣的方式,這是最低層次的溝通方式,動物性的、直覺性的反抗,或是說對幹、比大小,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是最困難的,因為常常小問題會變成大問題。
我們看很多離婚的家庭、或是好朋友做了幾十年,突然因為幾句話,兩邊就都絕交了,大部分都是因為一個小的問題因為兩邊都不肯退讓,到最後變成尖端放電,爆炸,然後就不碰面了。過去所有的恩德一筆勾銷,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現在臺灣這邊絕大部分的同胞除了原住民以外,基本上都是從大陸過來的,那如果要否認我們跟大陸血統的關係,說我們不是大陸人,這就有點比例原則不合,就因為一時的賭氣,斷裂了幾千年的連貫,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動物、直覺性的,不是人類——萬物之靈的作法。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很難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越來越惡化。
第二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碰到問題不直接對抗、反而繞著圈子從周圍的小問題開始解決,然後最後再來解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求同存異,任何中間有不同的見解,或是不同的意見、相衝突的問題發生的時候,其實不是百分之百地在各方面上都不能相容,而是在某些核心上不能相容,但是周邊還是有共同的一個想法,所以你看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又戰又合、又鬥又合,連北朝鮮跟南朝鮮一樣,一邊鬥又一邊可以談。就是在某些事情上面無法讓步,在某些事上可以談,慢慢緩和氣氛,然後最後來解決最主要的問題。或是讓時間化解,或著用智慧,或用什麼樣的利益交換來給彼此臺階下,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比較有氣度、聰明的方式。這個比較像是大國中間在玩的方式,如何解決問題。
第三種就是最高層問題的解決方式。我們碰到問題,不談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是什麼,而是最深層的知道這個問題本身最根源的什麼,就是起心動念為什麼會變成問題。然後我們把思想層次拉高,從更高層往下看,告訴他說你想過的問題我都想過了。只是在更大高層次環節裡面的一個小問題,所以就把它化掉了。所以問題變成不重要的問題,大家變成可以共同努力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就像是我們兩邊在軍事對抗,他出動陸軍的話,我就出動空軍;他出動空軍的話,我就出動太空軍。所以拉高層次的人自然就變成領導人,因為他看得比較廣、比較遠。所以變成對方就要跟著他走,因為他變領導人。就像愛因斯坦看到的是宇宙物理;牛頓看到的是地球物理,所以當愛因斯坦一出來的時候,牛頓就變成愛因斯坦的學生了,他就跟著愛因斯坦走,因為他所講的是地球的物理,不是宇宙的物理。牛頓看到最多的是四度空間,那愛因斯坦看到得遠遠超過四度空間。所以當你看的範疇越小,當別人範疇更遠的時候,你就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所以最高層次的,我們中國人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春秋左氏傳魯襄公二十四年) 」
太上立德:全世界最被尊崇的三位——孔子、釋迦摩尼與耶穌。他們既沒有社經地位也沒有財產。就算有財產他們也不需要了,因為他們以德服人,到了天地人的境界,與天地同光這種境界。我們一般人講的是求生存,但是他已經講到整個宇宙創始者的境界。境界差很多,自然我們就只有崇拜、聽他的。境界不能比他高,就被他帶領。所以兩岸問題其實也是一樣的,我們跟他玩武力對抗、兩敗俱傷;跟他玩經濟對抗也是一樣,也是彼此互相傷害,傷害半天都是自家人、都是同樣的祖宗,就像是猶太人跟阿拉伯人互相傷害,其實最早他們都是同一個祖先。誰也沒好處。這是有些愚蠢的方式。
所以孔子說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智者就拉高層次,大的把它當大水牛,人雖然沒有比水牛體積大,人有智慧、有文化,只要在水牛鼻子上套一個環,帶著他走,給他吃喝,他就跟著你走了。我們應該把大陸當作大水牛、臺灣當作小牧童,你這樣就有智慧了,很自然的,水牛不會跟你鬥。
那如何自然?率性之謂道,人的自然、人的本質都是從愛出發,都怕失掉這個、那個。當我們的層次拉高到天地人的層次,以千萬年的角度來看,這個時候兩岸關係很自然能夠解決。那我的主張是大家認祖歸宗,誰是祖先代表?就是我們的道統。從黃帝唐虞夏商周開始,整個中華文化的根基回歸到零,以祖先的祖訓為標準,誰都不說話,聽祖先的家訓,這樣的話十四億的中國人都同意,也都不會有危機了。如果我們誠心誠意按照祖先的祖訓去做事,誠心誠意修齊治平,自然中國一定強大,可以去領導世界。
所以兩岸關係不要去搞統獨,我覺得那些都沒有意義。因為那些都是動物性的直覺要搶佔資源,並沒有意義,搶地盤硬幹只會兩敗俱傷,讓其他民族的人看笑話,家醜外揚。當初我在讀書的時候,一九七〇年代,在費城(Upenn)讀書的時候,我們臺灣的少棒非常厲害,每次到威廉波特打的時候都拿冠軍,但是拿冠軍以後就開始,一邊拿中華民國的國旗、一邊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互相打,兩個都是臺灣去的留學生,那個時候沒有大陸去的留學生,就是說兩個都是臺灣教育出來的,可是一個回歸祖國、一個是忠黨愛國。兩個就拿兩邊的國旗在那邊對打,幾乎每年都上這種戲碼,我在旁邊看了都覺得很丟人,外國人看著笑。你們兩個都是臺灣來的卻在那邊對打,大家來為你們臺灣的少棒加油,結果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慢慢沒有了,那時候就變成臺獨了。
很奇怪臺灣人在外頭,反國民黨就變成回歸祖國,很少聽到臺獨。我那時候去參加臺灣同鄉會也沒有聽過臺獨。但是到八〇年代開始臺灣人有錢了,那時候臺獨就出來了。大家眼光高,成大爺了。那以後臺灣人就不會再搞內部鬥爭了。所以我們現在兩岸之間,對祖先是非常丟人的,在鬧笑話。說實話中華民國按照事實,我們都是孫中山革命出來的兩個小孩,思想精神的兒女,中華民國一九一二年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誕生,我們比他早了卅八年。臺灣是大哥,今天弟弟發財了,不認哥哥,要跟哥說你不存在,這有點妙。
用錢財跟暴力來違反祖訓,祖訓講德不講大。連孫子都說:「兵者休也」,動武不是為了搶奪資源,而是保護弱勢。不是要國家疆土大,國家疆土大只會造成未來別人的報仇。我們總有懦弱的時候,天地是有循環的,每個國家都一樣,不可能每個國家都強大,總會有好運、壞運。別人不可能永久都是你的俘虜,不可能的。天下為公,大家都有好日子過,輪流來,產業輪轉,跟股票概念一樣,股票總會輪漲,大家都要活,這是老天爺的智慧,我們是動態平衡,不是靜態。
所以我們要有從千古來看的胸襟,看得越大,智慧越高。所以兩岸問題,我認為我們應該藉著對祖訓——儒釋道的文化虔誠,而想盡辦法發揮到現實生活裏面,這是我們的功課。我們祖先他們的生存環境是在古時候沒有科技,是農業社會和君王社會的狀態。現在我們變成後工業時代,民主高生產力,高學歷,這種社會形態下,如何把我們原本祖先的思想原則和哲理運用到現代化的生活制度裡面。因為天不變、道不變,祖先指的道路一定有他的原則,這不會變的。幾十億年,每天太陽都在那裏,他不會變的,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特有的長處發揮。
這就是我們講比較經濟學,大家在講要怎麼合作,互相比較利益來合作,就連孔子也說自己要向農夫來學習,雖然他是聖人,但是在這方面他還是不懂,輸給農夫。所以我們必須承認自己什麼是不足的,不要逞強。要謙卑,要中性,要吾日三生省吾身,不要會幾個字就上谷歌道聽塗說,亂講話。講完講錯又不認帳,把面子放在第一,那國家和個人都沒有希望了,要實事求是。
鄧小平講:「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能夠給人民好生活就是好制度,所以意識形態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把人作的辛勞放在心裡的監牢,放在意識型態裏面就什麼都不能動了。自閉症就失掉了靈活性、失掉了巧妙,整個就僵化了,僵化就是死亡的前兆。人要死之前一定會先僵化,國家也一樣,一僵化就要死了。所以我覺得臺灣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祖歸宗,發揮祖訓,把蔣經國講的三民主義的模範活出來。
我們不是跟他比大小、比誰有錢、比誰兇悍、比誰更自主獨立,一個國家沒有辦法自主獨立,都需要和鄰國互相合作、互相忍讓為了整體的利益。所以每個人不是在魯賓遜的荒島上,一個人就可以,大家都是在互助合作的環境裡面,有拿有給,有進有退的社會。
所以我想兩岸問題能夠解決,我們很多在外交上環境的僵局就一定能打開。因為臺灣是小島,要做生意一定要靠國際市場,不是靠臺灣市場,只有一成是臺灣市場,如果只剩下臺灣市場的話,九成就不見了,你可以想像一轉眼九成收入不見的話會怎麼樣嗎?如果資產當中九成不見了的話,我們會回到什麼樣的一個社會程度?我們所有的資源、能源、材料都是靠外國進口。我們很多的關鍵零組件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尤其現在全球化趨勢下,將來更是國際間彼此分工,我們是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一環,所以當我們跟國際產業一斷掉的話,幾乎我們所有電子業的廠商:鴻海、臺積電幾乎全部關門。
所以我們受不了這種打擊就必須要交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和發展的空間。那假使我們無法做到這個,那臺灣的經濟策略要如何發展都很有限,因為那是整個大環境的限制,所以蔡英文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大環境準備好讓民間企業有發展的空間,那你把大環境縮小了,臺灣的企業就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慢慢地衰弱,第二就趕快跑,跑到外面不做你的子民了,只有這兩種方法,否則他就等死,因為生意願來越難做。
就像一間公司,董事長負責外界的資源,他要去交朋友、要去拉關係、負責找資源。負責人為什麼聽董事長的話,因為他把資源找到公司來好做。這個做外在環境的永遠最大。總經理只管內部的運作,所以董事長一走了總經理也沒辦法做了,因為他沒有資源,巧婦難為無米炊。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概念才能講經濟策略,否則空談,自己講自己的。
兩岸關係假如往這個方向走,那我們經濟該走什麼?大陸在各方面慢慢取代我們的優勢,我們一直是製造王國,在世界上,臺灣最厲害的就是會大量製造、做成本管控。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到美國去,我看到在國外商品的現象就很清楚,有韓國的同學也有日本的同學,只要臺灣的企業進入某個產品的生產線,韓國的供應商也慢慢撤退了,因為他比不過臺灣,不要說日本,日本更沒有辦法和臺灣競爭,所以他只能往提高技術層次方面走。
同樣的技術層次或是差不多技術層次的市場都會被臺灣給搶過來,因為臺灣在成本管控和大量製造上非常厲害,我們會低價競爭,另外我們的人民很勤奮,臺灣的工作環境、地理溫度也很適合,因為土地不大,所以資訊和零組件的交流非常快速。不像美國,美國汽車產業為什麼會垮下來,因為他太大了,福特汽車廠或是通用汽車廠要在美國設立的話,很多零組件公司近的距離幾百公里,遠的要上千公里,運輸上有麻煩困難,一下下雪、一下龍捲風,他的環境不像臺灣那麼友善,臺灣的溫度適中,頂多下下雨,來個颱風,交通很少產生嚴重堵塞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有很多的存貨,但是當他存貨多的時候就壓資金,就鬥不過日本人。日本地方小,所以他的零件廠供應豐田非常方便,臺灣更小就更方便,零組件幾乎無庫存,我要就馬上叫,只要前面一兩天跟他講,供應商就馬上製作,現做現賣,好像掛著的現宰羊一樣,所以成本就下來了。
韓國比我們地理環境差一點,他比我們大,也會下雪。所以臺商往深圳、崑山走,因為那邊比較不下雪。臺灣離海邊最遠也不到一百公里,很容易就出去,臺灣有一個天然的便利交通環境,到處都可以出海,海運是一個最重要的大量運輸。臺灣地理位置是亞太的中心,距離東南亞和東北亞都很近,所以快速連結、互相合作。臺灣到各個地方都很方便,人民勤奮、態度友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能吸引外面人的地方。
臺灣的人情味跟勤奮是吸引世界的一個利基。所以當初消費者基金會問我臺灣要不要往機器人的方面發展?我說機器人發展可以但是不要學美國的那種方式,學日本、美國、大陸馬上這個人情味就沒有了。我們臺灣一定要 human touch,有錢的人要人來服務他,不要機器來服務,因為再智慧的機器,也都沒有生命,沒有人情味,也不有趣。
一個有身分地位的人就是有一堆的人來服侍他,我們現在不要算人的服侍的話,我們現在的生活比皇帝還舒服,可是皇帝的生活還是比我們生活舒服,因為他一聲百應,這種氣勢就很爽,有錢的人就叫做大爺,品牌就是和大爺的聯繫,我是跟皇室貴族在一起的,其他都不叫做品牌,當大家都用機器人,我們就要用 human touch。我們要吸引各地方的年輕人,做最好、最溫柔的服務給你。這個就是臺灣的利基。
臺灣的醫療業和觀光業可以帶動,人來了給他 human touch,做高層次、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臺灣最寶貴的資源就是我們的好山好水,不要破壞自然環境。以瑞士舉例,以生產性來講,瑞士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他在非常深山的內陸,而且地無三里平,都是山,沒有自然資源、小國寡民。但是他的人均所得是全世界前十名,因為瑞士在觀光農場上發展出特色,再以細小的品牌賣出手工藝錢。他的價位都非常的高,但是很多人願意去,因為有品味,他有歐洲的品味。
我們要有中華文化的品味,故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為什麼不把故宮連結到生活所有高檔品牌呢?因為那就是王宮貴族在用的啊。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歷史跟文化連結,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中華文化五千年的傳承。
我們不需要服務大眾,我們需要服務小眾市場,服務業要走小眾市場、觀光市場,我們的觀光要服務高檔客戶,一年有八百萬進來就不得了。人多,就會破壞環境,那當然我們需不需要科技?當然需要科技,那我們在發展產業之前,政府必須知道他的工作除了擴展國際市場和國際關係以外,要引進國際人才進來。
第二個,國內要建設、國內的交通網要很好。因為所有的經濟要靠交通,交通是一個基礎建設。現在的交通比以前複雜很多,他不光是一個實體交通,我們以前講的交通是高速路、高鐵、飛機,把人運過來叫做交通,但是我們下一世代工業革命的交通是虛擬交通、就是網路交通、數據化交通。不需要業務跑、商品跑就可以賺錢了,這就是物聯網。
我們的房子、汽車聯網、冰箱聯網、冷氣機聯網,所有我們看到的東西都可以做互聯網,跟科技結合,人物連在一起,這就叫做智慧未來、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慧醫療。第二個一定要大數據化,一對一或一對多,冰箱一連線工廠,就馬上自動叫貨進來,這就叫做智慧化。他有很多人工智慧在裏頭,感應器知道外面的環境怎麼變。這樣的模式會增加很多的交易量,交通最重要的是互通有無、貨暢其流,當你沒有這個的時候,你就會落伍,成為孤島。
因為先進國家都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那整個是高效率的交通,比實體的交通高效率百倍以上,也不用浪費很多能源、資源。因為你天天在路上跑,能源資源浪費很多,所以未來對於能源的需求會越來越小,所有的燈和能源都是智慧的。以挪威舉例,他所有的馬路都有路燈,但是他不是像我們現在的路燈,一開從晚上七點開到早上七點浪費電,有的時候根本沒有人,路燈也照開,挪威的路燈有感應器,當你車子要進入這個區域,燈就亮了,一段路亮一個燈,當車子一走,他就黑了。跟樓梯間的感應燈是一樣的,因為燈的功能只是照明,當沒有人的時候他不需要浪費這個能源。所以這樣的話,馬上節省七成到八成的能源,那你用太陽能下來就很方便了。
我們不需要開很多的電廠、燒天然氣、油等等,要挖地熱也不是好事,你一直在地上打洞絕對不是好事情,跟挖礦是一樣的,我們的地殼其實是很薄的,也只有卅公里而已,沒有多深,你如果鑽超過卅五公里會有岩漿,海底打油也是很傷地皮的,為了一時的財富,子孫怎麼活?這不叫經濟發展,這叫遺禍子孫,現在吃光喝光,子孫無法活。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都不是好的領導人。
臺灣假如在環保能夠做好的話,他是一個美麗的島,叫做福爾摩莎。所以臺灣在基礎建設上做好重要的前瞻性,不是做輕軌而是做網路,要發展數據化聯網、要發展人工智慧、要發展很多的感應系統,讓將來的無人車可以走,無人車出來以後,我相信整個汽車的數量可以減少到不到一半,因為大家不要有車了。無人車在你旁邊,嘴巴一講,車子就來,馬上就自己開到你家門口。也不需要停車場,因為車子永遠在路上跑,我們的交通馬上就順暢了,我們省下來的土地可以讓我們的老百姓居住更舒服,也不用蓋那麼多的馬路,這麼多的高速路,永遠不夠,永遠塞車。
我說汽車比人還大,人住的地方比不上汽車所用的土地,我們總土地面積比例當中,人在住的跟車子在走的,車子用的面積比人大,這叫現代化社會,車子起碼有三張床,人睡覺只需要一張床,車子在家要有一張床、出去上班要有另外一張床、去買東西還要有一張床,起碼三個,所以停車場永遠不夠,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問題。
到底誰才是老大?一個人才六十公斤,要推動一個人要用一千多公斤、兩千多公斤的機器推動一個人,又佔這麼大的空間,這是過渡期,所以我們現在才真正開始進入科技時代,以前的人都不叫做科技時代,叫做摸索科技時代,很多科技的副作用和愚蠢的科技我們把它當作高科技,其實以比例原則一看,簡直笑死人,誰是主、誰是從、誰是本、誰是末,根本搞不清楚。
莊子說從九霄雲外看,笑話一場,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真正講我們進入到比較了解科技的一個時代,我們絕對不能落後,很重要的絕對是「交通的方式」,從原來要跑路的變成不用跑路的,那從網路變成聲光電、自動化、人工智慧和你互動,幫你處理事務。所以我們很多的人力可以節省下來做小眾市場的開發,這個在臺灣也是一個長處。
臺灣第一個長處是生產成本管控,第二個是商業化,把東西拿來以後稍微做一些小小的修改,然後商業包裝。珍珠奶茶、木瓜牛奶諸如此類的,他沒有基礎的創新,但是可以做小小的改善。臺灣這點靈活度很高,但是基礎建設很困難,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源跟市場。做重大科技發展或是投資需要市場支持,臺灣沒有這麼大的市場,他的市場不穩定,所以他要靈活,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我們的廠商要靈機應變,隨時保持靈活性。
臺灣會以小幅度的變化來去做到顧客需求客製化的部分,可是做大樣的商品,臺灣比不過美國、中國大陸本身的市場。美國和大陸可以支撐,但我們沒辦法支撐這種重大投資,因為成本划不來。這不是笨不笨的問題,只是沒有這個環境。所以我們只能就這個環境和這種文化的特質去發展我們的經濟,而不是看人家做什麼,我們就 me too。如果這樣的話,臺灣就沒有優勢了。所以我想臺灣人可以跟歐美高科技產品的下游,歐美發展重大科技、我們做周邊的科技,然後來配合他的市場,這是我們很強的一個強項。
所以小眾市場其實對臺灣人而言是很不錯的,只要政府給我們一個大環境、好的硬體設備,剩下的年輕人自然會自己發展出來,而不是靠政府來規劃的。如何利用這個大環境,而不是像家長告訴小孩,你將來要做會計師、醫師、律師,一定要這樣子,一定要接我的業、一定要子承父業,將來醫生說不定沒工作,因為機器人醫生可能會取代八成的醫生,因為機器人的判斷比一般人的判斷更準確,所以只有特殊厲害的醫生可以打贏機器人,機器人只會往前走不會退化,可是人會退化,年紀大就會忘記東西。機器人有內建程式叫做 deep Learning,學習的程度遠超過我們,廿四小時都在學習,永遠不會忘東忘西,每分每秒都在進步。
所以人只能做創新的,心靈上的事情是人要做的,智慧機器人沒有心靈、沒有靈感,沒有人跟人的感情和感覺,這是臺灣的長處,你如果還在走老式的孫運璿、李國鼎式的工業時代發展,你就完了,因為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做的非常好,可是我們整個的科技環境變了,馬雲說趨勢贏過制度,趨勢的製造者就是科技,你任何的政治體制,網路交易平臺,新科技一出來通通改變,整個大環境是跟著改的,科技是最強大的,科技又跟著人性走,就是天性,所以老天爺最大,他設計的法則控制一切,接下來就是我們發現多少科技如何運用,再來就是人發明一些制度,科技再把制度毀掉,制度也就沒用了。
制度在下去就是公司內部的團隊,再下去就是個人,一層比一層差,所以我們要拉高層次,臺灣應該往拉高層次方向走,而非往下流走,就是動物性、直覺性的反應,還在走老路,沒有創新,你一定要用未來式、用前瞻性的想法往前走,要傳承古人的精神。但不能用古人的方法,否則就走老路了。他的原理方法沒有錯,但是他解釋的方法全部要變,因為那個時候的環境是農業社會、皇帝社會,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那個社會了,這樣解釋就不對了。
所以中國哲學的研究者還在講考據、講歷史就沒有意義了,所以沒有人看得起中國哲學,因為跟現在脫節了,不接地氣了。人民的生活是一切的本,孫中山講民生主義是他整個的精神,人民的生活是歷史的重心。這都是中國儒道思想傳承下來的一貫精神,尤其儒家,任何東西光講,不能做的,都是假儒家,不是真儒家,因為儒家最後一定是行,要做出來,我講的就是我做的,這就是儒家。
表裡不一,說一套做一套是假的,那叫假儒學。孔子怎麼說,就怎麼做、孟子也怎麼說,就怎麼做,絕對沒有說這邊講完之後,那邊又另外一套言詞來講,所以叫大丈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這叫正氣。大家都有這種正氣的話,你的企業一定強盛,雖然說短期會有一些波折。
我有一個學生在北京,非常有創意,他做大數據、人工智慧方面的,他是從麻省理工學院出來的,他就說在北京大陸人太難搞了,常常不知道他們嘴巴講的是真是假,又很狠,說翻臉就翻臉,他就問我說我要不要學他們那樣狡詐一點,也不一定要講實話。我跟他說,大家都狡詐的時候,你就一定要老實,因為物以稀為貴。前面五年很痛苦,但是當大家都說你是真的的時候,大家都來找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人多的地方絕對不是好地方,那叫做盲目、盲從。一定是迷失自我,所以一定要跳脫,別人都這樣講,你就不要這樣講,再講就沒有意義了。
在經濟學也是,你的競爭力就是你跟別人不同的地方,當你跟別人都一樣的時候,那叫完全競爭市場,就無利可圖。那臺灣的特質就是臺灣經濟發展的方向,你用這些元素如何組一個未來性的產業,而不是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一定輸。青出於藍很難勝於藍。自成一派的話,那就是你的專利,可以要更多的錢,很多公司很有錢就是靠專利。專利少,天天做很多苦功都是要付給別人專利費的話就划不來了。臺灣經濟發展的策略就是不要去看別人,可以參考瑞士、挪威如何成功,為什麼沒有幾個人 GDP 卻這麼高。大陸有什麼問題我們要能夠補足,因為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做交易比跟別的語言不通的國家比起來,摩擦更小,可是我們要帶動他,如何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利或以力服人,因為利力兩個一定輸,就變成跟班了,做跟班的就少拿錢。
所以,沒有那麼深奧,但是要把原則抓住,不要去看經濟學亞當.斯密講什麼?馬克思講什麼、凱因斯講什麼,跟你無關,很多都落伍,現在都用不上了,因為環境不同,整個科技技術也都不同了,整個科技水準變了。有一些亞當.斯密講的原則是對的、有一些馬克思講的資本主義問題也是正確的。國家領導人看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生產、消費、分配就只有這三個問題。如何將市場拉大,臺灣人是最可信賴的人民,我們的文化上最讓人親近,別人來的賓至如歸,原住民、漢人、荷蘭人來過,美國人也來了,日本也來過,所以我們講話常常一句話有好多種語言混在一起講。我們必須把自己的心牢和意識型態打開來,我們就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越國際化,我們的國防安全就越有保障。
領導人一定要天下為公,當領導人私天下、黨天下,像現在蔡英文現在這樣,政府又慢慢回到蔣介石當初,搞警備總部的味道,整個立法院全部變成行政院的橡皮圖章,蔡英文要什麼法、就訂什麼法,那這些法訂了完全不符合憲法精神、完全不符合民主自由精神,也完全不符合仁義倫理的精神,無法無天。
所以這樣子的話比蔣介石時代還更糟,蔣介石時代是因為有特殊原因,在戰爭狀態。現在已經沒有戰爭、沒有戒嚴時期,憑什麼搞一黨專政,所以表示我們的民主制度本身出了問題,為什麼一個政黨在行政和立法都是多數席的時候就可以變成一黨專政,為所欲為?這樣的話就失掉了民主自由的意義了。民主制衡不代表說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就可以為所欲為,這就是整個民主制度極大的一個問題。
司法被控制了、立法她也控制了、行政也被控制,這樣的話這個國家就變成獨裁國家了,完全沒有人權、沒有憲法。所以現在臺灣等於說倒退到那個狀況,你會讓很多國外的友人看到會嚇到。他會覺得說,他喜愛臺灣是因為臺灣有中國文化,人民善良溫和,我們又是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大家在一起打鬧一下都無所謂。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也不敢特別霸道,還要讓步給民進黨。兄弟中間也要讓一讓,孔融讓梨、兄友弟恭,大黨就像哥哥,小黨像弟弟,兄友弟恭再加上和樂融融,而不是暴力,誰力量大誰就硬幹。這樣的話就變成流氓社會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問題,我們在民主產生的問題,司法也可以配合行政機關,他要怎樣做,就怎麼做,說抓人就馬上去抓人,這有符合法治程序嗎?也無任何理由、也沒有任何的後果。抓人的人還可以繼續升官,這是什麼道理?為非作歹?國際人士看到絕對會嚇一跳,覺得說臺灣到底怎麼了?跟共產黨的大陸有什麼差別?
我們確實越來越像大陸了,可是起碼大陸經濟胸有成竹,做出成績來了。蔡英文專制,也沒看到成績,也沒看到她有經濟發展。往年經濟發展每年總有六趴七趴,過去有一成多,如果成長接近七趴,臺灣被你專制統治就算了,維持平平沒關係,總有出頭天。但妳現在經濟沒有經濟、政治沒有政治,做什麼不像什麼,就讓你們一家發財、一家爽。這有什麼道理?
所以這完全不符合任何體制的規範,所以我覺得臺灣的醫療很好,但是教育沒有配合經濟發展,臺灣既然不斷喊出『觀光』、『醫療』、『環保』的口號,那就要集中火力大量培育人才,讀醫學的學生起碼要多三倍,我們醫學院出來的人沒幾個,然後制度又一蹋糊塗,所以我們將來說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是四大皆空。因為都去搞整形美容的皮膚科。
然後再有一部份被拉到中國大陸去,認為他的薪水高,你整個就空了,生技業起不來,我們不是要發展生技業,是要發展長照產業、預防養生、中西醫混合,臺灣已經有這個基礎了,我們很多好的中醫、好的推拿,跟外科、骨科結合在一起,做一個國家研究院,只要我們把它擴大,變成世界招牌,將觀光業與醫療業結合、來享受自然環境,好山好水。
我們所有東西都在顧客面前種給他看,拿出來完全無毒、完全可以吃,你這個東西,一個人一餐起碼一百美金起跳,一千美金都不為過,紐約很多餐館一個人一千美金吃一餐,如果我們是對國際市場看,價位一點都不高。
我們一定要打高利潤的,人做的不高利潤的話,就被機器人取代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氣度,將來做的產業是品牌產業,比現在都要高上十倍價錢,同樣的東西但是做的精緻,有設計,有裝潢、有傳統文化歷史因素在裏頭,你要這樣子設計,而不是吃喝玩樂,雖然臺灣很小,有小國經濟發展的困難,但是小國有小國經濟發展的好處。因為小國的困難在於不易主導市場,大國可以,可是我們沒辦法。可是小國要的不多,只要在某一個地方挖一點點他就很肥了。
你看現在世界上高收入的國家八成以上、九成都是小國,平均 GDP 最高的都是小國不是大國。全世界排名人口不到一千萬的一大堆,GDP 非常高。因為他只要一小塊賺到就很肥了,所以我們不需要多,我們要由量轉為質,品質要跟歷史文化、跟大地、交通連結,跟教育連結,我們的經濟就會好。我很早就說我們可以做退休老人的生意,世界的財富八成都在五十歲以上的人手上,所以退休族是最有錢的族群,日本也是,年輕人一般沒有什麼錢,他有窮困老人,可是有錢的老人有錢的不得了,臺灣的財主也都五十歲以上,臺灣五十歲以下的不多,不是靠退休金,如果臺灣依照這一套去做,十年的時間內一定是前十名。
十年要狠拚觀光、醫療、退休、養生、中國文化保留等等這些產業。然後透過交通、網路及科技繼續延續我們的電子科技。如果這樣配搭的話,全世界最有錢的高官都來我們這裡了。我們不走賤價銷售的路線,像杜拜也不是當地人在消費,而是國際人士到那邊消費,他只有一成的臺灣人口。我們是找中上層階級的人來,大家都喜歡去杜拜,但沒有人要久住,像臺灣風和日麗,要建設起來絕對比杜拜好太多,以前日本就做過民調,將近有三成的老人,願意退休後到臺灣來過、退休生活,日本的退休老人來一成,臺灣經濟就發展了。
臺灣光大陸的客人就帶不完了。因為大陸來的我們接待上很方便,大陸有更深的文化背景淵源,語言又通,只差政治上的考量。
民國一○七年元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