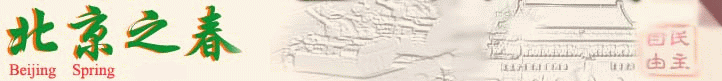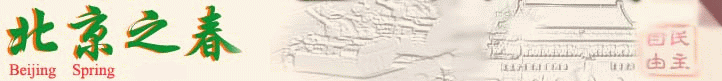文人的奴性和成就成正比
彭海
古代诗人最经不住鉴定。
诗是诗人对自我的人格想象,人格是诗人无法化妆的本质。
首屈一指的李白,未遭贬之前乃以溜须拍马混迹庙堂。并非逼不得已,实乃趋炎附势。
《唐史》记载,李隆基问李白,我用人比先皇(武则天)如何?
李白乖巧,对曰:先皇用人如同挑西瓜,专拣大的用,而陛下用人则注重物尽其用,拿捏得恰到好处。
李隆基经太白这么一拍,自是龙心大悦,捋了捋胡须,嗯!舒服。
未遭贬写诗也是意气风发,叹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遭贬,语境也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眼巴巴的看着没人搭理,又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从赏识到弃用完全是随机意外。
倒是诗人的情愫分泌出了眼泪。
苏轼的清高也是遭贬之后露出了端倪。
曰:高处不胜寒。再后来有些急切,曰:何日遣冯唐?
最后,“日啖荔枝三百颗”。
皇帝只不过借诗人的才华拉高“贤明”而已,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味道?皇帝的心思,核心价值,诗人不容易弄明白,还自作多情地遐想。
所以老是不知所措地遭贬时还幻想着皇帝回心转意再分一杯羹。
——活该!
——皇帝需要的是类似韩非、商鞅类的阴谋家。
——有了这种恶棍,做坏事便捷,到时候还是替罪羊。
中国的文人悟出了其中的奥妙竟然为虎作伥,通常脑洞大开后用黑话的形容词就是“积极主动”出卖灵魂兑换功名利禄,成为帮凶。
邪恶得邪乎,很悲催,但,这是真相。
更可悲的是更多的文人之乎者也地走火入魔了。比如范进类的砥砺前行者,苦苦思索也不开窍。
吴敬梓借用杀猪屠户厚实的巴掌照准面门重重的"伭斯ィ喽ァ�
很可惜,只是清醒了一会儿,回过神来,还是继往开来地做奴才。
——权力的魔力不可思议。
屈原刚烈。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同样经不起推敲。史学家考证出屈原乃是gay,断背,同性恋。
刚烈,情感的折磨迸发出匪夷所思的悲愤。此情此爱不是同性恋断断理解不了。此情此爱很尴尬,无法下笔吖。
无奈投江,因为风华绝代的屈原难免人老珠黄?岁月无情?
这事厘不出头绪呵,殉情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殉国,八竿子也捱不上。
但是,如此凄婉的断背爱情悲剧怎么就是这么硬生生的演绎成了殉国?端午节,还吃粽子。荒谬绝伦,断背节有没有?
以讹传讹的源头恐怕就是皇帝的核心价值观罢!如此一来还可成励志篇誘导更多的笨蛋殉国。
——权力的邪恶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