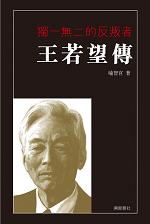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我离开中国,为的是求得更好的经验,求得更好的战斗的武器。暂别了,暂别了,在各方面斗争着的勇士们,我不久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到你们当中来!
—郑振铎《别了,我爱的中国》
第七章
别别了,我爱的中国
一 第三次出狱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来了,七月起,上海着火样的炎热持续了一个多月,气候异常既反应了天意也体现了民情,去年来积聚在人们心中的怒火至今还没散去。
羊子见不到王若望,只能从每月带出的东西来判断他的情况。几个月前,她发现王若望换出的裤子上“血迹”斑斑,忍不住捏紧裤子伤心痛哭,她以为王若望在狱中受了什么折磨。幸好,她含泪搓洗裤子上的“血迹”,半天褪不去红色,才看清原来是红漆。他裤子上怎么会沾上红漆?牢房里怎么会有红漆?
羊子焦躁不已,忧虞的心悬得更紧了。她不断打电话向作协及公安求援,希望中共当局不要为难年老体弱的王若望,但无人理会。
六月二十五日,在美国大使馆避难了一年的方励之夫妇被准许出国,听到这个好消息,羊子沮丧晦暗的心顿时闪出希望的光亮,王若望出头的日子应该不远了吧?亲戚朋友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有的还带上优质西瓜上门慰问,羊子企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羊子把好瓜保存起来,随时等待王若望回家吃个痛快。她引颈翘首,听到电话铃响,以为是公安通知她去接王若望;闻到有人敲门,她以为王若望回来了,就迫不及待去开门。一天、二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好瓜一个个少下去,有的已经变质了,仍然不见王若望归来,她的心又沉落下去。
羊子决定给上海市长朱镕基写信,信中说:六四期间,王若望写文章和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被中共视为反动言论,因此获罪。对于王若望的这些言论,我不加制止还相当赞许,因此我也有连带责任,希望政府把我也关进监狱,这样我既可接受中共“教育改造”,又可就近照料王若望的生活。
一个月过去了,朱镕基不理会她的请求。
一天,羊子途径人民广场,看到不远处的高楼上垂挂着两幅标语,红色布条上写着橘黄色大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她盯着标语,嘴里喃喃地念叨“民主、法制”,中国有“民主、法制”吗?如果有“民主法制”,王若望会无辜羁押在牢里吗?焱炎的烈日下,羊子的汗水混着泪水往下流,她要代丈夫发声,要为狱中的丈夫争自由。
回家后,羊子搦笔抒发自己的感触:
“……自从丈夫王若望被关进监狱后,我昼夜忧心忡忡,凄苦的思念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没人比我更了解王若望。他是离休老干部,却不甘坐享清福,颐养天年,难弃忧国忧民之心。不论高温蒸人的酷夏,还是寒气迫人的严冬,他都不停地伏案写作,批判阻碍改革的言行,为民主法制建设建言,常常写到半夜。好几次,他摸索着去上厕所时没找到门,撞到墙上跌倒了,他爬起来定一下神继续写……
“去年四、五月间,他给中央领导人写公开信,发表与领导不同观点和意见,力尽一个作家应有的职责,却为此遭遇‘秋后算账’。七月十九日他先受软禁,九月八日第三次入狱,至今十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尚未见上一面,还不能通信,更不得打听他的下落和近况。……我的心在收缩,我只能暗暗哭泣。
“……我渴望政府网开一面,宽容我们,及早让我们团聚,让王若望的严重眼疾及早得到治疗,让人道主义政策尽早落实到我丈夫和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身上。唯此,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一九九0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羊子拟了题目“何日王若望归”,文章在九月份的《百姓》杂志发表,羊子的呼吁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王若望的遭难暴露了中共的酷虐无道,引起更多的人讨伐灭绝人性的中共。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决定解决释放王若望。
二 失去难友钦本立
按公安“取保候审”的规定,王若望必须每月去第一看守所报到一次,如若违反要继续坐牢。
不久,王若望得到消息,钦本立病危,大约过不了一星期了。他听了心头一紧,自己戴罪在身,处于半自由状态,未经政府许可不能乱说乱动,尤其是探视同样是敏感人物的钦本立!但无形的胁迫挡不住患难中结成的情义,他决定不顾一切去医院看望老朋友,不!应该称老难友更合适,他们在同一条战壕上抗争,为此一同挨整受难。
钦本立形销骨立,面色灰白地躺在病榻上,王若望握住钦本立的左手说:“你会好起来的,要安心养病。”他强忍热泪,知道钦本立一直自认“愚忠”,始终对党保持着“第二种忠诚“,就轻拍他的手说:“党不会拋弃你的,你是党的忠诚的儿子,你要好好养病。”
王若望从钦本立的被精神迫害致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取保候审。钦本立的死没有吓住他,反而提醒他生命的短促,自己也进入暮年,在有限的生命中还要继续战斗。
三 办地下刊物
王若望又开始谋划新的斗争,这次他觉得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改变策略。
首先重新整合“人权研究协会”,在王若望的组织下,协会又吸收了九位新成员,他们都是忠诚民主事业的坚强战士。由于警察和特务到处跟踪,王若望为了他们的安全,吩咐他们不要盲动,暂时埋伏下来,同时积极扩大组织,争取全上海每个区都有协会的成员。
协会商讨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先办两份地下刊物,一份是《民主论坛》,由羊子牵头;另一份是《人权协会》,由王若望牵头。可惜,在各种势力的破坏下,地下刊物流产了。
四 别了,我爱的中国
地下刊物办不成,自己的文章没处发,王若望感到在大陆一事难成,有限的生命在空耗,他苦于找不到突破点。就在这时,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黄雨川再度邀请他出国领奖,上海作协领导同意王若望出国。
王若望也觉得,在大陆,他即使是一只鹰,也难逃被关在笼里的命运,啥事也做不成,不如暂时去国外,权作一只鸡,也可以自由飞翔,干点对中国有益的事。
王若望由此被逼上流亡之路。
飞机移动了,王若望紧贴舱窗,鲜红的“上海”两字渐渐缩小,最后随着飞机的升空而隐去,王若望凝噎着无声感叹:祖国,我眷恋的母亲,我在你怀抱已有七十四年,但无情的国家机器逼我远离,我不会忘了我肩负的神圣使命,更不会忘了江东父老,我要继续奋斗,争取早日重返祖国大地。
读者可通过“香港书城”网上书店邮购《王若望传》
|
王若望傳 --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