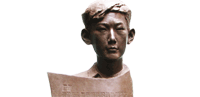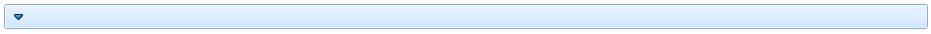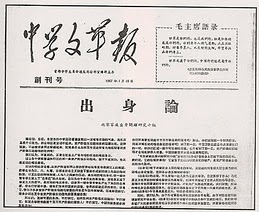
����ѧ�ĸﱨ��
��־��
��������ѧ��̸�ú�Ͷ����������һ��ǦӡС��������ѧ�ĸﱨ�������ˡ�
���Ļ����������ʼ�������������ȷ����˺������˶���������������1966��6�³����ڱ�����8��1�գ�ë��д�Ÿ��廪��ѧ���еĺ���������Ϊ���ǵ��ж�˵�����Է������췴�������������DZ�ʾ�����ҵ�֧�֡���ͬʱҪ�����ǡ�ע����ȡ�Ž�һ�п����Ž�����ǡ����Ӵˣ��������˶��鼰ȫ�����������ߺ����췴�������Ŀںţ�����ν��ţ�����ķ���������ν�������ɡ��������˵ط���ί�������Ⱥ��֮����ɱ����ͷ�������������1966��8���Ժ�����˴�����ë��֧�����ǵĴ��������8��18�յ�11��26�գ�ë���Ⱥ�8���ڱ����Ӽ�ȫ������������1300��ʦ���ͺ�������ȫ��ͣ�Ρ�ͣ��������������ǧ��ơ�9��5�գ��й����롢����Ժ����֪ͨ���϶���ȫ���ԵĴ�����1967��8�£�ë���١��͵��ָ�������������Ż����Ͻ�������
�������˶���ȫ�����Ļ���������ķ�չ�����Ʋ����������ã������ȫ�����ҵ���Ҫ���ء������ĸ�С���Ѳ�����ȫ���ƺ������������������һ��ʷ�����£������ˡ��ĸ�����е������������������ա������������˶��������ǰ����Ŵ��СС�ġ�С������Ծ�����ġ�1967�괺��֮�䣬��ȫ����Χ�ڸ���רԺУ����ѧ�ĺ�������֯�׳��汨ֽ����ʱ����ѧ��ֻҪ�����˴���һ�𣬰��ֱ����˴ռ���Ԫ�����ܳ�һ�ű�ֽ����
����ѧ�ĸﱨ�������������龳��Ӧ�˶���������Ѹ�ٴ���ȫ���ġ���
1967�����һ�죬�������е�IJ־������·�Ͽ����������ۡ������úܺã����������ĵ�ַ�DZ�����ʮ���е������ġ�IJ־����ͬѧ��������ȥ�������ģ�����̸�ú�Ͷ�����������ƪ����Ѫͳ�۵�����ӡ���������������������Ǻܿ�ó�һ�����ۣ���һ��ǦӡС������
˵�ɾɡ��⼸λ������Ѹ���ж���������������IJ־����ѧУ���500ԪǮ������֮�ڣ�����������ֽ����ϵ����ӡˢ����������æ�˼��켸�ޣ�1967��1��18�գ�����ѧ�ĸﱨ����ռ3��ƪ����Ǧӡ�������ۡ����������ˡ���
�����ġ���������IJ־���⼸��������������������ͬѧ��æ���������ǵĵܵܡ�ͬѧ�������ﻹ��Ů�����������˱�����ֽ��Щ�����Թ���������������СһЩ�ij��������ɣ������⼸�����������Ӵ����͡��༭��ֽ��У�����������ֽ�š���ϵӡˢ��Ů���Ǹ����������Ķ������š���ܽӴ����ù����������ĺ���������IJ־���ֹ�Ҳ�в��أ�IJϲ������д���˲š������ֵܱ���ͳһս�ߣ�����������֯���ƻṤ������ʱҲдд���ۺͶ��ģ�������ƫ����֯���ۻᡢ����ֽ�͵����ֳ�����λ����������������������Щ�����Ǹɲ��ɵ����Ժ����ǻ�������Ů��һ��ȥ��������Ů������һ�¶��ߵļ��顣��
���ǡ������ۡ�������ѧ�ĸﱨ��һ�ڴ��졡
��һ�ڡ���ѧ�ĸﱨ��ֻӡ��3��ݣ������̺䶯�˱����ǡ���
��һ�ڱ�ֽ�����������ǡ������ۡ��������ۡ�������̡�����������Ѫͳ�۵����£����ǻ���ͷһ�μ���������������߳��ڵ��ıʺͲ��ϵĹ㷺���²��������ж����ˡ�����Щʲô���ˡ���ʱ�ڽ��Ͼ��������������ۣ������Ƿ����������˵���������ˡ�����
�����ij���dz����ˣ�����Ķ��߰Ѽ�������������Χ�������γ���ǽ��ά������Ϊ�����ÿ졢������Ǯ�ͷ�ֹ���������Dz��ò��涨ÿ������5�ݡ���ʱ���ǰѱ�ֽ�����������Ĺ�Ƥ�����������ȵ���Ⱥ�Ѷ����ٽ��صĹ�Ƥ�䶼�����ˡ����������Ķ��飬ʱ���ﵽ200���ˣ��������ֻʣ��ӡ���˵�Ҳ�����������ߡ���
С���������½����г��ϣ�����ѧ�ĸﱨ�����̳��˼�ֵ��ߵ���Ʒ��������õ���������ֻ�û�2ԪǮȥ��ԭ��2��һ�ݵı�ֽ����
�������ۡ������ܵ�������˵Ļ�ӭ��ԭ����1966��7��29�գ���������ѧԺ���еĸɲ���Ů����һ�������������ǡ�����Ӣ�۶��ú����������ǡ����ӷ������쵰���������ǡ�������ˡ����⸱��������Ϊ���������������������������壬��Ϊ������һ�������������˵�ج�Ρ�8��2�գ��²����ڽӼ�������������ı���˫������ʱָ������������ȫ�桱���������Ϊ����ĸ�������Ӱࣻ��ĸ���������ѡ���Ӧ��ˡ�����
�²��イ���Ժ�ʹ�����ͳ�Ϯ�з⽨Ѫͳ��˼���ѧ���Գ���Ϊ����Ѹ�ٷ�Ϊ�����ɱ����廪�������ѧУ�������˳�����ƶЭ���ķ糱���˺��������Ҫ�ѡ�����Ӣ�۶��ú������ӷ������쵰��������ȫ��ġ��������Եġ����Ľ�·�������У�Ҫ����������Ϊ���ߣ�����Ϊ����������������ѧ��Ѹ�ٷֽ�Ϊ�������ࡱ���������ࡱ����
�������ۡ�������������ỷ����д�����ġ�����˵�������˵�ظ������ҷ���ռȫ���˿ڵ�5������ô���ǵ���Ů�������Ҫ��������ֶ�ü������������ʱ��ҡ���ʷ������ӡ���֪ʶ���ӵ���Ů����û����ְԱ����ԣ��ũ����ũ�ײ����Ů�����������룬�ǡ������������������һ�������Ӵ�����֡������й���һ�����Ĺ��ң����ǰֻ��200�����ҵ���ˣ���������������Ѫͳ������ͥ�IJ����ࡣ��һ�����������õ�����һ�㲻�ܲξ�����������Ҫ��������ˣ����嵽����λ�����ǣ��ǡ����������ռ�˾������ơ���ʹij���ǡ�������������������Ҳ��Ȼ�зǡ����������������ԶԳ������ⲻ���ĵļ���û�С���
�������ۡ��Ļ���Ҫ���ǣ�һ�����Ӱ��ԶԶ���ڼ�ͥӰ�죬���Ҽ�ͥӰ��ĺû���Ҳ������ĸ�����ε�λ��ת�ơ����������ͳɷ�����ȫ��ͬ���������������һ���˺û��������ı��־���ȫ�����ˣ������ٿ����ij������ġ������������������õ��������Ⱥ������أ��ѳ�Ϊ�����ġ����ˡ����γ��µ������ƶȡ�������ѹ�������������ȡӦ�е�ƽ��Ȩ�����������ۡ������ܵ�ӵ��������Ϊ�������һ�����˹��ĵ����⡣��
�����ǡ���ѧ�ĸﱨ��������ʵ�����ʡ�
д���������ۡ����ˣ��������ĵĸ�����ˣ���һ����24�꣬�DZ����������������ͽ�������˳�����һ���������ࡱ��ͥ������1950�걻����ר������ʱ������8�ꡣ�������º͡���������������ǻۡ���ѧϰ�����У�����ֲ�и��Ҫ�����ν�����Ҫ��������ȶӡ������ţ�Ȼ����Щ����Ҫ����Ϊ���ij�������ܾ��������ϵ�ʧ��ʹ����֪ʶ�����¿�����γɡ�˼�����Դ�������
���ѳ����7�ڡ���ѧ�ĸﱨ���ϣ�����һ����д�����ֽ���ռ�������ķ�֮�������˸ñ�������ʵ�����ʣ�����ȴ��һ������Ӣ�ۡ���ֽÿһ�ڶ���һƪ��������ͥ���������о�С�顱д�����¼��С�飩�Ĵ�����£���ʵ�������������ˡ����˻��Ը��ַ�ʽ����ͬ������д��������Ȥ��������Ʒ����������������ġ��ο���Ϣ�������������š�ר������ҲЭ��ѡЩ��Ĭ����Ԣ����̵���ģ����磺������������ѧԺ���˶������ơ��ľɡ�ʱ�����˹涨���������õ�ͬѧ���ܸ���������Ҫ�IJ��ɣ�ֻ�ܸijɡ��쵰�����������ӡ������磬�պ£���С��»쵰���ȵȡ������ӱ�ʡ����ij��ѧ��������һ��ͨ������õĽ�������ǰ�ţ��������õ��ߺ��š���Щ�������ò������ˣ��ֲ�����ǰ�ţ�Ҳ��Ը�ߺ��ţ�ֻ���ɴ��ӽ����ˡ�����
����ʦ��Ů����һЩͬѧ���ȳ��ơ�����������������ɷǡ������ࡱ����ˡ�������������������ij�����������Ѫͳ���ߵ�������Χ�������ڶ���Χ������Ωһ�����ǣ���֯���������˶����ǵ��ж������ͣ������ܵ�����ѧУ����֯����������ʵ���ԡ�������������ʺܷ��У���Ϊ���⽨ɫ��̫Ũ�����õܵ�����֯��������֯���������뺴��ij���ˣ�����֤������һ������������ʲô���������궼Ӧ����ƽ�ȵ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