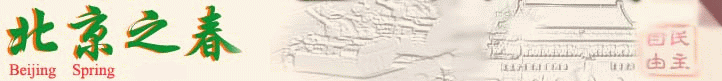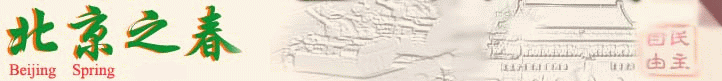以言为碑:纪念刘晓波逝世八周年
李聪玲
2025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八周年。在过去的八年中,世界持续剧变,而他所坚持的理念——自由、非暴力、言说的权利,依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挑战。在这个纪念的时刻,我们不仅回望他生前的轨迹,更要思考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刘晓波最初以文学批评家身份进入公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批判鲁迅传统、呼唤思想自由的“激进派”姿态而著称。作为一位“思想狂人”,他挑战意识形态权威,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1989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归来,卷入那年春夏之交席卷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他在天安门广场与其他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绝食行动,试图以非暴力方式缓和局势,避免流血冲突。虽然最终未能阻止镇压,但这一行为也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自1989年起,刘晓波因参与民间政治与言论表达,先后多次被拘押、软禁或监视居住。2008年底,他因参与撰写《零八宪章》再度被捕,并于次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零八宪章》是一份由刘晓波起草并联合303位知识分子签署的政治纲领,呼吁宪政改革、司法独立、结社自由与人权保障。其发布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却迅速被认定为“政治威胁”,成为他再次入狱的导火索。
2010年10月,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本国籍人士。当时他正服刑于辽宁锦州监狱,无法出席典礼。奥斯陆市政厅的授奖现场,为他保留了一张空椅子,这一象征画面震撼了世界舆论,成为当代人权斗争的象征之一。中国政府对该奖项作出强烈反应,封锁相关报道,切断与挪威的高层外交与文化交流达六年之久。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国与国际人权体系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2017年6月,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彼时他已服刑近八年,健康状况引发广泛关注。虽然当局批准他“保外就医”,但在国际社会和家属多次要求其出国治疗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仍未允许他离境。他最终于7月13日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逝,终年61岁。他的遗体随后被迅速火化,并于渤海湾海葬。在外界质疑家属是否充分知情与同意的情况下,这一做法成为持续争议的焦点。至今,他在中国没有一块公开的墓碑,也没有一个可以合法凭吊的地方。
2009年法庭上的自辩词中,刘晓波说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句话被写入诺贝尔奖颁奖词,也成为他精神信仰的核心表达。这一立场曾被部分人质疑为天真或软弱,然而在非暴力政治传统中,它却有其深远意义:正如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一样,刘晓波选择了“以和平对待压迫”。他的“不仇恨”因为他相信仇恨无法缔造真正的自由社会。在他看来,反抗暴政不应变成另一个暴政的温床。他用尽一生,去捍卫一个可能并不现实,但绝不应被遗弃的理想:用温和与理性去对抗不公。
今天,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较八年前更为受限。《零八宪章》的理念在公共媒体中几乎消声,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遭遇边缘化。然而,刘晓波的思想与名字,并未被彻底抹去。他的文字持续在网络、地下出版物与海外文集中流传。他的经历,成为人们理解政治良知、体制代价与自由精神的重要注脚。他留下的,不只是诺贝尔奖的一张空椅子,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中保持人格尊严的道义坐标。
假如刘晓波仍在世,2025年的今天,他或许仍在监禁中,或许依然拒绝仇恨。他不会指望暴力推翻什么体制,也不会沉浸于失败主义。他可能会继续写作、继续辩护,为思想表达而存在。他说过:“自由表达是一切自由之母。”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如何对待不同声音。
刘晓波生前不愿被称为英雄,他只是一个不愿沉默的写作者、一个不肯放弃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轨迹,让我们意识到: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中,说真话,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纪念他,并非将他神化,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即使身处黑暗,人也仍可选择温和、坚持、体面地活着。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仍愿意说出“我没有敌人”的人,都是一块无形的碑,一座没有墓地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