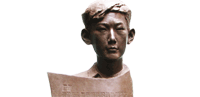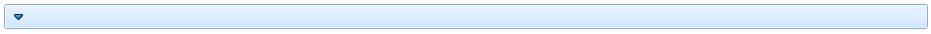1998�������Ժ��Һ���������������Ϊ�༭��������������䡷һ�飬һֱ�跨�����˵İ�����������ϵ����������������������ж��ˡ�ֱ����ף����ڡ��Ϸ���ĩ���Ϸ�����һƪ��Ϊ��������˭���Ķ��ģ�ȴ����ؽӵ��������ĵ�һ�����档ԭ���������˱���ͨ���༭������鵽�ҵĵ绰���ɴ�������ʶ����Ϊ���ѡ���ϧ��ʶ̫������ϵ�ϵ�ʱ���DZ����Ѿ�������Ƭ����ӡ�ڼ�����ʱֻ������д��һ����̵ġ��ϡ�������ĩ����������������ֵر����Լ����뷨��
������ʶһ�����������һ��ȥ�����ѧ�μӹ���ѧ�����ŵĶԻ���һ��ȥ�ݷù����ĸ�б��Ⱥ�������֣������ʿ������Ů����Ҳһ����ܹ����ߵIJɷá��Ҹе�������һ��ͷ�����ѡ������ḻ�����������ػ�������ʷ�ж���˼�����ˡ��ںܳ���ʱ�����û�з��ԵĻ��ᣬ�����롰��Ĭ�Ĵ�����������С���ʵ������������̫��Ļ�Ҫ˵�����ľ����������̲���һҳ������ʷ�������Ҷ��������죬��������Գ����������ļ������е��Ŀ��ѣ�Զ��һ����������ȡ���һ�������ˣ����ĸ�о����������Ρ�����������д�ˡ�������Ⱥ������ҲӦ�����˼�¼�������й��˾����Ŀ��ѡ����������뷨���ҽ���������дһ������¼����¼���ľ���������ȫ�ҵ����ˡ�
�����Ľ������ҵĽ��顣�����������˵ĺ����ߺ͡���ѧ�ĸﱨ���Ĵ����ߡ���Ȼ������¼����������������ִ���һ�����ʣ�ȴ�����˺ܸߵļ�Ԧ��������дһ���֣����ҿ�һ���֡��ҵĸо��ǣ���������λ���ѵijе��ߣ�Ҳ��һλʮ�ֵ�λ����ʷ��֤�ˡ������ı�ȷ��ϴ�������������ã��ḻ����ʷϸ�ڴ����ı��´��ݵ�������չʾ��һ�������������ʷ����������1999������ʣ��������������Ȿ�顣����ȡ�����ض���ζ��������֡��������Ҽҡ���
���Ҽҡ�����˵���й�������50�����70�����Ȩ״����һ����Ӱ�������ĵĸ�ĸ����������ѧ�����ѧ��ר���Ľ����˲ţ�һ���ó����̼�����һ���ó���ҵ�����������ҵ��Ǿ���1957�걻������ɡ����˱�����һ�����ΰμ�ĺ�ѧ���������ȲμӸ߿��������ڴ�ѧУ��֮�⡣�����ĺ��������⼸������Ҳ�����������б��������ᡣ
���˵�ʱ�ܹ���һ����ʮ���������ͽ�������ݣ���Ϊ��Ȩ˼��ң�����żȻ�ġ���������Ŀ���Ѿ�����Ʒ���˶��꣬��ʹ��˼���˶��꣬���˶��꣬��������˼��¬����������˼��ij��ӽ����˼���������ֱ��1966��ĩ��1967��ͷ���������ʧ�ص�ʱ�����õ���һ�������Լ������Ļ��ᡣ�����DZ�Թ���˺��Լ���ͥ�ܵ��������Ĵ���������Ϊ�����ܵ���Ȩ���ӵ�������ȡ�������������۵ĸ߶ȶ����ֲ���������������̵����С�������ԡ������ۡ�Ϊ�����ķ����ڡ���ѧ�ĸﱨ���ϵ�һϵ�����¡���Щ��������֪������һ�����������ϵõ�ǧ�����ˣ��ر����������ϱ����ӵ��������Ⱥ���ǿ�ҹ�����
���Ҽҡ��ּ�¼���й����ű���ʷ�ϵ���Ҫһҳ���������Ե����˵����ݣ���ϸ�����ˡ���ѧ�ĸﱨ����������չ��ز�۵�ʼĩ����ݱ�ֽ��Ȼֻ�ǵ�ʱ����ǧ�Ƶ�С��֮һ��ǰ��ֻ����7�ڣ���������꣬����һȺ��֪����û�в�����Ҳû�а챨����������˲ִٵذ������ģ��ഺ����������������ȼ�գ����Ǵ�������֪�����塣��Ȼز�ۣ�������Ϊ�й�����ʷ��һ����������ꡣ
���������±��Ͷ������˶����֪�࣬�����������������ļ��ˡ����ˡ����ݡ����ѡ��������Ǹ�����������ĸ���ĥ�ѣ��Լ�������ĥ���������ǿ�������������������������ʷ���л���ɲ��֡��������Ȿ�飬�����ö��������侳��ؽ����Ǹ���������ײ㣬�ӳ��е�ƶ������ũ��һֱ���η��������������������Ͻ������Ҽҡ�����һ���ѵõ�������60�����70����й����ײ�����Ρ����á��˼ʹ�ϵ���������������
������һ��Ҳ���й���������ҫ������ĸ�״��������ǰ�������˴������ƽ���Ժ��ֵ��ι�����ЭίԱ�����ĵܵ�Ҳ������Ϊ����ģ������������Ƶ����¥�������ֵܷ����ġ�ǰ��ʽˮ�л����������Ժ�����̸����Щ�����ʱ����ϧī���������Ҫ�ıʴ�������չʾ���ļ�ͥ�������������干ͬ�����Ŀ��������ˡ����Ҷ������й���д�Ļ���¼���ԣ����Ƶ�д�������������������Ǵ�̸һ������ô�����ն��������̸�������ȴһ�ʴ��������ַ��������֡��Ҽҡ�����ɫ���ںͷ������ڡ�
2001�꣬���ľ����ƾ��������������Ѿ�54�ꡣ���ڱ����з��г������ӹ��ò�������������������Ȱ�����DZ��������˵����á����������ͣ������ֲ�ͨ����ȥ�����ѹ��̫���ˡ��������ֹ۵�˵����ȥ��û���⡣
2004�����죬��ȥ��������һ�μ��������ġ���μ��棬������������ǰ�ݶ��ˡ�ԭ���������������·���װ�ޣ��ɵĶ�����������������Ļ�������ߣ����Ի�ɲ��꣬�������ࡣ̫̫�����ᣬ����������е����Բ�ͨ������ѹ���ܴ�����ô��������ӣ���Ȼͦ�����ˣ����Һܿ���Ӧ�˻������������˷��ӣ���Χ�����Ѷ�������Ŀ������룬���ıϾ��Ǿ�������ѵ��ˣ����������Σ������±��Ͷ������˶����֪�࣬������һ�㣬������˵����ʲô�����죬�����Ŀ���������ȥ���ҡ������¼Ұ��ڰͶ���Ħ���Ͷ���Ħ��������������ǣ�����˥���ˡ������ļ�ס��һ������һ���ֵ�ĩ�ˣ��羰�ܺá����ð���������һ���ϰ�����Ϸ��ӣ�����������������һ������ܴ�ֻ��һ��������仹��ס�������㶼��Σ������Ϊ����ʧ��Ҫȫ�������ޡ�������ҵ��ʱ�䣬һ���������·���������˵�����������������Dz���